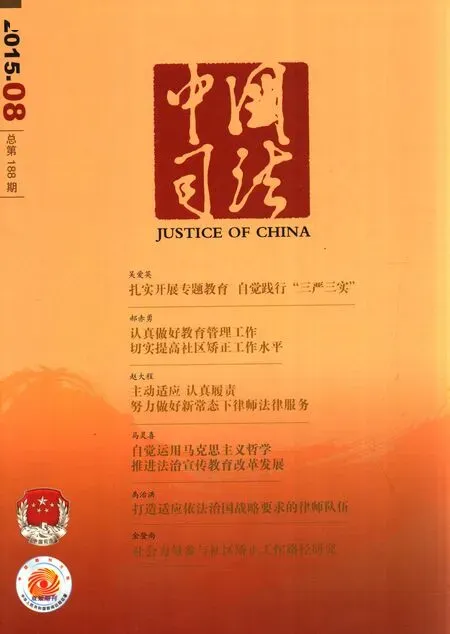各國(guó)關(guān)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比較及啟示
劉 方(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
各國(guó)關(guān)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比較及啟示
劉方(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一、我國(guó)刑法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guī)定
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第2款、第3款規(guī)定:“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關(guān)系密切的人,通過(guò)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權(quán)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guò)其他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為請(qǐng)托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索取請(qǐng)托人財(cái)物或者收受請(qǐng)托人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méi)收財(cái)產(chǎn)。”“離職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guān)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原職權(quán)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shí)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從刑法的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我國(guó)刑法中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主體包括三種情況:(1)國(guó)家工作人員和離職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其中又包括國(guó)家(離職)工作人員的配偶、父母(包括養(yǎng)父母)、子女(包括養(yǎng)子女)、同胞兄弟姐妹。(2)其他與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包括離職國(guó)家工作人員)關(guān)系密切的人。這是一個(gè)相對(duì)抽象的概念,在適用時(shí)不僅要從雙方之間的親密與交往程度上考慮,還要根據(jù)他們?cè)谑苜V過(guò)程中的配合程度以及實(shí)際所起的作用來(lái)綜合判斷,任何單純、片面的做法都可能是錯(cuò)誤的。(3)在職務(wù)范圍之外,對(duì)具有職務(wù)行為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產(chǎn)生影響的其他國(guó)家工作人員。當(dāng)然,這一點(diǎn)在理論上還存在爭(zhēng)論,但實(shí)踐中是客觀存在的,而且與斡旋受賄行為也存在原則上的區(qū)分。
我國(guó)刑法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客體,盡管理論上存在多種觀點(diǎn),其實(shí)還是一般受賄罪犯罪客體爭(zhēng)論的延伸。主要包括“職務(wù)行為的不可收買(mǎi)性”、“職務(wù)行為的廉潔性”和“法益侵害性”等幾種觀點(diǎn)。我們認(rèn)為,以“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廉潔性”作為犯罪客體比較合適,這樣可以明確體現(xiàn)出受賄類(lèi)犯罪的基本性質(zhì)。
在犯罪客觀方面,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的“影響力”和“不正當(dāng)利益”歷來(lái)是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也是司法實(shí)踐中判斷時(shí)最棘手的問(wèn)題。所謂“影響力”,是指國(guó)家工作人員固有的權(quán)力、地位、職務(wù)對(duì)社會(huì)所產(chǎn)生的影響。影響力的核心內(nèi)容是“權(quán)力”,但權(quán)力是通過(guò)具體的職務(wù)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所以,沒(méi)有職務(wù)的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可能產(chǎn)生這種“影響力”。刑法理論中也有主張“權(quán)力性影響力和非權(quán)力性影響力”共通的說(shuō)法,但把“非權(quán)力性影響力”概括進(jìn)去,是與賄賂犯罪的本質(zhì)要求相違背的。例如,一個(gè)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藝術(shù)家,倘若他沒(méi)有任何公職務(wù),即使存在較大影響力,同時(shí)也有人利用了他的影響力,但最終仍不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職務(wù)犯罪行為。至少在我國(guó)刑法中應(yīng)當(dāng)是這樣。
這里的“不正當(dāng)利益”,應(yīng)當(dāng)包括非法利益和其它不應(yīng)當(dāng)?shù)玫降睦妗7欠ɡ媸侵高`反法律規(guī)定的利益;其它不應(yīng)當(dāng)?shù)玫降睦妫侵阜欠ɡ嬉酝膺`反一般社會(huì)共同生活準(zhǔn)則所得到的利益。利益的違法性和不正當(dāng)性可能來(lái)自?xún)蓚€(gè)方面:一個(gè)是實(shí)體方面,一個(gè)是程序方面。前者是利益本身包含著違法性和不正當(dāng)性,如生產(chǎn)和販賣(mài)毒品所得利益;后者則可能包括利益本身的合法性和違法性?xún)煞N情況。司法實(shí)踐中要注意的是,不應(yīng)當(dāng)把“不正當(dāng)利益”限定在“非法利益”范圍,這樣理解實(shí)際上是曲解了《刑法》第388條的規(guī)定。
行為人主觀方面的構(gòu)成特征本文不展開(kāi)討論,筆者認(rèn)為,該罪與一般受賄罪對(duì)主觀構(gòu)成要件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二、《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guī)定
《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以下簡(jiǎn)稱(chēng)《公約》)第18條規(guī)定:“各締約國(guó)均應(yīng)當(dāng)考慮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故意實(shí)施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一)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shí)際給予任何不正當(dāng)好處,以使其濫用本人的實(shí)際影響力或者被認(rèn)為具有的影響力,為該行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從締約國(guó)的行政部門(mén)或者公共機(jī)關(guān)獲得不正當(dāng)好處;(二)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任何人員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直接或間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當(dāng)好處,以作為該公職人員或者該其他人員濫用本人的實(shí)際影響力或者被認(rèn)為具有的影響力,從締約國(guó)的行政部門(mén)或者公共機(jī)關(guān)獲得任何不正當(dāng)好處的條件。”①陳正云、李翔、陳鵬展等著:《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全球反腐敗的法律基石》,中國(guó)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頁(yè)。
上述規(guī)定在刑法中通常被解釋為“影響力交易”犯罪。從《公約》的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公約》)第18條規(guī)定中的(一)部分,主要針對(duì)的是影響力交易中的請(qǐng)托一方; 第(二)部分中指的是被請(qǐng)托一方,即受托人。實(shí)際上,這兩類(lèi)人中,都包括有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的犯罪主體。這是因?yàn)椋鳛椋ㄒ唬╊?lèi)中的人員,我國(guó)刑法中的利用影響力的犯罪主體,有的就是作為請(qǐng)托人來(lái)利用公職人員的權(quán)力和職務(wù)。如與公職人員關(guān)系密切的人,向公職人員許諾給予好處或者其他請(qǐng)求方式,利用他的職務(wù)和權(quán)力獲取非法利益。作為第(二)類(lèi)人員,無(wú)論是“公職人員”,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員”,都是在利用公權(quán)力上的影響力,基本上全部概括在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的犯罪主體之列。從公約規(guī)定的內(nèi)容看,主要目的在于打擊請(qǐng)托一方。在適用刑罰時(shí),即包括利用影響力的需求者,也包括利用影響力受賄的實(shí)施者。
在如何解釋“影響力”的性質(zhì)方面,學(xué)者們對(duì)《公約》)第18條規(guī)定的解釋明顯表現(xiàn)出與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規(guī)定的內(nèi)容存在差異。如有的學(xué)者將《公約》中所指的“影響力”,解釋為“可分為權(quán)力影響力和非權(quán)力影響力”。②陳正云、李翔、陳鵬展等著:《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全球反腐敗的法律基石》,中國(guó)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頁(yè)。這在《公約》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是可以理解的,因?yàn)椤豆s》)第18條中規(guī)定的“其他人”,顯然不是公職人員,無(wú)論是影響這類(lèi)人,或者利用這類(lèi)人的影響力,恐怕都難以界定為公權(quán)力影響力。但在我國(guó)刑法中就不能這樣認(rèn)為,因?yàn)槲覈?guó)《刑法》第388條規(guī)定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關(guān)系密切的人”,都是圍繞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和權(quán)力來(lái)設(shè)定的。如果把其他與公權(quán)力無(wú)關(guān)的影響力也包括到其中來(lái),必然違背了《刑法》第388條的立法原意。
從《公約》)第18條中(一)部分所規(guī)定的文字上看,請(qǐng)托一方似乎相當(dāng)于我國(guó)刑法中的行賄人。其實(shí)不然,第一,請(qǐng)托人在這里利用的是影響力,而不是直接利用職務(wù)和權(quán)力。雖然請(qǐng)托人可能就是行賄人,但也不排除請(qǐng)托人是利用影響力獲取好處的第三人。只能這樣理解,在《公約》第18條中(一)部分中,利用影響力進(jìn)行交易犯罪的行賄人和從中獲取利益的受賄人,可以作為同一犯罪的共犯處理。第二,《公約》中規(guī)定的是請(qǐng)托人“許諾給予、提議給予或者實(shí)際給予任何不正當(dāng)好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許諾給予、提議給予”和“任何不正當(dāng)好處”,與我國(guó)刑法中規(guī)定的“通過(guò)其他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為請(qǐng)托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索取請(qǐng)托人財(cái)物或者收受請(qǐng)托人財(cái)物”的規(guī)定之間差距較大。因?yàn)椋霸S諾給予、提議給予”不等于最終產(chǎn)生交易,“不正當(dāng)好處”也不一定就是“財(cái)物”。
三,其他各國(guó)刑法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guī)定
世界各國(guó)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采取不同的立法態(tài)度或者立法形式,有的國(guó)家對(duì)此作出了具體的、明確的規(guī)定,有的只簡(jiǎn)單地、概括性地規(guī)定,還有的至今并沒(méi)有規(guī)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里,我們將部分國(guó)家刑法中有關(guān)這方面內(nèi)容概括為以下幾種類(lèi)型:
(一)沒(méi)有作出明確規(guī)定
如《法國(guó)新刑法典》第435—1條規(guī)定:“為適用1977年5月26日在布魯塞爾簽訂的‘關(guān)于同牽涉歐洲共同體公務(wù)員、歐盟成員國(guó)公務(wù)員的賄賂行為作斗爭(zhēng)的協(xié)議’,共同體公務(wù)員、歐盟成員國(guó)的國(guó)家公務(wù)員或者歐洲共同體委員會(huì)、歐洲議會(huì)、共同體法院與共同體審計(jì)法院的成員,于任何時(shí)候,無(wú)權(quán)直接或間接索要或認(rèn)可奉送、許諾、贈(zèng)禮、饋贈(zèng)或其他任何好處,以完成或放棄完成其職務(wù)、任務(wù)或者受委托的行為,或者由其職務(wù)、任務(wù)或受委任而帶來(lái)方便的行為,處10年監(jiān)禁并科150000歐元罰金。”③引見(jiàn)羅結(jié)珍譯:《法國(guó)新刑法典》,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頁(yè)。該條法律被認(rèn)為是只針對(duì)一般受賄犯罪的規(guī)定,因?yàn)榉缸镏黧w只是公務(wù)人員,其中并不包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又如《蒙古國(guó)刑法典》268條第1項(xiàng)規(guī)定:“公務(wù)員在其職務(wù)權(quán)限內(nèi)利用職務(wù)支持、縱容或者作出對(duì)行賄人有利的爭(zhēng)議解決,或者為了行賄人的利益履行或不履行其應(yīng)當(dāng)或可能履行的職務(wù),無(wú)論事前有無(wú)承諾,而獨(dú)占地收受賄賂的,處以最低工資額51倍以上250倍以下罰金或5年以下徒刑,并處禁止3年內(nèi)擔(dān)任一定職務(wù)或從事特定職業(yè)。”④引見(jiàn)徐留成譯,謝望原、馬松建審校:《蒙古國(guó)刑法典》,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頁(yè)。該法律與前述法國(guó)刑法典的規(guī)定一樣,是只針對(duì)公務(wù)員的受賄犯罪行為。
再如《日本刑法典》第137條規(guī)定:“公務(wù)員就其職務(wù)上的事項(xiàng),收受、要求或者約定賄賂的,處5年以下懲役;接受請(qǐng)托的,處7年以下懲役。”“將要成為公務(wù)員的人,就其就任后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職務(wù),接受請(qǐng)托,收受、要求或者約定賄賂的,成為公務(wù)員時(shí),處5年以下懲役。”⑤引見(jiàn)張明楷譯:《日本刑法典》(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5頁(yè)。但日本刑法典除了上述規(guī)定的一般受賄罪之外,還規(guī)定有第三者受賄罪(第138條)、斡旋受賄罪(第141條)以及斡旋第三者受賄罪(第142條)等罪名,這些罪名中事實(shí)上也包括了部分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在內(nèi),只是從法律條文中難以直接找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個(gè)罪名罷了。
上述國(guó)家法律中雖然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并不排除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利用公權(quán)力所產(chǎn)生的影響力進(jìn)行受賄的行為給予處罰。只是處罰的罪名不是以利用影響力受賄認(rèn)定,而是以其他受賄行為認(rèn)定,如日本刑法就是這樣。
(二)與一般受賄罪混合規(guī)定
例如,《德國(guó)刑法典》第332條規(guī)定:“1.公務(wù)員或?qū)珓?wù)負(fù)有特別義務(wù)的人員,以已經(jīng)實(shí)施或?qū)⒁獙?shí)施的、因而違反或?qū)⒁`反其職務(wù)義務(wù)的職務(wù)行為作為回報(bào),為自己或他人索賄、讓他人許諾或收受他人利益,處6個(gè)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2.情節(jié)較輕的,處3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3.犯本罪未遂的,亦應(yīng)處罰。”⑥引見(jiàn)徐久生、莊敬華譯:《德國(guó)刑法典》(2002年修訂),中國(guó)方正出版社第167頁(yè)。其中規(guī)定的“讓他人許諾或收受他人利益”,實(shí)際上包括了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在內(nèi)。
又如,我國(guó)澳門(mén)地區(qū)《澳門(mén)刑法典》第337條規(guī)定:“公務(wù)員親身或透過(guò)另一人而經(jīng)該公務(wù)員同意或追認(rèn),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應(yīng)接受其不應(yīng)收之財(cái)產(chǎn)利益或非財(cái)產(chǎn)利益,又或要求或答應(yīng)接受他人給予該利益之承諾,作為違背職務(wù)上之義務(wù)之作為或不作為之回報(bào)者,處1年至8年徒刑。”⑦引見(jiàn)澳門(mén)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譯:《澳門(mén)刑法典澳門(mén)刑事訴訟法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yè)。該規(guī)定中的“透過(guò)另一人”,實(shí)際也包括了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在內(nèi)。
再如《俄羅斯聯(lián)邦刑法典》第290條第1項(xiàng)規(guī)定:“公職人員為了行賄人或其被代理人的利益而實(shí)施屬于其職權(quán)范圍內(nèi)的行為(不作為),或公職人員由于職務(wù)地位能夠促成此種行為(不作為),以及利用職務(wù)之便進(jìn)行一般庇護(hù)或縱容,因而親自或通過(guò)中間人收受金錢(qián)、有價(jià)證卷、其他財(cái)產(chǎn)或財(cái)產(chǎn)性質(zhì)的利益等形式的賄賂的,處數(shù)額為10萬(wàn)盧布以上50萬(wàn)盧布以下或被判刑人1年以上3年以下的工資或其他收入的罰金;或處5年以下的剝奪自由,并處3年以下剝奪擔(dān)任一定職務(wù)或從事某種活動(dòng)的權(quán)利。”《俄羅斯聯(lián)邦刑法典》的上述規(guī)定,實(shí)際上與我國(guó)澳門(mén)地區(qū)刑法典的規(guī)定比較接近。因?yàn)槭苜V行為主體中都涉及到第三人,就不免存在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
(三)概括性地單獨(dú)規(guī)定
如《西班牙刑法典》第428條規(guī)定:“當(dāng)局或者公務(wù)員對(duì)其他公務(wù)員或者當(dāng)局施加影響,利用后者職務(wù)或者其他源于其人際關(guān)系或者官職等級(jí)的地位,達(dá)成能直接或者間接為前者或者為他人謀取經(jīng)濟(jì)利益的決議的,處6個(gè)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并剝奪其從事職業(yè)或者擔(dān)任公職的權(quán)利3年至6年,同時(shí)給予追求或者獲得利益兩倍的罰金。確已獲得利益的,在法定刑幅度內(nèi)取較重半幅度處罰。”該法第429條還規(guī)定:“私人對(duì)某公務(wù)員施加影響,利用后者職務(wù)或者其他源于其人際關(guān)系或者官職等級(jí)的地位,達(dá)成能直接或者間接為其或者為他人謀取經(jīng)濟(jì)利益的決議的,處6個(gè)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同時(shí)給予追求或者獲得利益兩倍的罰金。確已獲得利益的,在法定刑幅度內(nèi)取較重半幅度處罰。”⑧引自潘燈譯,張明楷、(厄瓜多爾)美娜審定:《西班牙刑法典》,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頁(yè)。
又如《越南刑法典》第291條規(guī)定:“任何人利用自己的影響促使有職權(quán)者做或者不做其職權(quán)范圍內(nèi)的某事或者做某件法律禁止的事,以直接或者間接獲取金錢(qián)、財(cái)產(chǎn)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物質(zhì)利益價(jià)值在50萬(wàn)盾以上5000萬(wàn)盾以下,或者價(jià)值雖在50萬(wàn)盾以下但造成嚴(yán)重后果被紀(jì)律處分后又再犯的,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⑨引自米良譯:《越南刑法典》,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頁(yè)。
再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22條規(guī)定:“提議或者許諾向公務(wù)員或擁有公職身份的受委托從事公共服務(wù)的人員給予不應(yīng)接受的錢(qián)款或其利益,以誘使其實(shí)施職務(wù)行為的,如果該提議或者許諾未被接受,處以第318條第1款規(guī)定的刑罰,并且減少三分之一。”“如果做出上述提議或許諾是為了誘使公務(wù)員或受委托從事公共服務(wù)的人員不實(shí)施或拖延實(shí)施其職務(wù)行為,或者是為了誘使其實(shí)施違反其義務(wù)的行為,在該提議或許諾未被接受的情況下,對(duì)犯罪人處以第319條規(guī)定的刑罰,并且減少三分之一。”⑩引見(jiàn)黃風(fēng)譯注:《最新意大利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6頁(yè)。
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第2款、第3款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其內(nèi)容和形式與上述國(guó)家法律比較接近,即都是明確地、單獨(dú)地規(guī)定了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的處罰,但規(guī)定得比較簡(jiǎn)單,在范圍、對(duì)象的界定方面有些粗放,因而也容易造成司法實(shí)踐中應(yīng)用時(shí)難以準(zhǔn)確把握。
(四)既明確、又相對(duì)具體地規(guī)定
例如,《新加坡共和國(guó)刑法典》第163條規(guī)定:“從任何人處為其自己或他人接受或取得,或者同意接受或企圖取得任何酬金,作為通過(guò)施加個(gè)人影響誘導(dǎo)公務(wù)員做或克制做某項(xiàng)公務(wù)行為,或在該公務(wù)員履行職權(quán)時(shí)提供或不提供好處,或從政府、國(guó)會(huì)議員或內(nèi)閣成員、或任何公務(wù)員的職權(quán)為誘餌給任何人提供或企圖提供服務(wù)或不予服務(wù)的起因或回報(bào),處可長(zhǎng)至1年的有期徒刑,或罰金,或兩罰并處。”引見(jiàn)柯良棟、莫紀(jì)宏譯,柯良棟、陳力校:《新加坡共和國(guó)刑法典》,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頁(yè)。可以看出,新加坡刑法中規(guī)定的內(nèi)容,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方式、行為對(duì)象和行為主體等,都比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規(guī)定的內(nèi)容更具有可操作性。
又如我國(guó)澳門(mén)地區(qū)《埃及刑法典》第106條A規(guī)定:“任何人因?yàn)槔闷湔鎸?shí)的或者聲稱(chēng)的影響從公共機(jī)關(guān)獲取或者力圖獲取工程、命令、裁判、決定、勛章、特許權(quán)、許可證、供應(yīng)協(xié)議、采購(gòu)協(xié)議、職位、服務(wù)、其他任何種類(lèi)的特別待遇或者利益,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取、收受禮物或者接受將被給予這些禮物的許諾的,視為受賄。如果行為人是公務(wù)員的,處以本法典第104條所規(guī)定的刑罰;在其他情況下,處拘役,單處或者并處200埃鎊以上500埃鎊以下罰金。受公共機(jī)關(guān)監(jiān)督的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視為公共機(jī)構(gòu)。”引見(jiàn)陳志軍譯:《埃及刑法典》,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頁(yè)。
再如,《奧地利聯(lián)邦共和國(guó)刑法典》第306條a規(guī)定:“(1)作為公營(yíng)企業(yè)負(fù)責(zé)雇員的同事,用咨詢(xún)、建議或者證明材料對(duì)企業(yè)管理施以有規(guī)律的影響,且以該身份為通過(guò)影響負(fù)責(zé)雇員違反義務(wù)實(shí)施或不實(shí)施法律行為,為自己或第三人索要、收受或讓他人許諾給予利益的,處2年以下自由刑。(2)有經(jīng)驗(yàn)的顧問(wèn)用咨詢(xún)、建議或證明材料,對(duì)官員或公營(yíng)企業(yè)的負(fù)責(zé)雇員在履行其職務(wù)行為時(shí)施加重大影響,且以該身份為通過(guò)影響官員違反義務(wù)實(shí)施或不實(shí)施職務(wù)行為,或通過(guò)影響負(fù)責(zé)雇員違法義務(wù)實(shí)施或不實(shí)施法律行為,為自己或第三人索要、收受或讓他人許諾給予利益的,處與本條第1款相同之刑罰。”引見(jiàn)徐久生譯:《奧地利聯(lián)邦共和國(guó)刑法典》(2002年修訂),中國(guó)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頁(yè)。該規(guī)定雖然主要針對(duì)公司、企業(yè)而言,但在我國(guó)存在大量國(guó)有企業(yè)的前提下,仍然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還有如,《美國(guó)模范刑法典》第240·7條規(guī)定:“行為人以對(duì)公務(wù)員施加特別影響力或者使他人對(duì)公務(wù)員施加特別影響力為對(duì)價(jià),索要、收受或者同意接受經(jīng)濟(jì)利益的,成立輕罪。‘特別影響力’,指利用親屬關(guān)系、朋友關(guān)系或者其他關(guān)系而行使的影響力,與事務(wù)本身性質(zhì)的好壞無(wú)關(guān)。”劉仁文等譯:《美國(guó)模范刑法典及其評(píng)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頁(yè)。美國(guó)屬于普通法國(guó)家,刑法典對(duì)司法不產(chǎn)生直接約束力,但對(duì)法官判案仍然具有較大的參考作用。該法律與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罪相比較,在行為方式和行為對(duì)象方面要更為明確。
四、對(duì)完善我國(guó)刑法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guī)定的啟示
通過(guò)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第18條規(guī)定和世界各國(guó)有關(guān)賄賂犯罪法律規(guī)定的比較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為完善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提供參考。
(一)在犯罪主體認(rèn)定方面的啟示
按照我國(guó) 《刑法》第388條第2款、第3款的規(guī)定,構(gòu)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一般是排除在國(guó)家工作人員之外,即只有屬于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關(guān)系密切的人,才構(gòu)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這樣從立法上人為地進(jìn)行限制,給司法實(shí)踐中帶來(lái)了很大困難。這種規(guī)定主要是受我國(guó)傳統(tǒng)犯罪構(gòu)成理論的影響。國(guó)際上關(guān)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犯罪的法律規(guī)定,如《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第18條、《新加坡共和國(guó)刑法典》第163條、《埃及刑法典》第106條A以及《美國(guó)模范刑法典》第240·7條等都沒(méi)有明確限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犯罪主體的范圍。《埃及刑法典》中是用的“任何人”,《美國(guó)模范刑法典》中是用的“行為人”,《新加坡共和國(guó)刑法典》中沒(méi)有典明,意味著什么樣的人都可以構(gòu)成。我國(guó)刑法中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主體的限定,不僅難以調(diào)和與其他賄賂犯罪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也造成司法實(shí)踐認(rèn)定中的很大麻煩。
(二)在行為方式認(rèn)定方面的啟示
我國(guó)刑法對(du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客觀行為方式規(guī)定的內(nèi)容,即表述為“通過(guò)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權(quán)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guò)其他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為請(qǐng)托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索取請(qǐng)托人財(cái)物或者收受請(qǐng)托人財(cái)物。”從這一法條規(guī)定中,并沒(méi)有看出行為人是利用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而是直接在利用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職務(wù)行為。所以,我國(guó)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將該規(guī)定解釋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雖然迎合了立法者的意圖,但并沒(méi)有切中法律條文的原義。到底是立法上的問(wèn)題,還是解釋方面的問(wèn)題?我們認(rèn)為主要是立法方面的問(wèn)題。因?yàn)榱⒎ㄕ咴O(shè)立本條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懲治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解釋者如此進(jìn)行解釋沒(méi)有錯(cuò)。可以看出,無(wú)論是《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還是《新加坡共和國(guó)刑法典》,抑或《美國(guó)模范刑法典》,都是明確地把“利用影響力”作為本罪成立的主要客觀表現(xiàn)形式。而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的“通過(guò)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似乎讓人感覺(jué)到行為人是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共同實(shí)施一般受賄犯罪。
(三)在共犯關(guān)系認(rèn)定方面的啟示
最后一個(gè)問(wèn)題是,我國(guó)刑法關(guān)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guī)定,在理論和實(shí)踐中所產(chǎn)生的一個(gè)難以解決的矛盾,就是在認(rèn)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一般受賄罪、介紹賄賂罪以及行賄罪之間所導(dǎo)致的模糊概念。這個(gè)問(wèn)題在各種賄賂犯罪之間本來(lái)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很多國(guó)家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只規(guī)定一般受賄罪、行賄罪,或者再增加一些如斡旋賄賂罪、賄賂第三者罪、介紹賄賂罪等等,也可以稱(chēng)得上是五花八門(mén)。但我國(guó)既然規(guī)定了這個(gè)罪名,就需要從概念上把它的構(gòu)成要件闡述清楚,否則司法實(shí)踐中就難以有效操作。例如,我國(guó)《刑法》第388條第1款規(guī)定的行為,被認(rèn)為是以受賄罪處罰的“斡旋受賄行為”。對(duì)此,如果某一國(guó)家工作人員不是以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身分去利用另一個(gè)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權(quán)的影響力受賄,是應(yīng)當(dāng)定受賄罪,還是應(yīng)當(dāng)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一個(gè)簡(jiǎn)單的例子是: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如果他本身也是國(guó)家工作人員,那么他通過(guò)該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上的行為,為請(qǐng)托人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而收受賄賂,是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還是以《刑法》第388條第1款的規(guī)定定受賄罪?當(dāng)然,如果該“近親屬”是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當(dāng)然不成問(wèn)題。這類(lèi)同樣的行為性質(zhì)就完全有可能得出兩種不同的處罰后果,而這兩個(gè)不同罪名在刑罰上的量刑幅度又相差很大,這就可能給行為人帶來(lái)不公平的處罰結(jié)果。這個(gè)問(wèn)題是我國(guó)有關(guān)賄賂犯罪立法中應(yīng)當(dāng)亟待加以完善的問(wèn)題。
(責(zé)任編輯朱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