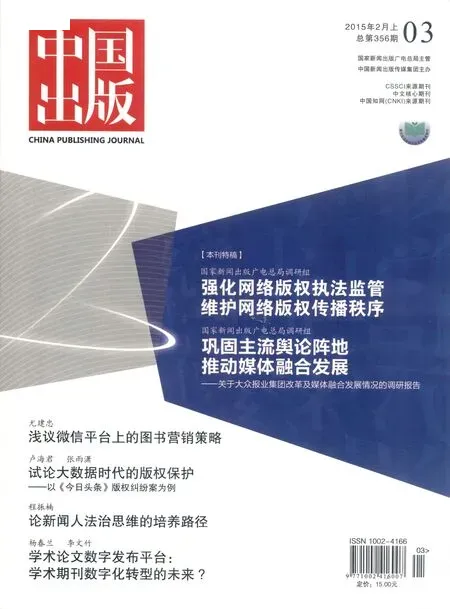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生態影響初探*
□文│李林容 李 珮
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生態影響初探*
□文│李林容 李 珮
新媒體日新月異的發展對傳統媒體生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及影響,解構和重塑著整個媒體生態格局。本文主要從新媒體對媒體生態的沖擊和影響、傳統媒體的數字化轉向兩個部分展開探討,力圖為傳統媒體的新變革及其未來走向提供一些啟示。
新媒體 傳統媒體 媒體生態
21世紀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更是一個創造傳奇的時代。新媒體技術以前所未有的迸發之勢,重構了媒介的現實圖景,重塑著媒介生態結構,并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及行為方式發生變化。
一、新媒體操盤牽動社會變動
各種新媒介已經成為了傳媒版圖上日漸顯要的板塊,然而其生存與發展絕非割裂傳統媒體的存在價值,而是在拓展、整合與優化中彰顯新媒體謂之“新”的價值和意義。
1.立體延伸:拓展舊媒體功能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在他看來,媒介不僅僅包括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播介質,而且還包括“一切人工創造物,一切技術和文化產品,甚至包括大腦和意識的延伸”。[1]換言之,任何媒介的出現都是人的感覺和器官的延伸。報紙和雜志是人視覺的延伸,廣播是聽覺的延展,電視是視聽感官的綜合拓展。以網絡技術、移動終端為支撐的新媒體在生活生產領域的應用,實際上是人的感官在更高層次上的延伸。同時,這種延伸也是傳統媒體(舊媒體)在功能上的歷史演進與時代發展。
“一種媒介有自我轉化為另一種媒介的功能”。[2]媒介的形態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化與演進之中。數字電視、手機報紙、衛星廣播、手機廣播、移動電視等作為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地拓展了舊媒體的媒介功能。例如,數字電視就是對傳統電視功能的一種延伸。一是數字電視的頻道增多,數字電視頻道多達百套;二是信號質量提高,畫質更清晰;三是互動性增強,傳統電視觀眾只能按照電視的播放順序觀看電視節目,而數字電視實現了雙向傳輸,觀眾可以自由選擇播放的時間、順序和進度。數字電視作為數字技術與電視技術合力鑄就的產物,它不是兩種技術的物理疊加,而是在拓展電視技術的基礎之上的數字化生成。
每一種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模式發生變化。報刊、廣播、電視等舊媒體在人的交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媒體傳播的內容往往是人際交往的重要談資。而互聯網、手機新媒體等,強化了交往的重要性并拓展了人際交往的范疇,不僅延伸了舊媒體的傳播內容,且在時效性、交互性上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2.生態重塑:改造傳統媒體生態環境
“數字化生存”讓人們重返“部落村”,媒介環境由此發生各種改變,媒介結構在數字化的推動下日益變遷。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普及,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媒介生態重塑,受眾分流。新媒體的便捷性、交互性、虛擬性等特征,讓許多年輕人對傳統媒體不屑一顧。在數字化時代,人們似乎已經不再習慣傳統的報刊閱讀和電視觀看,而是在網絡上瀏覽數字報紙和觀看網絡視頻。
《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2011-2015年展望》顯示,“中國的娛樂和媒體產業,在寬帶以及移動網絡用戶激增的推動下,正朝著數字化平臺轉向,預計到2015年,26.3%的娛樂及媒體行業收入將來自數字化平臺”。[3]這也印證了尼葛洛龐帝預言的“數字化生存”時代的來臨。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必將導致媒體生態、媒體格局的重構。
新媒體時代,宏大的敘事結構在眾生喧囂中被消解,完整的意義被割裂成為無數的碎片,海量的信息傳播正逐步向“微傳播”轉向,微型傳播媒介以及微傳播內容備受人們喜愛。比如微博、微信等改變著舊媒體的結構、意義以及人們的媒體經驗。碎片化的媒介內容讓用戶體驗便捷的同時,成為了新媒體的語境表征。新媒體語境下的“微傳播”是數字化的一種產物,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
3.媒介融合:跨界生產與跨域重組
隨著互聯網、流媒體等媒介技術的不斷出現,在加劇媒介變遷的同時,讓媒介融合成為這個時代的各種可能,成為當代傳媒發展的流行趨勢。“媒介融合關注媒介形態的聚合和變遷”[4],它并非是不同媒介的一種物理融合,而是多種媒介形態內在的滲透與融合,以達到媒介重構的目的。
從目前來看,新媒體的強勁發展既是媒介融合的體現,又是媒介形式的新突破。換言之,新媒體整合、重組了傳統媒體的各種元素。傳統報刊的深度閱讀、廣播的聽覺體驗以及電視的視聽享受都被融入了新媒體的內在肌理。2010年,我國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移動電視、智能手機、iPad等新設備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閱聽信息的重要平臺。如手機報就是以手機終端為技術支撐,以報紙內容為意義指向的融合形態,它滿足了受眾的兩種需求,即獲取報紙信息和享受手機樂趣;再如網絡視頻至少由兩種媒介融合而成,即電視媒體和互聯網媒體的融合。
總之,媒介融合是傳統媒體走向數字化發展的必由之路。新媒體并非是一種單一的媒介樣式,而是整合了多種媒介元素的媒體形態。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元素的整合,所要實現的是“1+1﹥2”的效果及價值。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傳播內容的再造,使內容資源得到復合性使用,擴展延伸了原有產業鏈。并且,我們不應當忘了媒介融合將帶來的是“先合后分”的局面,“合”是為了更有效地進行“分”。通過融合最終實現更高層次的多樣化和細分化。
4.想象互動:重構人際關系模式
新媒體重構了人際交往模式,作為一種融合媒介,是人際交往、組織交往以及群體交往與溝通的最佳平臺。
新媒體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交往方式和行為習慣。比如,在社交媒介的影響下,人們已經不再習慣整體思維,而崇尚整體被割裂的碎片樣式,喜歡簡單的符碼、簡潔的表達、簡約的傳播。在人們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改變的過程中,對傳統的人際交往進行解構。面對面的溝通被自媒體的交互式體驗所取代,QQ、SNS、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讓人們的對話與交流更自由和開放。在新媒體所建構的朋友圈子中,信息的互動更多地體現在缺乏真實場景互見的精神交往,這種交往過程就是一種想象的互動。以微博為例,朋友圈子通過關注而建立,關注的那一刻,想象就已經開始。關注朋友的同時,本身充滿了對新信息的期待以及對細節的想象。通過對朋友信息的瀏覽和閱讀,內心會對想象信息和事實信息進行對比。當然,博主在發布信息之前,內心會想到關注自己的閱讀心理,這同樣是一種想象。在相互關注以及相互評論的過程中,想象互動更為清晰。博主與粉絲之間留言的同時,對遠隔時空的另一方都充滿了想象和期待。無論是在線的互動留言,還是一廂情愿的信息關注,想象互動一直存在于人際關系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跨越時空的傳情更能夠表達真實的自我心境。
5.生產革新:推進文化產業轉型
文化產業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媒體新技術與文化內容的交融匯合成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新媒體改變著當今文化的生產結構,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加速了文化產業的整合、升級與轉型。
新媒體產業作為當今文化產業的建設性力量,其建構的過程就是加速文化產業轉型的過程。當今文化產業正處在全面轉型時期,這種轉型包括了文化體制的轉型和文化形態的轉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向,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也是走向文化、經濟繁榮的標志,而“傳播新技術正在消解傳統文化的生產形式”。[5]傳統文化產業以內容為導向,以整體為形式。新媒體打破了這種結構,導致文化產業分化以及與其他文化樣式融合。“文化產業的邊界被拓展,形成多種技術相結合、多方利益相糾結的新的產業形態”。[6]總之,新媒體不僅成為文化產業的有效制作和播出平臺,整合了產業組織,優化了產業結構,使文化產業圍繞著創意生產形成新的文化產業鏈,并促使媒體在融合中不斷創造出新的產業類型與盈利模式。
二、新媒體轉向彰顯價值存在
新媒體在完成自我超越的同時,推動了傳統媒體的新媒體轉向。無論是報紙與網絡的融合,還是廣播與數字技術的匯流,抑或電視與移動終端的交匯,都體現出了媒體發展的數字化轉向,并滲透到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成為彰顯媒體價值的最佳佐證。
1.體驗消費:受眾行為的變遷及轉向
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內容的“碎片化”和選擇的自由化契合了新時期受眾需求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傾向,受眾的這種選擇是他們對“微傳播”的一種體驗消費。有實證研究表明:在信息認知上,微博受眾個體之間離散化;在態度傾向上,微博受眾之間則呈現趨同化現象,這是因為微博平臺將信息和意見的傳播同步化了,受眾比較容易受微博上主流意見的影響,對同一事物作出類同的評價。[7]作為新媒體的微博正是因為受眾在信息認知和態度傾向上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于傳統媒體的新特征。
任何新技術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傳播技術也不例外。當受眾不能滿足于傳統媒體的時候,當現有傳播技術不能適應受眾需求的時候,新媒體便呼之欲出了,此時,媒體為受眾的存在而不斷革新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2.謀變而動:社區結構的更新與升級
我們生活在一個組織的世界里。組織內部成員之間、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溝通、交流和協調都離不開媒體,為了適應組織結構和組織關系的改變,媒體必然發生改變,反之,媒體的創新也必然影響組織的改善與重建。這里的組織在新媒體中其內涵等同于“網絡社區”,互聯網傳播的多樣化和靈活性為瞬息萬變的社區成員的關系提供了交流的良好平臺,為社區功能的實現夯實了基礎,“是傳遞工作期望和落實工作程序的重要環節”。[8]
互聯網上的虛擬社區代替了現實生活中的組織,網上的實時聊天、視頻和其他互動代替了傳統組織中的人際傳播,盡管交流的可靠性有所降低,但交流的便捷性今非昔比,互聯網上的“社群”成員之間的聯系更加頻繁和緊密,也更容易實現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
Web2.0社區把傳統的“以內容為王”轉化為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與人的關系,其內容生產主體由專業組織變為個體,而個體生產內容的目的,不在于內容本身,而在于以內容為紐帶和媒介,來延伸自己在網絡社會中的關系。這種新型網絡社區通常以“鏈”為主,此“鏈”式結構是靈活的、動態的,用戶活躍度較高,規模也非常龐大,每個人都可以“以自我為中心”來構建自己的人脈網。[9]不過,網絡“社群”沒有剛性的契約關系,群主可以任意建立和解散一個群,群里的任何成員想要加入或退出也不需繁瑣的程序。顯然,新興“網絡社區”具有不同于傳統“組織”的含義,更具有虛擬性、集合性和自由性。
三、結語
新媒體形態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社會的生產構成、文化模式,解構了傳統的人際交往模式,影響了大眾的閱聽行為,成為傳媒版圖上最靚麗的文化坐標。并且,新媒體強大的力量和能量對傳統媒體形成巨大沖擊并改變著傳統媒體格局,促使傳統媒體以及新媒體自身在不斷變革、轉向和尋求進步。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
[1]何道寬.媒介革命與學習革命[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5)
[2][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57
[3]何懷崇.宣傳片的媒體結構特征變化[J].現代傳播,2012(12)
[4]趙紅勛,王甫.尋求媒體最大公約數[J].西部電視,2013(4)
[5][6]吳小坤.新媒體發展的問題導向與破解思考[J].新聞記者,2010(8)
[7]管登峰.新舊媒體受眾的觀念現實差異實證研究——以報紙和微博為例[J].新聞世界,2012(7)
[8]胡河寧.組織傳播學:結構與關系的象征性互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2
[9]李林容.社交網絡的特性及其發展趨勢[J].新聞界,2010(5)
*本文系2014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微信與媒介生態環境建構研究”(14BXW01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