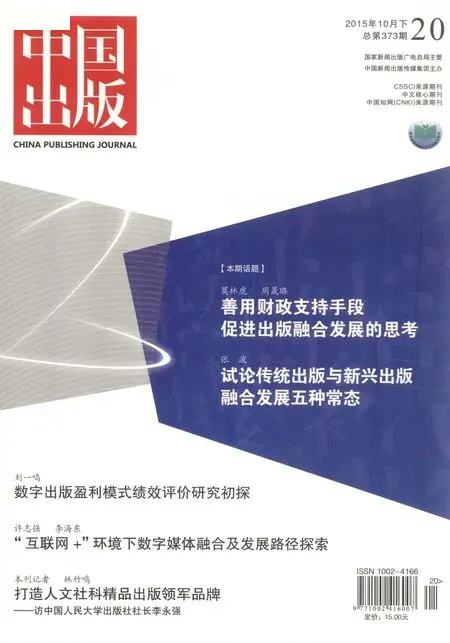由記者臥底高考反思新聞專業主義與職業法理道德*
□文|李小華 張付偉
由記者臥底高考反思新聞專業主義與職業法理道德*
□文|李小華張付偉
由《南方都市報》記者臥底高考替考組織及其報道引起社會爭議為案例和緣由,從新聞專業主義的不同理解和態度、新聞法規與職業倫理道德的缺失及媒體在調查和報道中所體現的價值取向上的失衡等方面,探討這一事件及相關行為引發爭議的原因,以期促進新聞報道的良性發展。
臥底暗訪新聞專業主義新聞法規職業倫理
2015年6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第一場考試開考沒多久,《南方都市報》就在其新聞客戶端、官方微信公眾號同時發布一篇“重磅!南都記者臥底替考組織,此刻正在南昌參加高考”的文章,詳細披露了南都記者長期臥底一個高考替考組織,并探明湖北個別高校有多名大學生加入該組織,試圖通過充當“槍手”牟利,而7日上午,包括南都記者在內的多名“槍手”正在江西南昌一些考點參與考試。此報道一出,立刻震驚正高度關注高考的家長和網民們,引爆了社交輿論場,該文隨即在微信朋友圈被迅速傳播,僅十幾分鐘,輿情從微信急速擴散至微博,引起頭條新聞、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主要賬號的關注與轉發,也引發了一大批意見領袖與媒體人的評議。其后,《南方都市報》繼續以“江西開查跨省團伙實施高考替考”“江西9涉案者被警方控制,替考者如何闖關?”等為題進行后續報道。關于南都記者臥底調查此事的輿論,剛開始幾乎呈一邊倒的傾向,稱贊記者的膽識和魄力,維護了高考的公平和社會正義;但隨后,輿情發生了轉變,出現了多元的聲音,主要就記者直接走進考場替考,這種調查方式是否違法,以及新聞呈現的細節、報道的方式是否符合職業倫理道德規范等問題,引發了較大的社會爭議和擔憂。對此,本文擬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討論。
一、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不同詮釋
“新聞專業主義”這個源于西方新聞界的概念,是新聞由一種“職業”演變成“專業”,進而在追求“專業化”過程中形成的一套新聞操作理念。新聞專業主義強調傳媒作為社會的公器,應獨立于任何威權之外;新聞從業者作為事件的報道者、社會的瞭望者,不應從屬于任何利益集團,而是無論何時都要客觀、準確、公正地報道事實,挖掘真相,表現出新聞記者崇高的職業操守。自20世紀初以來,新聞專業主義被不斷宣揚,成為新聞從業者追逐的理想,記者們在這一理念的觀照下,高舉專業主義的大旗,紛紛扮演著“真相代言人”或“新聞專家”的角色。
但是,興起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公共新聞學對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理念提出了挑戰,“公共新聞學”強調公眾與新聞工作者平等地參與新聞事件,每一個受新聞事件影響的人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記者不僅要報道新聞更應該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告訴公眾如何應對問題。公共新聞學基于“社群主義”,源于20世紀20年代杜威與李普曼關于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作用的爭論。[1]杜威主張平民主義的新聞路線,因為他認為公眾自身有能力獲取所需要的新聞信息,這樣更能促進民主社會的形成;而李普曼則強調精英主義的新聞路線,他主張隨著人類交往范圍的無限擴大,信息總量與社會環境的復雜性進一步增強,個人必須借助于專業的新聞媒體才能更好地了解自身與周圍的環境。后來的現代新聞學基本踐行李普曼的觀點。新聞專業主義強調記者自由、獨立的調查和報道身份,通過對公眾利益和公共服務的關懷來獲得職業自主性和社會聲望。[2]
不僅公共新聞學思潮沖擊了新聞專業主義,社會化媒體的興盛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通過對公眾的賦權給予公共新聞學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不但降低了專業媒體的“職業自主性”,而且通過對精英主義意識的否定削減了專業媒體的社會聲望;另一方面,在傳統媒體主導的時代,媒介被譽為“社會的公器”“正義的化身”,但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大眾媒體被從神壇上請下來,媒介化語境下人人都可能是記者,處處都有“麥克風”,記者的權威性被降低,公眾不再迷信記者的專業性。
在此背景下,南都記者臥底高考事件出現質疑的聲音就不足為奇了。在此次替考事件中,南都記者不辭辛苦跨省調查,從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進行長達7個月的追蹤暗訪,并千方百計深入替考組織,獲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站在精英話語的角度看,這是媒體秉持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報道的體現。然而,正如前所言,當今社交媒介已動搖了傳統媒體對信息傳播的絕對權威,信息化時代,民主思想不斷提升,公民意識得以極大覺醒。受權力、地位、身份等外在因素制約的民眾,曾經都是弱勢群體,總處于失聲狀態;但在轉型期社會主導價值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領域意識形態的控制開始弱化,部分話語權從精英階層轉移至普通民眾身上,公民的主體意識增強,開始理性地思考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并作出自己的判斷。[3]因此,或許是歷經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新聞界、社會精英、普通民眾都對新聞專業主義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態度,故針對南都記者臥底高考事件,民眾有自己的認知和評判,不再一味地相信新聞報道,不再毫無疑義地信奉媒體所宣揚的專業主義,開始質疑記者參與高考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其報道方式的合理性。
二、新聞職業法理道德的反思
任何成熟的行業都是他律與自律的結果,新聞業也不例外。在法制層面上,“新聞法治”是為了規范和治理新聞傳播活動,雖然目前我國法制建設總體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新聞法規的完善還較滯后。這種法制缺失的最大困境就是造成新聞活動法律邊界的模糊性,從而給新聞采寫與報道留下了爭議的空間。比如,就“江西替考事件”來說,一些業界人士認為記者臥底替考涉嫌違法,并援引我國刑法的規定說明臥底記者所面臨的法律風險;但另有些學者和民眾對記者的行為表示理解和支持。
在替考事件中,記者本人也進入考場參與考試,干擾了考場的秩序,有損高考制度的嚴肅性,從嚴格意義上說,同樣也涉嫌違法違紀,質疑的焦點就在于記者用不合法的手段去揭露違法的行為是否合理。我們贊同,目的的合理性不能替代行為及其結果的合法性,目的不正當,方法再精致,也是一種罪惡。[4]記者的參考行為雖然暗含正義與邪惡斗爭的道德支撐,但是難掩其本身的不合法性,違背了高考制度這一群體規范的原則。
除了是與非的法律問題,新聞傳播活動還涉及好與壞、善與惡等倫理與道德層面的糾紛。法律是媒體在新聞實踐過程中應遵循的“底線”,而職業道德與媒介倫理則是自律的要求。在暗訪替考事件上,媒體的新聞操作也存在一定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在報道中直接披露被替考者的姓名、住址等個人信息,對其他相關人員的照片也未經過一定的技術處理,媒體這種過度暴露公民個人信息、涉嫌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有失新聞報道的人本精神和人文關懷。美國倫理學家雅克·保羅·蒂洛曾提出人道主義倫理學的五條原則——生命價值原則、善良(正當)原則、公正(公平)原則、說實話或誠實原則、個人自由原則,蒂洛認為,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任何道德體系都能發揮作用。[5]這些原則相當廣泛地關注一切人及其道德待遇,但自由原則必須建立在遵守其他原則的基礎之上,媒介實踐活動也是如此,記者雖享有采訪和報道的自由,但首先得尊重他人的生命,維護人的尊嚴始終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國內外類似的案例屢見不鮮,譬如,2014年2月央視通過暗訪的方式披露東莞色情服務產業,輿論譴責色情行業泛濫的同時,也對記者假扮嫖客的行為提出了疑慮。同年7月,上海東方衛視派遣3名記者進入福喜公司,潛入生產線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臥底調查,后公開題為《過期重回鍋 次品再加工 上海福喜食品向知名快餐企業供應劣質原料》的深度調查報道,揭露了這家公司的違規行為,但記者的行為同樣受到了倫理道德方面的拷問。在國外,記者臥底調查事件也時有發生,如2002年,英國《泰晤士報》的一名記者假扮銀行家,進入牛津大學試探暗訪,聲稱愿捐贈40萬英鎊給4個學院,條件是讓其兒子進入該校學習,牛津大學在“銀行家”許諾保守秘密的前提下接受了他的資助,丑聞爆出后引發了強烈的社會輿論,記者的釣魚采訪手段同樣受到了廣泛的批評。
不過,所幸的是,經過長期的新聞實踐,媒體也逐漸形成了一套暗訪自律準則。比如,莊永志曾表示,暗訪作為一種非常規的新聞采寫手段需謹慎用之,不能僅是為了增加事件的戲劇性,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則,如在沒有其他正常的途徑和辦法收集所需要的新聞素材,或暴露記者的真實身份難以了解事件的真相等情況時方可運用。[6]《BBC制作人守則》也列出了一系列暗訪問題清單,如是否涉及犯罪或反社會行為?是否觸犯他人隱私?等等,提醒臥底暗訪一定要自我設限,需慎之又慎。[7]針對這一替考事件,南都記者參與高考的行為本身有違法理,對新聞暗訪準則也未能嚴格執行,因此,從職業法理的層面看,此次記者參與替考及其具體的新聞操作均有值得反思之處。
三、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擇取
從更深層次上說,記者臥底調查信守的新聞專業主義與媒介法理道德的矛盾,其實反映了新聞報道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觀念的沖突。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這一對二元范疇,源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實現人的某種功利服務,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 “效率理性”,持工具理性的人不看重行為本身的價值,更注重行為所達到目的的有效性;而“價值理性”強調的是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自己要達到的目的,而不管結果如何。[8]
被喻為“第四權力”的新聞媒體,因其作為社會公器的性質及關注公共領域、公共利益的特點,一般而言,在新聞活動中應崇尚價值理性的理念。但在市場化經營的環境下,有些媒體為了生存,為了經濟利益,常常遵從工具理性的價值觀,追求眼球經濟,造成新聞炒作、虛假報道泛濫成災。譬如,一些電影在新片推介中,為了博人眼球,取得轟動效應,經常斷章取義,過分渲染色情片段,制造爭議話題,引發民眾關注,進而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傳播發酵,以達到輿論推動宣傳的目的,獲取票房收入和經濟回報。
關于此次替考事件,記者選擇的調查和報道方式也暗含了工具理性的價值傾向——為了追求目的、效益的最大化,而忽略手段的合理、合法性。因為,其一,記者進行了為期幾個月的跟蹤暗訪,媒體暗訪的事件往往都是負面消息,負面新聞最具吸人眼球的功效;其次,記者已獲得大量一手資料,足以打擊替考組織,但記者不選擇考前報警和阻止事件的發生,而是親自走進考場參考;其三,在高考正在緊張嚴肅地進行的時候,媒體發了“重磅!南都記者臥底替考組織,此刻正在南昌參加高考”的文章,這一系列行為不免使人們產生媒體欲博人眼球、制造轟動新聞的嫌疑,也就無怪乎引起民眾的爭議和質疑了。
雖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各有其蘊含的價值傾向,但媒體所具有的社會職責決定了價值理性在媒介從業者心中應占的分量;記者臥底這一新聞操作方式需做到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平衡,新聞報道在追求效果最大化的同時應考慮手段的正當合理性。客觀、公正的信息是人們做出抉擇的依據,在信息時代、媒介化語境下,普通民眾多依賴新聞媒體獲取所需信息,進而做出行為選擇,這就隱含了公眾對以價值理性為基準的信息的極大渴求。然而,當前媒體面臨激烈的競爭壓力,不能不追逐經濟效益與轟動效應,從而造成了公眾信息需求與媒體報道之間的失衡,這也是江西替考事件中記者行為引起爭議的深層原因之一。
因此,一方面,媒體作為社會的瞭望者,具有監督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責,暗訪、臥底調查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和合理性,記者在暗訪過程中的“角色扮演”也有其存在的客觀因素;但另一方面,媒體在參與新聞事件、收集重要新聞素材時要把握法律的底線和倫理道德的度;同時,法律和制度也應不斷完善,厘清禁區與特區,為新聞媒體行使職責提供安全的法律保障,能讓記者在合法合理的情形下行使新聞采訪權與報道權。
總之,記者作為新聞事件的記錄者、社會正義的守望者,在促進民主進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我們依然認為,在新聞調查與報道中,臥底暗訪只宜作為一種輔助的手段,記者在此過程中也應加強法律意識和職業倫理素養,做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平衡,并在具體的新聞操作中體現人文精神,盡量避免質疑和爭議。值得欣慰的是,8月3日《南方都市報》微信公眾號以《江西替考案大學生槍手:希望得到社會原諒》為題進行了追蹤報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涉事者的人文關懷,體現了媒體的社會責任,也對媒介價值作了較圓滿的詮釋。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本文系2013年度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二五”規劃一般課題“熱點事件報道與城市形象塑造之關系研究”(13Y09)、第48批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新媒體語境下的熱點事件詞化傳播及其輿論引導研究”及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2014年度學科共建項目(GD14XXW04)“網絡語言暴力問題研究”之階段性成果
[1]張向陽.公共新聞:議程設置理論的改革性實踐[J].今傳媒,2013(2)
[2]張壘,劉旻.職業理念夠了嗎:新聞專業主義話語的另面[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3)
[3]祝興平.轉型期民謠與社會輿論評價[J].當代傳播,2002(3)
[4]陳力丹.新聞理論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5]展江.媒介專業操守:能夠建立理論框架嗎?——基于倫理與道德分殊的一種嘗試[J].南京社會科學,2010(1)
[6]莊永志:暗訪之爭,別再一次次推磨 http://www.aiwei bang.com/yuedu/30077999.html
[7]年度傳媒倫理研究課題組.2014年十大傳媒倫理問題研究報告[J].新聞記者,2015(2)
[8]王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理解韋伯的社會學思想[J].甘肅社會科學,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