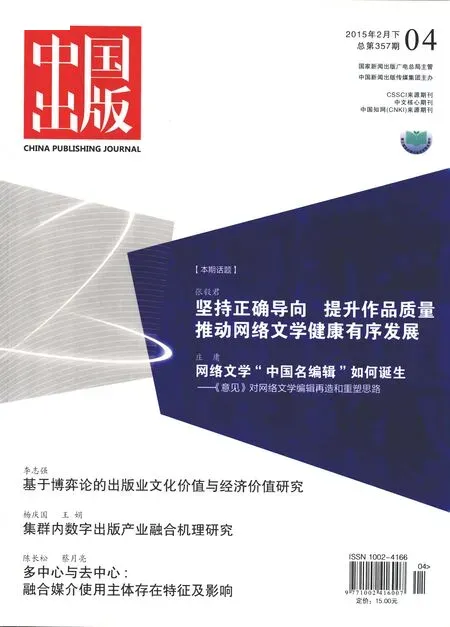多中心與去中心: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存在特征及影響*
□文│陳長松 蔡月亮
多中心與去中心: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存在特征及影響*
□文│陳長松 蔡月亮
本文在分析融合媒介的空間特性與主體自由切換概念的基礎上,討論了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呈現的多中心與去中心的存在特征,并認為這些特征對主體碎片化的閱讀行為及主體的社會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多中心 去中心 主體 融合媒介
隨著網絡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融合媒介逐漸成為業界、學界關注的焦點。作為一種新的媒介形態,融合媒介成為主導的信息傳播方式,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傳統媒介新聞產制的方式,也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可抗拒的推動作用,更徹底顛覆了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傳受關系,媒介使用主體憑借融合媒介這一“智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動傳播者。當前關于融合媒介與媒介使用主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使用主體如何利用融合媒介展開傳播活動及相關影響方面,關于其存在特征的研究則較少。本文嘗試從空間的視角對融合媒介使用主體的存在特征及影響進行討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討論的是一種趨勢,一種正在興起并有可能成為普遍性情狀的主體的存在特征,這就排除了少數絕對化的敘述。
一、融合媒介的空間特征與主體的自由切換
相較于傳統媒介的使用主體,融合媒介的使用主體可以在由融合媒介構建的各種精神空間中自由切換,這種自由切換的特性與融合媒介在物質空間、精神空間以及社會空間等三方面表現出的空間特征密切相關。
1.融合媒介的空間特性
法國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空間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將空間分為物質、精神、社會三種形式。列氏劃分的三種空間形式打破了傳統上按物質和精神對空間的二元分類,將人們對空間的認識推進到了“三元辯證法”時代。以空間理論考察融合媒介的空間特性,即是考察融合媒介在物質空間、精神空間以及社會空間等三方面的空間特征。
物質空間指以物質形式存在的空間,強調空間的物理屬性,主要表現為地域空間。所謂融合媒介的物質空間是指融合媒介存在與使用的現實地域空間。在微觀層面,融合媒介的使用空間偏向于個人私密空間。作為一種空間形態,私人空間屬于私密空間,具有封閉性、排他性和不可侵犯性。私人空間的上述特性具有延展性,其中發生的一切行為原則上也具有上述特性,這也包括融合媒介的使用。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媒介因與個體的附著關系而表現出更強的個人性、排他性與不可侵犯性。事實上,手機、iPad等融合媒介在公共場合中的使用也因公民人身自由的不可侵犯性而不可侵犯。
精神空間是指由相關意向和符號建構的意義空間,突出空間的精神屬性,主要表現為媒介的內容空間。所謂融合媒介的精神空間即是指融合媒介存載的內容空間。相較于傳統的媒介精神空間,融合媒介是一種高度開放的空間形態,其中含納了眾多不同的子空間。融合媒介興起之前,主體通常難以在不同的大眾媒介精神空間之間自由切換,更遑論同一時空中的自由切換。融合媒介興起后,融合媒介技術讓主體在同一時空中自由切換于不同的媒介精神空間,甚至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
社會空間是“由社會生產同時也生產社會的空間”,[1]突出空間的實踐特征,主要表現為媒介的實踐空間。因而融合媒介的社會空間主要是指融合媒介使用主體通過能動性實踐而生產的融合媒介社會空間,其不僅是宏觀社會空間的構成部分,也參與宏觀社會空間的生產過程。社會空間的實踐性主要通過眾多主體的主體間性予以實現。融合媒介環境下,主體可以通過不同空間的自由切換,更好地實現主體間性努力達成的文化認同,影響社會發展。
2.主體的自由切換
主體的自由切換是新媒體條件下主體在多個媒介精神空間的切入轉換狀態,這是一種自由流動狀態。這一是緣于主體的自身需要,二是新媒體技術提供了多種媒介精神空間共時態存在的可能性。
如列斐伏爾所言,“空間與自然場所的鮮明差異表現在它們并不是簡單的裝置:它們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結合、互相疊加——有時甚至互相抵觸與沖撞”。[2]然而,“疊加”“介入”“結合”等空間“膠著”樣態并不意味著傳統媒介的使用個體(受眾)可以在不同的媒介精神空間中自由切換,更不意味著使用個體能夠實現多種媒介精神空間的共時態存在。事實上,主體在不同精神空間的自由切換只有在融合媒介條件下才能實現,這是由融合媒介空間的獨特性帶來的。一方面,融合媒介具有鮮明的個人媒體的性質,與主體的關系更密切,像是人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人的延伸”功能,其使用空間具有私人空間的特點。作為媒介使用空間,私人空間的封閉性、排他性和不可侵犯性為融媒使用主體在不同媒介精神空間中的自由切換提供了“安全”保證;另一方面,融合媒介技術為媒介使用主體的自由切換提供了技術支持,基于Web3.0技術的多空間共時呈現技術以及網絡的匿名性、交互性、即時性等特點,在技術層面上為融合媒介的使用個體在不同媒介精神空間中的自由切換、實現多種精神空間的共時態存在提供了可能。
二、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多中心與去中心的存在特征
媒介使用主體的存在特征是指媒介使用主體在媒介傳播實踐中表現出的主體特征,這種特征是客觀的。相較于傳統媒介傳播實踐中主體的“穩定性”與“固定性”存在狀態,融合媒介的使用主體呈現出多中心與去中心的存在特征。
1.主體的多中心存在
傳統媒介環境下,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媒介使用主體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媒介精神空間,這種特定性賦予了媒介使用主體空間實踐行為的專注性,有助于單一主體的建構。此種條件下,主體即是唯一的一個中心。融合媒介環境下,媒介使用的情況與傳統媒介有著巨大的差異。有學者研究了手機媒介的使用,“手機屏幕將空間和時間約束進一步打破,短信和微博的流行讓人和人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被前所未有地減弱”。[3]融合媒介條件下,融媒使用主體在特定的時空中可以在多個媒介精神空間中實現共存。如果考慮到媒介精神空間與主體建構的一一對應性,那么融媒使用主體的這種多中心的共存狀態必然建構了多個主體,這就是所謂的融媒使用主體的多中心存在。
波斯特在討論印刷文化與主體建構時認為,無論是對讀者還是作者,印刷文化都傾向于將個體建構成一個有所依據的本質實體,[4]一個有著穩定和固定身份的實體。應該說,印刷文化對個體的“主體性”構建“惠及”整個傳統媒介尤其是大眾傳媒的使用主體。在傳統媒介環境下,媒介使用者的身份是相對穩定和固定的,身份的穩定與固定讓傳統媒介使用主體的媒介實踐更具專注性。隨著融合媒介的出現及成為主導的個人信息傳受媒介,波斯特所說的印刷文化“構建”的有所依據的本質實體遭到了解構,融媒使用主體的身份不再穩定和固定。
如上所述,融合媒介讓主體在同一時空中可以在異質的媒介精神空間中自由切換,不僅可以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還可以實現異質媒介精神空間的共時態存在。相較于傳統媒介環境下主體空間實踐的專注性,融合媒介主體的空間實踐在呈現多中心狀態的同時,也造成了傳統專注性空間實踐主體的“分裂”。運用融合媒介提供的新技術,媒介使用主體可以隱匿部分或全部真實身份,甚至“重造”一個或多個“身份”,在不同的媒介精神空間中自由切換。由此,主體越來越呈現出或真或假的多重“身份”,這就打破了傳統媒介使用主體身份具有的穩定性和固定性特征。
2.主體的去中心存在
如前所述,融合媒介使用主體的空間實踐呈現出多中心的特性。然而,如果我們從二律背反的角度考察這一問題,那么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在呈現多中心特性的同時,也必然呈現出去中心的特性。特定時空中,無論主體共存于多少個異質空間,融合媒介的使用主體只有一個,這是客觀事實。因此,主體在呈現多中心狀態、塑造多重身份的同時,也勢必對使用主體產生“分裂”性的影響,原本單一的主體分形為多個主體,這就是所謂的主體的去中心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媒介使用主體通過自由切換實現的多種空間的共時態存在也是遵循線性時間先后展開,但由于融合媒介多界面技術的支持,線性時間的差異可以忽略不計。應該說,融媒使用主體的這種多空間的共存狀態也必然對主體產生“分裂”性的影響。應該看到,主體的多中心存在是與身份的重塑緊密聯系的。通常情況下,不同的精神空間需要不同的身份,當主體同存于不同的異質精神空間時,主體也需要不同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應該指出的是,多空間共存的主體雖然要塑造多個身份,扮演多個角色,但是各種身份、角色之間卻不能發生沖突,必須“和諧共存”,否則就會導致主體在某個空間甚至多個空間的角色扮演失敗,交流無法維續。在共存的每個精神空間尤其是異質精神空間中,主體都需要投入“足夠”的精力與專注力,這就讓主體呈現出“一心多意”的實踐形態,這既不同于傳統媒介環境下主體“一心一意”的專注性實踐,也迥然于“三心二意”的散亂性實踐。融合媒介使用主體的這種“一心多意”的“專注性”實踐形態正是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去中心化的現實延伸。
三、產生的影響
如上所述,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在呈現多中心特征的同時,也呈現出去中心的特征,這種相反相成的存在特征必然給主體帶來長遠的影響。以下僅從傳播學的視角,就主體的閱讀行為與主體的社會化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1.深度閱讀與碎片化閱讀
閱讀不僅關涉個人的自我發展,也關系一國社會文化的發展。于個人而言,閱讀既是獲取知識的渠道,也是成為合格、健康的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對社會而言,閱讀普及率的高低意味著社會精神狀況的漲落,這也標志著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強弱。相較于淺閱讀,深度閱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深度閱讀通過促進公民的“精神發育”,來培養合格、健康的現代公民,從而推動社會的健康發展。碎片化閱讀,主要指的是對類似微博、手機這種短的內容,或者長的內容被拆散后通過零碎時間進行閱讀的一種方式。[5]盡管傳統意義上的報紙和期刊閱讀,可以歸為碎片化閱讀,但其主要是伴隨著手機、筆記本電腦等融合媒介興起的。通常認為,碎片化閱讀存在易讓主體思維分散,導致淺層次理解、難以系統思考、弱化判斷能力等弊端,這些弊端與深度閱讀追求的系統、深度與判斷力的提升是相矛盾的。本文則認為,融合媒介背景下,碎片化閱讀與深度閱讀之間的差距并沒有那么大,在一定意義上,兩者是統一的。
如前所述,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具有多中心與去中心的雙重存在特征,這種雙重存在特征在“消解”原本主體單一中心地位的同時,可以讓主體分形為更多的主體,存在于多個媒介精神空間,在每個媒介精神空間中都可以“建構”一個中心。單一主體分形為多個主體,必然對深度閱讀狀態產生影響。一方面,主體的時間、精力被分散了,打破了深度閱讀實踐的專注性;另一方面,主體的多中心塑造了主體的多重身份,破環了深度閱讀實踐建構的穩定、固定的主體身份,主體的閱讀實踐表現出碎片化的特征,這是一種“一心多意”的實踐形態,是對傳統“一心一意”的深度閱讀實踐的背離。在此意義上,碎片化閱讀與深度閱讀確實存在矛盾。然而,如上所述,“一心多意”并不是“三心二意”,主體的分形并不意味著主體的“分裂”。事實上,“一心多意”本身不僅反映出主體的能動性,也能因為意向的多向度而擴展主體閱讀的廣度和深度,這是一種“交互式”的閱讀,有利于主體的判斷力的提升。應該說,盡管碎片化閱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負面效應,但作為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我們所能做的是順應這種“一心多意”的閱讀狀態。
2.“社會化”與“宅化”
社會化是指社會個體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經由社會化將外在的社會行為規范、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標準,[6]家庭、學校、社會群體以及大眾傳媒是個人社會化過程的主要路徑。宅化,通常認為是伴隨融合媒介興起而逐漸盛行的熱衷于待在個體空間(住宅)的社會現象。應該說,自邁入現代社會,人類就變得越來越“宅”了,但是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宅化”則與融合媒介的興起有著密切的關系。雖然媒介是社會化的重要載體之一,但是通常認為走入社會、與社會發生密切的聯系是個人社會化更為重要的路徑。因此,通常認為“宅化”不利于個人的社會化。本文則認為,伴隨著融合媒介成為社會信息傳受的主導媒介,“宅化”開啟了異質主體間相互了解和認同的可能性,更有利于實現個人的社會化。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宅化”具有追求個人感受和獨立的象征意義,并不包含消極被動的“家里蹲”等“偽宅”行為。
傳統媒介環境下,主流社會空間與邊緣社會空間之間的“區隔”是分明的。只有為主流群體所承認的社會空間才能成為主流社會空間,獲得公開表達的機會;邊緣社會空間則因主流群體的排斥而以隱性的失語狀態存在。應該看到,媒介話語和空間的生產關聯密切,“空間被列為生產力與生產資料,列為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特別是其再生產的一部分”。[7]主流社會空間和邊緣社會空間的話語區隔直接帶來兩種后果:一是絕大多數社會主體生活在主流社會空間中,少有機會接觸邊緣社會空間,甚至不同的邊緣社會空間之間也少有接觸;二是出于安全的考量,邊緣社會空間中的個體藏匿、放棄某些身份,被動接受主流社會空間的“型塑”與“規誡”。上述兩種后果均給不同社會主體尤其是異質社會群體間的“認同”設置了障礙。融合媒介則打破了這些障礙,其使用主體在多個空間的共時態存在突破了傳統媒介環境下媒介使用者存在空間的單一中心狀態,主體由此呈現出多中心的樣態。運用融合媒介技術,不同的個體、群體不僅可以通過自由切換進入不同的話語空間,也可以根據需要創造一個屬于自身的話語空間,傳統媒介環境下不同話語空間的“區隔”逐漸弱化,這就為社會主體尤其是異質主體間的接觸和了解帶來了可能。因此,融合媒介在促進不同群體、不同主體以及主體與群體間相互認同上具備更大的可能性,進而能夠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通過主體間、群體間的意義交流、分享與互動,使得不同主體能夠認同統一規范、準則,并且被主體內化為自我的選擇,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融合媒介環境下,“宅化”能夠使異質主體間相互了解,創造了更多的認同的可能性,也有利于實現個人的社會化。
融合媒介使用主體呈現出多中心與去中心出存在特征,這種特征雖然造成了主體的碎片化閱讀及“宅化”行為,但這些行為與傳統的深度閱讀實踐與個體的社會化并不矛盾,根本上,它們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以主體的自由發展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
(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
[1]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2][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M].Oxford:Blackwell,1991.轉引自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3]姜浩.四種屏幕:傳播媒介的空間特性[J].現代傳播,2011(12)
[4][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姜煒宏.警惕,碎片化閱讀[EB/OL].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lg/rpzm/wh/201204/t20120423_153152.htm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7]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融合媒介的空間特性與新聞影響力生成擴散研究”(12YJC860002)和淮陰師范學院青年優秀人才支持計劃(11HAQNZ1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