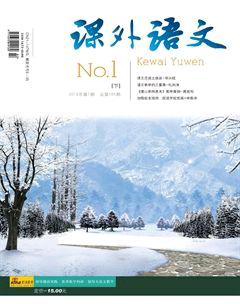淺論易安詞的藝術形象及表現手法
李小青
【摘要】易安詞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詞壇上具有獨特的意義,而且具有形象的完整性,性格的鮮明性,從她塑造的形象來看,反映了人物的成長歷程,從天真、活潑、聰慧而又帶著羞澀的少女形象到至誠至癡、情真意切的少婦少妻,以致國破家離后的孤寡老人,镕鑄了詞人一生的悲歡哀樂,讓讀者體悟到一個閉鎖社會結構下一個孤苦的旅人的悲苦和不幸,我們從中體會到的是她所塑造的形象的典型意義和當代社會的人生哲思。其詞作語言高度洗練,在發掘生活中富有詩意的情感場景后,從口語中挑選最準確、最生動的語言來表達,所以能夠在平易中顯現功力,于淺近中顯現精美。這對塑造完整、個性鮮明的抒情形象至為重要。
【關鍵詞】易安詞;藝術形象;表現手法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A
回望中國古代詩歌藝術長廊,我們不難發現,李清照是唯一一位與詩歌廝守終生的獨具藝術魅力的女性詩人。她個體生命的存在,她的生命活動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她的詩歌——詞。簾卷西風,詞香滿袖。那“西風”,吹過近千年依然颯颯作聲,那詞香依然清淡而雋永。李清照和她的詞,在漫漫詩歌歷史上,不僅具有文學史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其文學本身的價值,她在詞的領域中持之以恒的女性寫作,給后人留下了一筆藝術珍品和寶貴的藝術財富,為漢語詩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這里,從形象塑造和表現手法兩個方面對易安詞做些粗淺的探討。
一、李清照詞的女性形象
李清照所塑造的生動鮮明的女性抒情主體形象,在詞壇上具有獨特的意義。女性形象在詞中出現,不乏其例。隨著女詞人人生經歷的發展變化,李清照塑造了三類各具情致而又相互拈連的抒情主體的形象。
第一類是天真、活潑、聰慧而又帶著羞澀的少女形象。典型的詞作有那首膾炙人口的《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這里描寫的是一群少女,是少女的群象,在風光秀麗的湖光水影的背景上,十分開朗,十分歡快,而又頗為頑皮。這些少女不同于那種受封建禮教束縛,行不露足,笑不露齒的豪族閨秀。她們熱情奔放,而又憨態可掬,自有其天然情態,自然風韻。毫無疑問,女詞人必然是這一群體中最為活躍的一個。
第二類女性形象較之第一類,則脫去了憨態稚氣,而變得篤于情,摯于愛,活靈活現為血肉豐滿的少婦形象。她與丈夫趙明誠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婚后生活甜蜜美滿,但卻因丈夫常常赴別處他方,釀成情感上的相思之苦。李清照在許多首詞中,把自己熱烈、真摯的愛情和深深的相思之苦抒寫得淋漓盡致。
比如她與丈夫婚后不久離別時新作的《一剪梅》。詞中回憶與朋友分別時的情景,何其逼真,描繪餞別時難過的心情和恍惚的情態,何其生動;而依依惜別時所道的那一聲珍重,所留的那一份眷戀,所給予的那一種祝福,又是何其感人!女詞人珍視友情,渴望友誼天長地久。
李清照詞的第三類女性形象,以飽經憂患、多愁善感和深懷故國之思為特點。靖康之難使李清照的生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國家的不幸往往給個人帶來更大的不幸。金人的鐵騎蹂躪了她的家鄉,戰火紛飛中,他們夫婦一生珍愛的金石書畫化為灰燼,她又罹遭亡夫的心靈重創,自此孑然一身,漂泊江浙,備受卑鄙小人的欺凌。山河破碎,人生多舛,人心潛隱的猙獰盡露,往日的情懷,曾經的歡樂,一切都煙消云散,襲入詞人心肺的是亡國之恨,身世之悲,使她南渡以后的詞作格調變得凄惻哀婉,煞是悲愴。那是一首催人淚下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寫盡了多少郁結于胸的憂愁和刻骨銘心的創痛,整首詩把作者晚景的凄涼、愁苦展現得栩栩如生。一首《永遇樂》則把家國淪喪后的悲戚描述得更為真切。
在這首詩里,抒情主人公沒有了少女的歡快,也失去了少女的寧靜,哪怕在元宵佳節融和的天氣里,也擔心風雨降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故,不但心思厚重,而且心存余悸,華燈笑語之間,她所滋生的只有流亡的悵惘和失國喪家的切膚之痛,只有對國難當頭卻依舊終夜喧闐的不知忘國之恨的人們的憎惡。
李清照詞作塑造的三類形象各自具有因年貌不同和生活內容、生活閱歷不同而帶來的鮮明性格特征,但把這三類形象連貫起來,更是一個鮮活的女性人生的動態寫照,是知識女性心路歷程的真實再現,只有李清照式的端莊與沉穩,不似溫庭筠只狀女子之貌而未表女子的心跡,也不似柳永筆下女子的庸俗和輕浮,所以別具典型意義。
二、李清照詞塑造形象的藝術手法
李清照是中國詩歌史上的抒情大家,她非常善于捕捉稍縱即逝的生活場景和真切感受,醞釀成詩意醇厚的主題,同時在表現手法上自出機杼,奇思連綿,新意不斷。
她善于通過塑造生動的抒情形象展示和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眾所熟知的《醉花陰》一詞寫道:
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全詞塑造了一個在重陽節思念情人的癡心女子形象.詞作者抓住主人公因思戀而消瘦這一特點,創造性地運用了“人比黃花瘦”這樣的形象,突出了抒情形象的特征,把一個傳統的主題表達得十分新穎優美。她沒有抽象地寫孤寂、相思的痛苦,不直接寫面容的憔悴,只與黃花類比,一個“瘦”字傳神,以瘦削的形象曲折含蓄地寫出思念之深切,手法奇特而高妙。
李清照善于運用通感手法,移情于物,化抽象為具象。例如,在她的詞作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愁”字,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經她藝術處理,可以有長度:“從今更添一段新愁”;可以有濃度:“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可以有形體:“獨抱濃愁無好夢”……
她對對比手法的運用更是爐火純青。短短一首《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處,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以對話的形式,塑造兩個相互對照的形象:卷簾人天真單純,看不出海棠的變化,問話人卻惜春傷春,一句“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感嘆,從對時光流逝的敏感中透露了對沉悶生活的艾怨,兩相對比,抒情形象的特征更加完整而鮮明。
在運用烘托、襯托手法上,李清照更是技高一籌,獨具特色。這里,不單作詳細分析。
(編輯:龍賢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