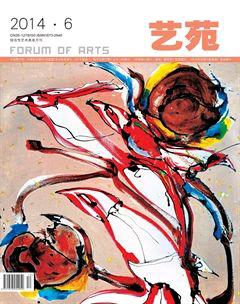清代學者之于“笛上三調”、“清商三調”研究
成軍
【摘要】 荀勖“笛上三調”理論曾引起清代學者的興趣。胡彥升、徐養原、凌廷堪以及陳澧等諸位知名學者,均認為“笛上三調”當指三種調高。徐養原把荀勖“笛上三調”之“清角”調追溯到《韓非子·十過》中的“清角”調。凌廷堪更是將“笛上三調”對應于“清商三調”,認為正聲(黃鐘)調為清商三調之“清調”,下徵調為“平調”,清角調為“瑟調”。
【關鍵詞】 清代學者;“笛上三調”;“清商三調”;三種調高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荀勖“笛上三調”理論較為完整的保存在《宋書》、《晉書》“律歷志”中。據《隋書·音樂志》“開皇樂議”記載,至隋代,“笛上三調”以及古琴上旋宮的“清商三調”理論對于當朝的一些音樂行家來說,已經成為迷惑不解的一大難題。至清代,“三調”理論日趨備受漢族學士的關注,他們引經據典,著書立說,形成了荀勖“笛上三調”以及魏晉“清商三調”理論研究的熱點。當然,這種學術氛圍是與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緊密相關的。
清朝是我國又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政權。為了鞏固統治地位,清朝統治者政治上推行“剃發易服”,軍事上嚴厲打擊農民政權以及明庭殘余勢力,文化上則大興“文字獄”,并對懷有高尚民族氣節的漢族學士進行殘酷的鎮壓。諸多文人學者為了保身避害,埋頭于書桌案前,讀書寫文章成為日常生活之要事,并逐漸形成以“考據”為特點的樸素學風,學界多稱之為“樸學”。胡彥升就是清代較早研究經學的漢族學士之一,之后“乾嘉學派”又把古代“樸學”發展到頂峰。在“乾嘉學派”(1)“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術傳統的基礎上,荀勖“笛上三調”以及魏晉“清商三調”理論逐漸引起清代學者的興趣,徐養原、凌延堪以及陳澧等諸位學者相繼加入學術論爭的隊伍,并發表了一些極有創建意義的學術觀點。
關于荀勖“笛上三調”之性質問題的研究,清代胡彥升(2)先生就尤為關注。他首先將“三調”解為三種調高。其《樂律表微》曰:
晉御府所藏笛律,即荀勖笛譜所本,十二笛即十二調也。但列和言漢魏相傳,但有“三尺二”、“二尺九”等名,則笛之據宮稱調自勖譜始……所言下徵、清角,特旋宮之二調耳,十二笛皆有之。然黃鐘笛為徵角正聲,故可用;余笛非正聲,故不可用。古人言下徵、清角,專言黃鐘之下徵、清角也。二調所假用之律,雖皆濁一律,在笛則七聲流轉循環,自然互相為用,不必“并發三孔”及“哨吹令清也”。(3)
荀勖制作十二律笛以吹奏十二個調高,胡彥升卻并不贊賞。胡氏認為一個笛孔可吹二律,一支笛子即可吹奏七個調高,二支笛子即可吹奏十二個調高,這就是胡氏“二笛十二調”理論。一支笛子采用不同的吹奏技術的確可以吹奏出一個八度內的十二個半音(十二律高),但在藝術實踐當中,應用非常困難。且不說演奏技術問題而單就笛孔音位變化而言,樂工難于記憶,快速的樂曲更是難以把握。不過,從胡氏“二笛十二調”笛譜以及“下徵、清角,特旋宮之二調”來看,胡氏是把荀勖“笛上三調”認作三種調高的。
徐養原依據沈約《宋書》“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像”記載,認為《宋書》記載荀勖笛律理論時,原本附有笛像(笛譜圖),其后亡佚。據此,徐氏依《宋書》記載以及自己的藝術經驗為荀勖律笛繪制了圖像并作了注解,故書曰《荀勖笛律圖注》。(4)徐氏認為,“旋宮之妙在十二律循環絡繹,一氣相生”,若只用兩笛則“不見旋宮之妙”。荀勖當是依古法制作十二律笛,“十二笛,笛當一律”,即一笛一調。可見,徐氏并不贊成胡彥升“二笛”應“十二調”之理。在論及“笛上三調”時,徐氏不僅認為“笛上三調”當指“三宮”,而且認為荀勖“十二笛”“各有三宮,共三十六宮”,黃鐘宮是其統率。此外,徐氏還論及了“清商三調”理論。徐氏說:“笛雖七孔,只用三宮,余四宮無施于樂,故不用。相和有三調(筆者按:實為清商三調),當別是一義,與此不同。就三宮論之,‘清角不合雅樂,故荀氏于十二笛惟言正聲、下徵所應之律,而不及清角;然韓子曰:‘清徵不如清角。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清角雖非雅音,去雅未遠,故得列于三宮歟。”在徐氏看來,荀勖“笛上三調”乃與相和三調有所不同,就三宮(三調)來說,均有“清角”調,并把“清角”調追溯到《韓非子·十過》中師涓、師曠等人在古琴上表演的清商三調之“清角”調。不過,在徐氏看來,“清角”調不合雅樂,與《宋書》“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的觀點是一致的。
“乾嘉學派”知名學者凌廷堪(5)在解讀與匡謬荀勖笛律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笛上三調”理論。凌廷堪在《晉泰始笛律匡謬》一文中云:
隋以前多不以律呂名調,故隋平陳得清樂三調,但曰“平調”、“清調”、“瑟調”而已。三調者,乃周房中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因列和所言,尚可略考見漢魏之制。又荀勖所制笛,有“正聲調”、“下徵調”、“清角調”,疑亦因三調而附會者。蓋漢魏以來,只用三調也。《隋書·音樂志》:何妥曰:“近代書記(籍)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此其明徵也……荀勖“三宮”,疑即漢魏以來之清商三調。正聲者,清調也;下徵者,平調也;清角者,瑟調也。勖未必能前無所因而創此三調也。以燕樂考之,當有七宮,而漢魏相傳只有三調。故知勖之三宮,即三調也。然勖笛尺久廢,清商三調又失傳,不可臆度,書此以俟知者。(6)
凌廷堪在談到荀勖“笛上三調”時說,荀勖“三宮”疑即漢魏以來之“清商三調”。凌廷堪直接把三調稱之為“三宮”,可見,凌氏認為荀勖“笛上三調”以及漢魏以來的“清商三調”均是指三個調高。不僅如此,他還將“笛上三調”對應于“清商三調”:正聲黃鐘為清調,下徵為平調,清角為瑟調。可見,在今天看來,凌氏這一觀點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學者陳澧(7)《聲律通考》專設《晉十二笛一笛三調考》一節對荀勖“笛上三調”理論進行考釋。和以往胡彥升、徐養原以及凌廷堪研究鮮有不同,陳澧除繼承“考據”之學術傳統外,還依據相關典籍確定晉代黃鐘律管的長度,進而復制了晉代荀勖十二律笛。關于如何復制,《聲律通考》曰:“荀勖創為應律之笛,史載其制,分厘畢具,古書言樂器未有如此之詳備者。余取宋王厚之《鐘鼎款識》,冊內晉前尺,即荀勖律尺。《隋書律歷志》云荀勖律尺為晉前尺。截竹仿造十二笛,使西晉之音復存于今日,誠快事也。荀勖笛制,文義間有隱晦,今為圖表于(左)下,復詳釋之。庶后之讀史者皆能仿造矣。”(8)從陳澧復制十二支笛子的笛譜來看,每笛均有“三宮”,即正聲調、下徵調、清角調。可見,陳澧也是把荀勖“笛上三調”看成三種調高的。不過,陳澧仿制的笛子,每笛均標注“三調”,十二笛共“三十六調”。理論上,“三十六調”固然可以成立,但在實踐之中,每一類樂器最多用全十二個調。因此,陳澧“十二笛”之“三十六調”并無多大應用價值。筆者認為,荀勖要在黃鐘之一笛上吹奏三個調高,僅僅是應“清商三調”表演之需要。
據上分析,清代學者關于荀勖“笛上三調”理論研究,盡管在某些細節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就“笛上三調”之性質而言,得出的結論認識大體相同,即“笛上三調”是指三個調高。不僅如此,清代學者已經開始探究“笛上三調”“清商三調”二者之關系。他們全心鉆研均是為了逼近歷史真相,無論觀點對錯與否,對于今人研究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或啟迪價值。因此,他們應有的學術地位值得被尊重和和肯定!
注釋:
(1)乾嘉學派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經史學、文字學、金石學。他們收集整理文獻、考證源流發展和辨析史實根據。許多重要古籍,經過他們旁征博引的考證辨析,較為清晰的展現了古代文獻的本來面目,為后人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文獻史料。乾嘉學派代表性成果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讀書雜志》、郝懿行《爾雅義疏》、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凌廷堪《燕樂考原》、阮元《十三經注疏》及其《經籍纂詁》等,在他們研究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音樂方面的內容,是我們今人研究古代音樂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輯佚文獻也有較大收獲,如王謨《漢魏遺書鈔》、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等。
(2)胡彥升,大清雍正八年進士,著名經學家,著有《樂律表微》八卷留存。
(3)胡彥升《樂律表微》,乾隆耆學齋刊本。
(4)徐養原(1758-1825),浙江德清人,除注釋儒家經典著作之外,另有《管色考》、《律呂臆說》等音樂專著。
(5)凌廷堪(1755-1809),乾隆年間進士,著名的經學家、音樂家,也是《四庫全書》的重要編纂者之一。
(6)凌廷堪《晉泰始笛律匡謬》,貴池劉氏校勘本。
(7)陳澧(1810-1882),晚晴著名學者,重要著述有《聲律通考》、《漢儒通義》、《琴譜集》、《簫譜》等。
(8)參見陳澧《聲律通考》(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