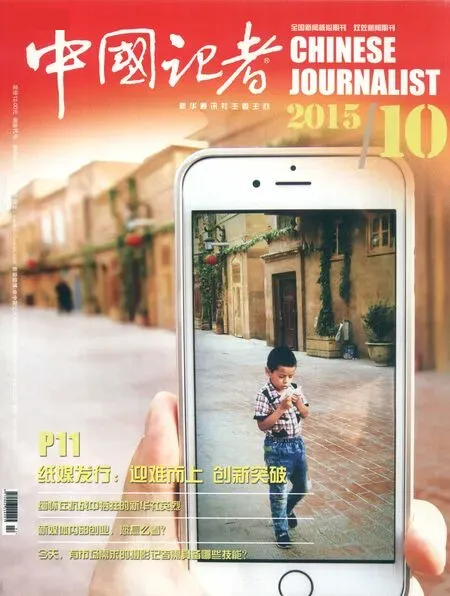紀念報道如何書寫歷史
——品評《悲壯的起點,不屈的抗爭——1931-1937年局部抗戰啟示錄》
□ 文/陳文舉
紀念報道如何書寫歷史
——品評《悲壯的起點,不屈的抗爭——1931-1937年局部抗戰啟示錄》
□ 文/陳文舉
在眾多抗戰題材的新聞報道中,標志著抗戰全面爆發的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歷史,得到媒體較多的著墨。而1931—1937年這段可歌可泣的6年局部抗戰史稍顯沉寂和單薄,這不僅體現在歷史學界的研究分水嶺,而且在相關的新聞報道中表現尤為明顯。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到來前,新華社組織記者奔赴東北三省、河北、內蒙古、上海等地,尋訪1931-1937年發生在中華大地的那段抗爭史,遍訪堅守14年抗戰的抗聯足跡、江橋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舊址及英雄家屬后裔、研究學者專家,采寫了重頭文章《悲壯的起點,不屈的抗爭——1931—1937年局部抗戰啟示錄》(后文簡稱“《啟示錄》”),于2015年8月10日播發。在短時間內被全國各大新聞媒體、客戶端,微博、微信等廣為轉載和傳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特殊種類,紀念報道絕不僅僅是重溫歷史,緬懷歷史,相比較而言,思想性、可讀性、啟示性應成為衡量報道質量的重中之重。《啟示錄》一文相對不少紀念報道而言,較好地實現了上述目的和要求。
主題與歷史
《啟示錄》這篇通訊選題的價值和意義,從這段歷史較少出現在大眾視野就體現出來。除了紀念“九一八事變”之外,包括東北抗聯在內的英勇抗爭的這段局部抗戰史涉及太少,這固然與之前強調“8年抗戰”的史學論證有關,也與這段歷史是“恥辱的開始”“未放一槍一炮”的認識誤差有關,因這段歷史長期以來容易被忽略或被遮蔽,也讓該文在史料的敘事中占得先機。

紀念報道的價值在于追溯歷史,觀照現實,啟迪未來。要實現這一目標,主題的開掘是報道成功的基礎。在主題的開掘上,《啟示錄》從中國人民奮起抗爭的起點、拉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序幕的高度謀篇布局,將落腳點放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生死攸關之際,作為重要力量肩負起民族的重任,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在東北獨立領導抗日力量發揮主導作用等重大歷史史料上,從而揭示民眾覺醒的悲壯歷程,從血與火的淬煉中誕生的偉大的抗戰精神,以及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魂所在。
主題與歷史的咬合則是還原現場的最佳手段。文章以歷史回溯、縱橫交織的方式,分“這個戰爭,從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義勇軍領袖都是共產黨員”“這塊土地是我們的”三大板塊展開敘述,彰顯了局部抗戰對于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意義、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先鋒性作用和同胞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的堅定捍衛,既有對抗戰歷史的打撈和挖掘,又有重點的突出,且以愛國熱情為貫穿其中的紐帶,將全文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通篇讀來,給人以一氣呵成、意猶未盡之感。在梳理和集成豐富歷史材料的基礎上,文章以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較為詳盡地展示了東北軍駐北大營620團的第一槍、遼西抗日義勇軍、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東北抗日聯軍的創建、“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爆發,直至最終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新聞事實的過程,并進行多側面、多角度的分析解讀,其價值顯然與傳遞單一信息的體裁不可同日而語,加深了讀者對1931-1937年局部抗戰的全方位了解。
與此同時,記者用凝重的筆觸、客觀的形式對抗戰的悲壯過程進行分析解釋,從而進一步擴展和深化了報道的內容。報道沒有停留于對史實的重復陳述,而是以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對大量的、復雜的新聞素材進行分析、歸納、梳理、加工,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個復雜、壯闊的歷史場景,以穿針引線的文字探尋和解釋歷史的歸因,并將之與民族復興的夢想相勾連:“一個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籍由無數悲壯的犧牲,從這里浴火重生。”
宏大歷史與細節表達
抗戰全面爆發前的6年,波瀾壯闊,充滿了不屈的抗爭和殘酷的犧牲,非一篇短文可以盡述。作者在充分掌握歷史和現實材料的基礎上,精心挑選有代表性、極富感染力的歷史細節,以不長的篇幅,勾勒出抗日戰爭的宏大畫卷,提綱契領地點出局部抗戰對全面抗戰的精神孕育作用,可謂四兩撥千斤。
歷史細節的象征表達,照進現實。在強敵入侵、民族危難之際,中國的抗日戰爭從“悲壯的起點”開始。記者選取了一個典型細節,既是歷史事實,又在冥冥之中隱含著巧合與象征:“東北軍駐北大營620團團長王鐵漢接到了‘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后,忍無可忍,違令阻擊,持槍殺出一條血路。”正如王鐵漢最終“殺出一條血路”一樣,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經歷了14年艱苦卓絕的戰斗之后,換來了最終的勝利。“落敗的北大營舊址定格了那個恥辱的夜晚,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依舊肅穆莊嚴,兩地相距還不足5公里。”——“它們是中國抗日戰爭真正的起點和極富象征意義的終點。”
又如,在展現“不屈的抗爭”時,作者采取了欲抑先揚凸顯細節的手法。先看今天的東北大地,“山川競秀,沃野千里。冬天,是滑雪愛好者的樂園。夏日,是民眾消暑勝地。”隨即將鏡頭閃回到80多年前抗聯老戰士周淑玲和黃殿軍充滿細節的回憶:“環境異常艱苦,只能靠野菜、樹皮、草根充饑,被圍困的時候一根蘿卜堅持一個禮拜。有時候吃不上飯,只能喝尿。”“餓得皮包骨,我們還是堅持與日偽軍頻繁作戰,餓死、凍死和戰死者不計其數。”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穿插對照,是為了讓我們這些后人銘記歷史,勿忘先烈:為挽救國難的抗日將士們挑戰人類生存極限的方式是何等慘烈!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多么的來之不易,中國共產黨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犧牲!
細節中的人物凸顯歷史的宏大力量。歷史不僅是由史實構成,更是由人構成,由那些走在時代前列、體現時代精神的英雄所書寫、所構筑。因此,報道事實,要通過的人的行動來體現。對人物的細節化表達,更勾畫出這幅歷史畫卷的悲壯、凄美。習近平總書記9月2日在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儀式上說,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包括抗戰英雄在內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在記者的筆下,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人物們從歷史的畫卷中走出來,走到我們的面前,鮮活立體,毫發畢現。
孫銘武的昂首陳情、陳翰章的父子“反目”、趙尚志之父的沉郁堅韌、馬占山將軍的拍案而起……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鮮活的、充滿血性的、大寫的人,正是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構筑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史,而這些遠去的歷史事實因“人”而生動,因“人”的可歌可泣而具有永恒的價值。
當年涌動在白山黑水間不屈的信念,通過這些英雄個體的言行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在全家30余人作為“反滿抗屬”被追捕,房屋地產全部被沒收的情況下,孫銘武昂首陳情:“國破家亡,有產何用,倘東北有光復之一日,詎患其沒收耶!”言辭慷慨,大義凜然,國難當頭毀家紓難、決不放棄抵抗的神情躍然紙上,給人以極大的感染。
抗聯英雄趙尚志之父在作者短短的白描中,沉郁堅韌,予人以極大的震撼。趙父得知其子死訊后沒有落淚,平靜地對家人說:“我死后,在我墳前戳個板兒,上面寫上‘趙尚志之父’五個字足矣。”
思想的敘事與議論
體現思想性,需要正確處理紀念報道的敘事與議論,這是本文另一個成功的實踐表達。作者洞幽燭微,以旁觀者的身份客觀敘述,但歷史的啟示力透紙背,從豐富和悲壯的史實中生發出拳拳的憂國之心、愛國之情。這是通過夾敘夾議的文字娓娓道出的結果。這些文字既是新聞報道本身,同時又超出了一般的報道而具有了歷史的意義,超越于一時一地的價值而具有了歷時性的內涵和力量。
突出史料的思想性。該文不僅僅有緊湊的結構、流暢的語言,更為突出的是以史實和思想取勝。作者將自己的思想寓于恰到好處的議論中,善于用議論作過渡,讓議論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既使文章銜接自然,又增加了文章的深度。在回顧了東北抗戰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東北14年抗戰中,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將領獻出了生命”“僅在1931年到1937年間,抗聯殲敵就達10.35萬人”后,記者從中引發的議論自然而然卻驚人猛醒,如“局部戰場的抗戰,犧牲慘烈、何其悲壯!”“84年滄桑,歷史在冥冥中總有些巧合,昭示出正義的真諦。”
基于歷史的敘議交融。這篇報道寓議于敘,不露痕跡,使人難以區分哪些段落是敘,哪些段落是議,體現了作者高超的表現技巧。如“為了這塊土地,為了最后的勝利,無數英魂長眠在白山黑水,長城內外。”“無數的犧牲換來了最終的勝利。”回望歷史后平實的敘述,充滿了悲壯之情和難平之緒,作者的議論也與敘述一起,成為水乳交融的整體,不可分割。
在報道的最后部分,作者以歷史的啟示作結:“回首那悲壯的6年,那些在抗爭中孕育出的偉大抗戰精神,起自民眾的覺醒,化成民族的意志。四萬萬同胞在她的先進分子帶領下,英勇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的滾滾洪流。歷史無言,精神不朽。”寥寥數語,將6年局部抗戰的最重要意義點出,有烘云托月之效果。而這些議論之所以精彩,是因為記者寫出了自己獨到深刻的見解,且用如此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來,達到了“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筆下之所無”的境界。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新聞中心;報道原文載于2015年8月1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時的標題為《1931-1937:局部抗戰啟示錄》)
編 輯 張 壘 leizhangbo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