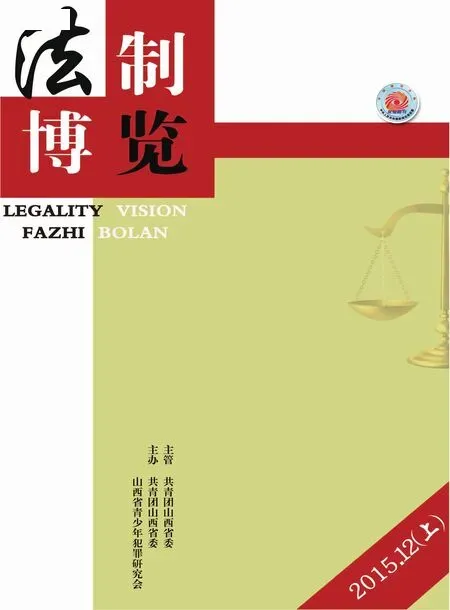西寧市城東區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調研報告
西寧市城東區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調研報告
張浩
青海民族大學法學院,青海西寧810007

摘要:通過對城東區法院的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判決現狀進行調研,發現問題,并對社會熱點問題諸如“民間偏方”以及青海地區民眾對于藏藥的看法等進行調研。然后對調研的結果進行分析,對調研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建議,進而從細化認定標準、刑事和行政處罰等方面完善生產、銷售假藥罪。
關鍵詞:假藥;偏方;藏藥
中圖分類號:D924.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5)34-0080-02
作者簡介:張浩(1990-),男,安徽阜陽人,青海民族大學2013級法律碩士,研究方向:刑法學。

藥品安全直接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必須被法律規制的領域。然而近年來藥品安全領域頻發的問題、惡劣的影響以及嚴重的后果都對刑法規制能力提出嚴峻挑戰。《刑八》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門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一些新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規定。筆者調查西寧市城東區法院辦理生產、銷售假藥犯罪案件的情況,綜合分析新出現的情形。最后對調查中所出現的問題提出完善建議。
一、西寧市城東區法院辦理的生產、銷售假藥犯罪案件的情況
由圖1可以看出,西寧市城東區法院辦理本罪的案件相較于2014年同比增長200%。筆者在同城東區法院的工作人員和西寧市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交流后得知,在生產、銷售假藥罪的裁判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
(一)鑒定意見公信力不足
西寧市城東區法院通常把假藥認定的決定權交由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認定,由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出具假藥的鑒定意見。但是對假藥的鑒定過程中存在以下的問題:第一,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作為行政執法機關來鑒定“假藥”,這使得其鑒定意見的中立性沒那么牢靠。第二,在西寧市城東區法院辦理的案件中,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出具的鑒定意見中,對于假藥的認定,基本上都是依據“有未獲得批準文號、依法應批準而未得到批準銷售”這項原因來認定。這使得鑒定意見沒有一套完整的,客觀的體系和標準來遵循,受鑒定人主觀因素影響較大。
(二)新出現的現象按傳統方式認定、處罰
西寧市城東區法院于2014年所裁判的“南某生產、銷售假藥罪”一案中,南某所生產和銷售的藥品是真的,是用藏藥材加工而成的。雖然南某本人不是醫生,也沒有取得醫師資格證。但是其所生產的藏藥是按照老藏醫提供的藏藥傳統處方,用傳統工藝制成的。他生產的藥品沒有獲得批準文號,所以鑒定機構直接認定為假藥,法院根據該鑒定意見作出了有罪判決。此類最新出現的情形“民間偏方”算不算假藥,也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二、細化刑法上“假藥”的認定標準
(一)“藥品”范圍
保障性是刑法的根本特性。[1]從調整內容來看,藥品管理法重心在于規范秩序,而刑法重心在于打擊不法。從規制的手段來看,其他部門法不具有極端嚴厲性和最后保障性,而刑法依法被賦予這項特權。
從刑法角度看,《藥品管理法》中所規定的“藥品”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藥品,刑法規制手段的終極性決定刑法只關注那些最不能容忍的、應當處以刑罰的行為。[2]所以,應對本罪中的“藥品”進行限縮解釋,其范圍應小于藥品管理法中“藥品”的范圍。
(二)嚴格刑法上“藥品”的認定標準
刑法直接采用藥品管理法對藥品的定義,導致了刑法上“藥品”范圍的擴大,進而導致了不好的社會效果。筆者認為,應該限縮藥品范圍,只對該處以刑罰的行為予以規制。一方面,建議將中藥材、藏藥材等從刑法規制的“藥品”中排除出去。[3]中藥能有效的治療疾病,并且其幾千年的應用也使得中國人能夠接受,但是中藥只是人類對動植物等物質進行的加工,而有些藥方甚至需要不經任何加工的原料入藥。在我國嚴格藥品準入的前提下,不可能所有中藥都有批準文號。[4]所以刑法意義上的藥品認定應更為嚴格,并且要與藥品管理法不同。另一方面,應有真藥的標準來對應假藥,使得假藥更容易認定。藥品管理法把假藥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質上的“假藥”,即藥品成份不符合標準規定。另一類是形式上的“假藥”,如:未取得批準文號的原料藥生產的。兩類假藥的認定都是要有與“真藥”相對應的國家藥品質量標準。[5]這樣細化刑法意義上的“假藥”的范圍和認定標準以后,就能夠避免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僅僅依照“未取得生產批號”等原因作出鑒定意見。[6]而是參照藥品外形、功效等等綜合作出實際上應該有的、客觀的鑒定意見。這樣就勢必要求我國藥品標準體系的完善,只有經過實際上的檢驗,以及對比標準之后得出的鑒定意見才具有公信力。
三、民間偏方應視情況來處罰
藏藥在我國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通過長期在青海等地區的實踐,形成了被當地人所接受的醫藥體系。其理論基礎也很深厚,是我國比較完整的民族藥。西寧市城東區人民法院2014年所判的關于南某生產、銷售假藥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南某及其妻子錄某某自2012年4月起做藏藥材生意,2013年5月南某租賃倉庫房九間,在未經食品藥品監督局批準、未取得生產藥品許可證及生產批號下,雇傭其侄子被告人索某某某在租賃的倉庫房內生產藏藥藥丸。被告人索某某某按照被告人南某提供的藥單生產、加工藏藥藥丸,加工后的藥丸由被告人錄某某負責零散銷售和批發藥丸。而此藥單是由一個熟知藏藥的藏醫提供的。藥材是正規渠道采購的,藥方也是由老藏醫提供的。那么這種藥材是否應僅僅根據“未取得生產批號”就被鑒定為假藥。城東區法院2013年“馬某某生產、銷售假藥罪”也是根據西寧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出具的的鑒定意見作出了有罪判決。在這個案子中,馬某某的部分藥品也是根據民間偏方制作出來的,而且他所售賣的藥丸并沒有造成購買者的病情更為嚴重。雖然不確定他所售賣的藥丸是否具有應有的作用,但是在筆者看來,這樣是有失偏頗的。從情理的角度來看,民間偏方以及藏藥等雖然存在著不規范性和不確定性,但大都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且覆蓋了一定的區域及民眾。如果想要用法律取締這種傳統醫學是不現實的,對所有這樣的“醫生”進行處罰也是不現實的。從法理的角度來看,偏方,藏藥大部分都是沒有批準文號的,因此不宜用“未取得批準文號”作為認定假藥的標準。[7]另外盡管缺乏對所有偏方及藏藥的一個權威認定,很多偏方的效用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對于有些經過批準的藥品不能治好的病,偏方甚至能起到一個很好的作用。這樣缺乏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用《刑法》來規制,不能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也不能罪責刑相適應。
筆者通過對本地區發放的一百份問卷綜合分析情況如下:100份案卷中50份是藏族人填寫的,50份是其他民族填寫的。對于生病時會選擇藏藥、中藥還是西藥,94%的藏族人會選擇藏藥,8%的其他民族的人會選擇藏藥。綜合得知,本地區51%的人會選擇藏藥。80%的人吃過藏藥。在問及購買藏藥藥丸的地方時,80%的人在醫院購買過;72%的人在診所購買過;51%的人在私人處購買過。而吃過藏藥的人中,100%的人知道所吃的藏藥藥丸是藥品。對于所吃的藏藥有未達到治療效果,47%的人認為達到效果了;13%的人認為沒達到效果;20%的人表示不清楚。對于“有無吃過藏藥反而使病情加重的情形或聽說過此類情形”6%的人表示聽說過;94%的人表示沒聽說過。對于“購買的藏藥藥丸包裝上是否有生產批號、日期”28%的人表示只買過包裝上有生產批號和日期的,52%的人表示買過包裝上沒有批號、日期的,20%的人表示兩種都買過;對于“若買藏藥的店老板因賣藏藥被判刑能否接受”這個問題,92%的人表示不能接受;6%的人表示能接受;2%的人表示不清楚。綜上,藏藥在青海這個地區的受眾以及普及還是較為廣泛的,換句話說,藏藥在本地區的適用并沒有引起較為嚴重的后果,并且對于一些疾病的診治比西藥更為有效。所以南某的行為沒有給社會造成實際危害后果,其生產、銷售的藥材材料來源系正規渠道獲得。加工、生產也是按照制藥的工藝、程序加工,未添加非藥成份,售后也未造成危害后果的情況下,僅僅依照“未取得生產批號”作出的鑒定意見對其進行判刑是不妥當的。筆者認為,因為南某不具有生產、銷售藥品的資格,擾亂了藥品管理秩序,僅應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綜上,刑法意義上的“假藥”應當作限縮性理解。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應視具體情況來分別處理。[8]對于存在實質性問題的假藥,應對其進行刑事處罰。對于存在形式問題的假藥,也即是不符合藥品管理法對于形式的規定的藥品,在檢驗合格的情況下,若其主觀惡性小,在客觀上沒造成嚴重后果可以不對其進行刑事處罰。[9]可在其行為違反藥品管理法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但是疫苗、注射劑、急救藥品、處方藥等藥品是保護的重點,制造和銷售上述品種的假藥應當一律入罪。刑法要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正確確定假藥范圍,做到既不過度打擊,也不放縱犯罪。[10]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陳興良.風險刑法理論的法教義學批判[J].中外法學,2014(01).
[3]許美.生產、銷售假藥罪使用調查分析[J].人民檢察,2013(17).
[4]于志剛.涉藥犯罪的立法缺陷與完善[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3.
[5]龍敏,倪超,李志民.刑法中假藥、劣藥界定之反思[J].人民檢察,2010(19).
[6]劉曉莉,逢曉楓.制售假藥行為之行政處罰與刑罰適用研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09).
[7]劉佳.藥品制假售假的整治對策[J].中國藥事,2014(08).
[8]龐維俊.生產、銷售假藥罪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14.
[9]趙娟.生產、銷售劣藥罪的立法完善[D].中國政法大學,2010.
[10]王玉玨.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司法認定[J].人民檢察,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