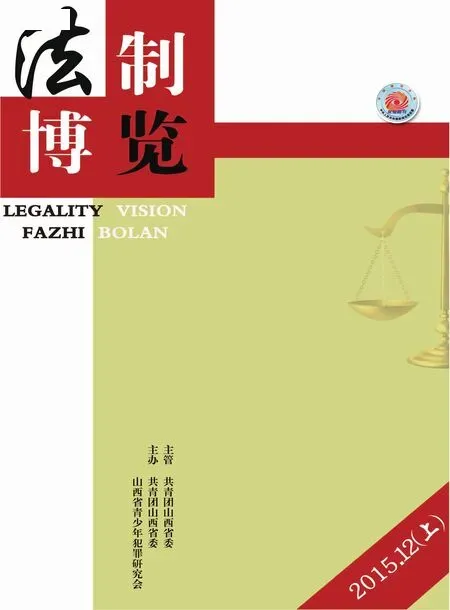“人肉搜索”的法經濟學解讀
趙 青
中國海洋大學,山東 青島266100
一、對人肉搜索成因的經濟分析
由于目前無法對參與“人肉搜索”的網民進行法律管制,他們在網絡平臺發起和參與“人肉搜索”的成本又非常低,因此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中很容易形成“人人是記者”的局面。這造成了傳統新聞報道與針對具體事件的“人肉搜索”有十分類似的地方,但二者又存在幾處關鍵的不同:
(1)“人肉搜索”是網民的自發啟動,沒有既定的行業規則和職業道德約束;(2)網絡具有較強的技術性,缺少相關立法規制;(3)“人肉搜索”的矛頭多指向社會丑惡事件、不道德行為(尤其是官員腐敗)等;(4)“人肉搜索”的真實性缺乏保證;(5)網民在網絡世界使用虛擬身份,真實身份很難確認。綜上,這就使網民在“人肉搜索”中可以恣意曝光他人隱私,對自己所憤慨的人物進行言語攻擊而不必擔心事后會被當事人報復或受到法律的懲處。
對于記者在進行傳統形式的新聞報道時,披露可能涉及個人隱私的敏感信息,其成本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記者披露信息的成本=調查信息成本+發布信息的成本+事后遭遇報復或法律追究責任的風險成本。
而在“人肉搜索”中,網民披露敏感信息成本可如下表示:網民披露信息的成本=調查信息成本+發布信息的成本。
對上述兩個公式,我們進一步分析可知,記者往往需要花費時間和金錢成本親自深入實地調查事件中尚無法掌握的信息,如涉及個人私生活的信息;但網民卻可以通過在網絡平臺上發帖向其他網民求助的行為,由對情況比較了解或有辦法獲得這類信息的網友提供。記者在調查后將所獲的信息發布到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上,還需要編輯、排版、付諸印刷等步驟;網民只需直接在相關網站發帖即可發布消息。前述比較可知,信息調查成本和發布信息成本要低于傳統形式的新聞報道中的同類成本,在“人肉搜索”中事后遭遇報復或被追究法律責任的風險成本更是可以忽略不計,網民進行“人肉搜索”的總成本接近于零。因此網民在追求“正義”、敦促相關部門對事件進行處理與私力報復獲得精神快感而積極參與“人肉搜索”之間選擇后者,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二、對營利性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經濟分析
08年一起轟動一時的中國“人肉搜索”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一審判決,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張某某和北京某公司構成對王某隱私權和名譽權的侵犯,判令上述兩被告刪除相關文章及照片,在網站首頁刊登道歉函,并分別賠償王某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和3000元,加上公證費,王某總計獲賠9367元。海南某公司因在合理期限內及時刪除了相關內容,被判免責。
由此案我們可以看出,即使網站被判令侵權,可預估的侵權損害賠償數額對網站的經營者來說微不足道,法律無法有效制約其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行為。因此,要想通過增加法律成本來激勵網站經營者過濾涉及當事人隱私的信息,其前提條件是侵權的法律成本超過網站經營者相應的廣告收入。有三個原因導致上述條件無法滿足:
第一,侵權賠償金數額太低,無法對網站經營者起到威懾作用。我國的侵權賠償以補償損失為目的,基本不存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此對網站經營者起不到威懾作用。
第二,通過訴訟,網站經營者增加了額外的曝光,獲得額外收入,進一步削弱了賠償金的威懾作用。在人肉搜索案件中,網站的立場通常被視為是具有道德優勢的一方,因此人肉搜索案件的訴訟作為一個事件,無論勝訴還是敗訴,都可以進一步提高網站的正面知名度和相應的廣告收入。
第三,過錯責任原則為網站提供了免責的法律可能性。鑒于互聯網具有的廣泛、迅速、即時等傳播特點,網站經營者在原告起訴前刪除有關內容履行監管義務,可能不構成侵權。網站經營者完全可以在受害人的信息已經廣為人知后,再采取刪除措施來免除自己的法律責任。
三、對受害人的的經濟分析
伴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訴諸于“人肉搜索”解決問題的方式越來越普遍,動輒人肉搜索的也聲音越來越多。被“人肉”者個人隱私遭到曝光或被人辱罵、誹謗,心理甚至生理上都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但最后真正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當事人少之又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被“人肉”者訴訟利潤=訴訟受益—訴訟成本
訴訟成本=舉證成本+訴訟費用
訴訟收益=勝訴或和解獲得的賠償+訴訟產生的社會影響
在訴訟成本中,舉證成本相對于訴訟費用存在不確定性。“人肉搜索”侵權案件適用一般侵權的過錯責任原則,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但這其中通常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往往原告當事人因為缺少網絡相關知識,不能及時保存證據,并且泄露他人隱私的網友人數眾多且為虛擬賬號,難以確定其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身份。對于網站管理者,其一旦發現涉及侵權可立即將網站中的相關記錄刪除,由此我們可預見收集證據的成本必定十分高昂,令人難以負擔。
在訴訟收益中,首先通過勝訴或和解獲得的賠償金額很低,無法彌補信息擴散造成的損害。其次,訴訟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是當事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選擇通過司法途徑保護自己的權利,會讓受害人的隱私信息更加廣為人知。
由此可見,通過訴訟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人肉搜索”的當事人來說,訴訟成本太高而收益通常過低,不但無法彌補在“人肉搜索”中的損失,相反可能擴大不良影響。被“人肉”者不愿提起訴訟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但也導致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后無法得到救濟,從反面推動了“人肉搜索”的發展。
四、“人肉搜索”的去留
法律經濟學要求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該目標要求我們從社會總收益與社會總成本的差額最大的角度分析不同情況下“人肉搜索”可能對社會產生的長期影響。其中,社會總成本等于“人肉搜索”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成本與整治規范“人肉搜索”的成本之和。結合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假設兩種極端情況:對“人肉搜索”任其發展,不加治理(即整治規范“人肉搜索”的成本為零,社會總成本為“人肉搜索”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成本);或者持全面否定態度,堅決封殺(“人肉搜索”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成本為零,此時社會總成本為整治規范“人肉搜索”的行政成本與封殺“人肉搜索”帶來的負面效應的成本之和)。
(一)任其發展
對“人肉搜索”放任不管,從短期來看將出現如下現象:從社會的正的收益來看,人肉搜索充分發動了人際網絡的力量,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揭露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等。從社會的負的收益來看,“網絡暴力”橫行,個人合法權益如名譽權等遭受侵害,糾紛增加。
從長期來看,對“人肉搜索”放任不管可能會出現以下后果:從社會的正的收益來看,保障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促進了監督方式的多元化,督促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法治建設。從社會的負的收益來看,“人肉搜索”導致對個人的合法權益的損害;網民守法意識削弱,導致道德敗壞;可能養成司法辦案依賴“人肉搜索”的惰性,產生對侵害公民隱私權利的漠視;可能造成網絡環境低俗化,不利于社會文明建設等。
(二)堅決抵制
對“人肉搜索”堅決抵制,短期內可能有如下影響:從社會的正的收益來看,有效遏制“網絡暴力”;從社會的負的收益來看,由于“人肉搜索”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此時一舉抵制必然引起網民的抵觸,加深矛盾;一些反腐案件缺少“人肉搜索”的幫助,收集證據的成本將極大提高,偵破難度加大等。
長期下來可能會出現以下后果:從社會的正的收益來看,保證了對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的尊重和維護;重塑健康和諧的網絡環境。從社會的負的收益來看,抵制的行政成本過高,對政府和納稅人造成巨大負擔;不論具體情況的“一刀切”導致民眾言論自由遭受侵害、知情權得不到保障;信息傳播受阻,影響網絡發展,阻礙創新精神的形成等。
綜上所述,對于“人肉搜索”問題,不論任其發展還是堅決抵制,都是既有利又有弊;兩種做法都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對社會福利來說都是沒有效率的做法。因此我們要選擇介于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的辦法解決“人肉搜索”帶來的問題,使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五、治理“人肉搜索”的對策建議
由前文論述可知,“人肉搜索”既不可任其發展,也不宜堅決抵制。因此筆者嘗試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提出如下幾點規范“人肉搜索”的建議。
(一)事中監管:區別對待,“分而治之”
對于“人肉搜索”是否侵權,不妨區別對待:
第一,應該引導、鼓勵的情形。如果是出于法律和道德鼓勵的目的而進行“人肉搜索”活動,不應當限制,而且有關部門還應該加以引導、鼓勵。比如針對現有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或者在逃的貪官等等,對這樣一些人的“人肉搜索”,實際上起到了弘揚社會道德、維護法律正義的客觀效果。
第二,應該謹慎、克制的情形。在面對法律沒有規定,道德也難以評價的一些人物現象進行“人肉搜索”時,網民應當謹慎和克制。因為在這種背景下,法律并不贊同這種搜索行為,道德上可能也不能輕易判斷是壞還是好。在這種情況下,“人肉搜索”游走于道德、法律的邊緣。這樣的行為可能就是純粹滿足一下好奇心,甚至是有一些低級趣味等等。這種情況就不應該鼓勵,網民本身也應謹慎為之。
第三,應該抵制、禁止的情形。對于道德譴責、法律禁止的信息、現象等等進行“人肉搜索”的時候,網民應該自覺地抵制或者是拒絕,要不就有可能構成對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公民合法權益的侵犯等等。
(二)事后救濟:由解決外部性成本最低的一方承擔責任——網站承擔責任
外部性指一個人的行為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祗,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獲得回報。“人肉搜索”現象產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其中,對他人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的,我們稱之為負外部性,行為人沒有承擔該外部性的成本。對于負外部性問題的解決,傳統的經濟學分析遵循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的觀點,即在承認原有權利配置的前提下,采取由負外部性的制造者來“內化”外部性的做法,即如果A傷害了B,A就要對B做出賠償。而科斯認為這種做法掩蓋了問題的實質,由此他提出了相互性的概念,即避免A對B的損害,將導致A遭受損害,至于究竟要允許A損害B還是B制止A,則要看誰承擔這種損害的成本即避免外部性的成本最低。
“人肉搜索”一般涉及三方:被“人肉”者(被侵權人)、網民和網絡服務提供商(共同侵權人)。根據科斯的理論,這三者中誰解決外部性的成本最低,就應當由誰來承擔責任。
初看可知,只要網民不進行“人肉搜索”,就不會有“人肉搜索”侵權問題的發生,不進行“人肉搜索”對網民本身也不會造成損失,因此由網民承擔外部性成本最合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這既符合庇古的糾正理論也符合科斯的外部性原理。問題在于,網民無自覺也無外來激勵約束自己的行為來尊重他人的隱私、名譽,如果要求網民對“人肉搜索”侵權行為負責,因為網絡的虛擬性,追查行為人的成本將成為天文數字,即網民本身避免侵權行為的成本雖低,但若規定由網民承擔責任將導致另一巨大的外部性——大幅增加的司法成本和行政成本。
如果對“人肉搜索”問題放任不管,即由被“人肉”者(被侵權人)承擔侵權成本,則會發生前文提到的種種消極后果,而這是社會所不欲求的。所以我們應該考慮由網站來承擔外部性成本。選擇這個方法有以下優點:網站和網站管理者處于隨時被主管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掌握的狀態,調查取證成本低;網站情況又處于網站管理者的隨時監控管理的狀態,網站管理者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言論可以及時處理,將侵權消滅于萌芽中;管理者對網站的管理操作成本相對低廉。
因此結合三方各自情況不同及不同歸責對象對社會的影響,出于對社會總成本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一旦“人肉搜索”侵權,應當由網站來承擔責任。
(三)加強網絡道德風氣的建設
人肉搜索這類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民眾普遍缺乏尊重他人隱私權及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意識。減少“人肉搜索”的負面效應,長久之計應是從內部加強網絡道德風氣的建設,加強對民眾的法制教育,從根本上解決“人肉搜索”的弊端。
六、結語
“人肉搜索”作為一種工具,和所有群體性活動一樣,人肉搜索也需要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得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而作為人肉搜索的載體,相關網絡平臺無疑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去提煉和萃取人肉搜索獲得的資源。約束不當言論和行為,維護網絡搜索平臺的秩序。讓人肉搜索能夠通過互聯網健康、規范地發展,最終服務于社會。
[1]李成陽.論“人肉搜索”與隱私權的保護[J].商情,2010(13).
[2]林瀚.虛擬與現實是網絡暴力還是道德延伸[J].電子商務,2008(10).
[3]張樂.檢索、道德與暴力:人肉搜索的社會學思考[J].當代青年研究,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