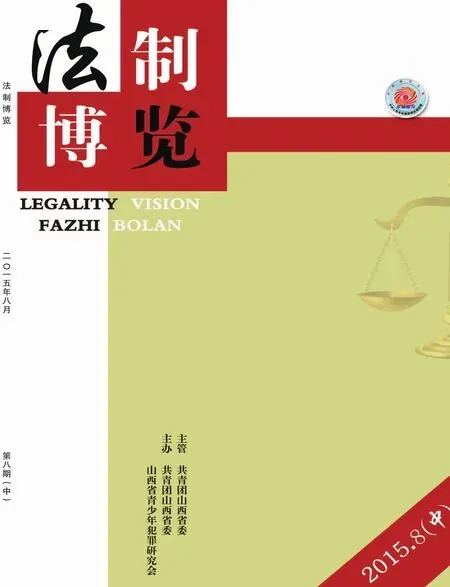論唐朝血親復仇案之禮法矛盾
應濤濤 溫慧輝
中國計量學院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呂思勉先生說:“復仇之風,初皆起于部落之相報,雖非天下為公之義,又有親親之道存焉。”[1]以現代人眼光觀之,復仇是極其暴力與荒蠻的。然而,在宗法親情深深植根于人倫道德的中國古代社會,血親復仇既作為一項與生俱來的權利,又作為一項不可推卸的義務而長期存在。《禮記·檀弓上》記載,孔子曾就子夏“居父母之仇,如之何”的疑問作出“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的回答。不難看出,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學對血親復仇持以支持和肯定的態度。
盛世唐朝是中國古代各項基本制度趨于成熟完備的歷史階段,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法為政教之用”的法律思想為其基本治國方針。表面上看,統治者將“禮”與“法”兩相結合,以儒家禮義指導其立法與司法實踐,但在司法實踐中仍舊不能避免“禮”之同情與“法”之嚴肅的固有矛盾。
一、烈女衛氏案:屈法而伸情
唐初統治者汲取隋亡教訓,為安民心,減輕刑罰,以“一準乎禮”的司法理念規范百姓行為,以儒家禮義感化百姓,維穩江山社稷。出于主宗法、重倫理的社會現狀,“孝心大過于法律”的司法模式為當時所接受。“父之仇,弗與共戴天”,血親復仇在當時社會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并得到了朝廷、官員、民間三方的強烈認同。
《舊唐書·列女傳》記載:“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仇。無忌從伯常設宴為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本案有其內在的特殊性:一方面,母親改嫁且無兄長,作為父親唯一親情血緣的紐帶,復仇的責任必然落到了年僅六歲的衛氏身上,復仇的長期性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復仇者以一個弱女子的身份“常思復仇”并“功德圓滿”必然會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較之君子復仇更為無可厚非、大義凜然。孝女衛氏想必深知復仇枉法的規定,“既而詣吏,稱父仇既報,請就刑戮”。但此事為朝廷所知,唐太宗對衛氏替父報仇之行為“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并賜其良田豪宅,命地方官員為其尋親送嫁。
司法者對衛氏復仇一案的同情審判,體現了屈法而伸情,即在“禮”與“法”相矛盾的過程中,“禮”的價值體現更為突出,“法”的正常適用應“禮”的介入而夭折。維護復仇是基于固有感情的需要,當復仇的習慣深入人心,當權者感同身受地佩服復仇之行為,對復仇者予以寬恕及赦免時,“法”的權威性與認同感則大打折扣,儒家強調的“禮”則上升為司法者裁判的強有力依據。
烈女衛氏在禮法的“二元標準”下得到寬宥似乎并未出乎意料,然而武則天時期對徐元慶復仇一案的依法審判卻超出了預期。
二、徐元慶案:憫情而從法
轟動一時的徐元慶案發生于武則天時期,此案以民殺官的情節展開成為古代血親復仇案的又一典型。在趙師韞任下邽縣尉時期,徐的父親因觸犯刑律而被趙師韞處死。徐元慶隱姓埋名,隱匿為驛站仆役,終于一日手刃仇人,并向官府自首服罪。
對于徐元慶的審判應當從“禮”還是從“法”,這在當時激起了不小的爭論,諫官陳子昂則以一篇《復仇議狀》上書武則天。陳文云:“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強調了國家統一的律令法規執行不能兩樣,徐元慶應當伏法;另一方面,“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茍,元慶不宜誅。”說明了禮義教化不能馬虎,徐元慶孝悌之為足以感化百姓,可免其死罪。在“禮”與“法”的兩難境地中,他提出“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閭墓,嘉其徽烈”。陳子昂中庸式的裁斷方式為武則天所采納,他兼顧“禮”與“法”兩方面,既維護“禮”的神圣,又堅持“法”的不容褻瀆。由是觀之,武則天時期,司法者基于統治的需要以及社會秩序構建的考量,對復仇的法律限制有所強化,當權者在“禮”與“法”的抉擇中更加注重國法的嚴肅性。然而,對“禮”的難以摒棄還是使司法者的同情審判難以走出困境,公眾的道德愿望強烈要求血親復仇的司法不能與孝道文化相背離。
然則,此種留有余地的審判模式還是未能擺脫“禮”對于“法”的桎梏,陳文之諫雖似乎合國法、順人情,但難免陷入賞罰不明,禮法不分的泥沼。百有余年,柳宗元舊案重提,一紙《駁復仇議》據理力爭,對“編之于令,永為國典”的徐元慶一案大加批駁。其認為陳子昂“誅而后旌”的做法自相矛盾,可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①并指明應“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
三、禮法矛盾之辨析
歷朝歷代對于復仇案件的記載難以計量,司法者對于復仇案件的審判或是情就于法,或是法從于情,難以形成整齊劃一的審判模式,禮法矛盾正是復仇司法處于尷尬境地的重要根源。觀儒家經義之禮,復仇符合孝悌倫常,順應民意且牢不可破。而唐朝立法者對復仇行為的禁止也并非斬釘截鐵。《唐律疏議》卷十八議曰:“殺人應死,會赦免罪,而死家有期以上親者,移鄉千里外為戶,其有特赦免死者,亦依會赦例移鄉。”此“移鄉避仇”制度將被害者親屬與殺人者分隔千里,旨在以空間距離的增加杜絕復仇行為的發生。可見立法者并未直接明確禁止復仇,只是從側面對復仇行為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唐律卻專條禁止雙方當事人私下和解,私和者將會受到“流二千里”甚至更嚴厲的處罰。親屬為人所殺被視為忘孝不仇,不得私和則間接強調了“仇必復”,這也就為民間私相仇殺留有了縫隙。唐朝立法者模糊規定限制復仇,但對私和卻明令禁止,足見立法者的矛盾心理。由是觀之,“禮”對“法”的羈絆阻礙了血親復仇案的統一審判,可又為何不摒棄“禮”還復仇司法的“一元標準”呢?
首先,民間濃郁的復仇意識由來已久,若要根除并非易事。復仇源于原始社會,在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部落,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尚未構建,復仇不單單被視為一項親情義務而無法拋棄,更是一種依靠“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便捷手段得以自救的方式。復仇已然成為民眾深入骨髓的慣性思維,豈是一朝一夕能夠更改的?唐朝統治者如若對復仇予以偏廢,不論是在治國方針、政治思想還是在立法司法中都需要作出極大的努力,其難度可想而知。
其次,唐律儒家化在極大程度上使得“禮”對“法”的約束增強。“德本刑用”是《唐律疏議》的核心思想,“一準乎禮”是《唐律疏議》的基本特征。[2]唐朝統治者為教化百姓,引禮入律,力圖將“尊尊”、“親親”等儒家德禮思想與法兩相結合,殊不知在復仇案件的司法上留下了懲處與否的尷尬境地。一方面,生殺予奪的權利本應歸公權所有,殺人者依法處死無可辯駁;另一方面,《唐律》中影射的德教禮治又允許著對復仇者法外施仁,網開一面。
最后,儒家“孝義”思想契合了復仇的正當性。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作為王道正統自然對唐代上至皇親貴胄,下至黎民百姓影響極大。推行禮治的儒家強調“孝悌為仁之本”,“以孝治天下”自然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承繼。就唐朝而言,《唐律》中諸多“不孝入罪”的規定更是將原屬倫理道德范疇的孝上升為法律準則。況且,在家國一體的封建社會,盡孝與忠君具有一致性,對孝義之德的推崇必然有利于強化忠君思想。從穩固皇權的角度來講,以孝維護封建統治,何樂而不為?子復親仇無疑是社會日常最突顯孝義的行為,雖然它對國法的正常實施構成挑戰,但是孝義的彰顯卻是最深入人心的。在重孝的社會背景下,復仇者寧可受到殺人償命的屠戮之刑,也不愿茍活于世而背負不孝的罵名。因此,在對復仇者的審判過程中,依“禮”縱之,損的是國法的權威;依“法”斷之,失的卻是社會的道德期許,“禮”與“法”的難以調和便是顯而易見的。
不管是屈法而伸情的烈女衛氏一案,還是憫情而從法的徐元慶一案,始終擺脫不了“禮”與“法”這一對矛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禮”與“法”的博弈只不過是統治者對“禮”與“法”的重視程度不同,作出此消彼長的選擇罷了。
[ 注 釋 ]
①柳宗元.駁復仇議.
[1]霍存福.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0.
[2]徐祥民.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