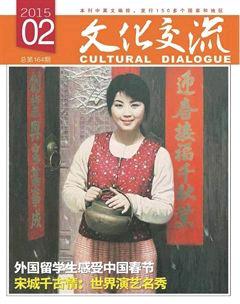慈城全恩堂:麒韻故鄉情
王靜



古文“風情張日,霜氣橫秋”:風度之高勝于太陽,志氣之凜盛如秋霜,用于描述中國京劇史上的大家—周信芳的表演藝術,應當可行。
周信芳以獨特的風格,創造了京劇的一種藝術流派—麒派,世人譽之為“麒韻”。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聯等多次舉辦紀念周信芳舞臺生涯的活動,祝賀這位藝術家的創造性勞動。
作為周信芳的故鄉,浙江寧波也先后為他舉辦過紀念活動,最近一次在2012年。紀實文學作品《再尋麒麟童》首發式、名家座談周信芳、參觀故居全恩堂……以追大師足跡,以尋大師精神。
說周信芳的京劇生涯,得先說其父周慰堂與京劇的緣淵。周慰堂是慈城周氏顯宗祠十八世孫。慈城舊時為寧波府慈溪縣治所,早在明代已是戲文之鄉。至晚清,小城流行徽班(京戲)、紹興大戲、余姚灘簧等,“午前開肆,午后閉肆,擊鼓吹簫,謳歌唱曲,凡戲玩無不為”。在這樣的市井風俗中,布店伙計周慰堂一旦閑暇,便愛去看戲文,后來竟跟戲班遠走。慈城周氏讀書傳家,世譜上有三十八人取功名入仕途,這樣的“世族”再怎樣看待“士農工商”也不會允許子孫行此“賤業”,族長作出了將周慰堂逐出祠堂的處罰。
逐出祠堂是封建宗族制度最嚴厲的懲罰,但周慰堂似乎并不介意梨園。1895年1月14日(甲午臘月十九),周慰堂的兒子在江蘇淮安出生;周慰堂不忘按家族輩分排行,為兒子取名“信芳”。1899年,周慰堂送四歲的小信芳拜師學藝。1902年,戲班讓七歲的小信芳以“七齡童”之藝名,在杭州拱宸橋天仙茶園為他人配演,引起戲曲界和戲迷的關注。
如果說杭州的戲臺讓小信芳初露鋒芒,那么上海的戲臺則讓其成名。1907年的某次演出,海報上把“七齡童”誤寫成“麒麟童”;戲迷戲說,從此以后,就像祥瑞一樣,“麒麟”馳騁,周信芳的戲藝譽滿大江南北,成了人們戲曲生活中向往的名字。
十余載舞臺淬煉,十余載喜怒哀樂,十余載春華秋實。1916年,已然以麒派藝術立足上海戲臺的周信芳,首次擔任上海丹桂第一臺的后臺經理。這時,飄泊多年的周慰堂渴望榮歸故里,渴望落葉歸根,他覺得兒子年輕而有為有成,便作出讓周信芳陪同返鄉認祖歸宗的決定。
周信芳十分理解父親的心愿。他曾說,他小時候學戲最原始的動力之一,就是要為父親鋪就一條認祖歸宗的路。
按族長的安排,1918年8月,周慰堂興沖沖采辦了供奉祖宗的物品,采辦了敬送族親的禮品,從上海十六鋪上船到寧波江北岸落船,再坐車到慈城。走過德星橋,走近顯宗祠,可是祠堂的大門依然緊閉,父子倆傻傻地站著……一會兒,有人來告知:須拿出三千塊銀元作為修繕費,才被允許進入祠堂祭祖,否則,即使是族長的決定也無法通融。
父子倆喪落地回到寧波客棧。族人托人“協商”于周家父子,表示可減價到兩千塊銀元,若沒有帶錢也可寫下欠條……這數目的錢,對于當時上海灘紅角的周信芳來說不難籌集,他勸父親同意、完成心愿。
但周慰堂說什么也不答應,他認為:緊閉祠堂不讓進、先拿錢,這于情理不通。在回上海的輪船上,父子倆商定自己建座祠堂,以免一切糾葛。三年后,周信芳陪父親到慈城掃墓,落實了此事。
1925年1月18日,是甲子臘月廿四,上海的戲班封箱停演,周信芳陪父親回慈城半個月,舉行周氏全恩堂開堂儀式。這組建筑由臺門、全恩堂、后樓及廂房組成,后來稱“周信芳故居”。全恩堂的建立,表示著周氏后裔周慰堂一支認祖歸宗。
1945年清明節,周信芳護送父親的靈柩回故鄉。靈柩安葬在慈城夏家岙(今白龍山公墓附近)的周御史房祖墓墓地。全恩堂懸周慰堂遺像。
周信芳助父親建全恩堂,是他不忘祖先血脈傳續和恩澤的中華文化根基使然。為報故鄉,他多次來寧波演戲,影響所及的有:認祖歸宗后的次年夏天,他率上海大新舞臺全體藝員,在江北岸的鼓舞臺連演9天15場麒派戲《南天門》《四進士》等;1936年,他率戲團登天然舞臺,連演20天自己的代表劇《掃松下書》《明末遺恨》等;1958年,時任上海京劇院院長的他鼓勵九個子女中唯一繼續京劇表演的幼子少麟到寧波為父老鄉親演戲,并回慈城全恩堂祭祖……
周信芳有濃烈的愛鄉情懷。1949年寧波解放,他發動上海演藝界為寧波災民義演,并到電臺現場播唱數次。1951年,寧波效實中學籌建圖書館、實驗室,時任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的他將租賃的寧波西門老郎殿無償轉讓。
歲月的風雨侵蝕不止,周信芳故居曾有重修,如今僅存全恩堂。三開間的全恩堂為一幢典型的祠堂建筑。祠堂右側內墻鑲嵌一大一小兩塊石碑,大的鐫《重建全恩堂碑記》,小的刻“祠堂禁條”。1985年4月,出席寧波各界紀念周信芳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周信芳之女瞻仰了全恩堂。
一個人記憶著一個地方,一般有兩種可能:一是留下一個人的生命痕跡,一是留下一個人的感情痕跡。寧波慈城是周氏父子的故鄉,那是與生俱來的記憶。如今,我們從這座漫漶的全恩堂,從這位大師的藝術成就遙想周氏父子建立全恩堂的心情,不難看出這兩位游子感恩祖先、感恩家鄉的情懷,這就是當年為什么名取全恩堂之由吧—篤于親親之義……
(除署名外,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