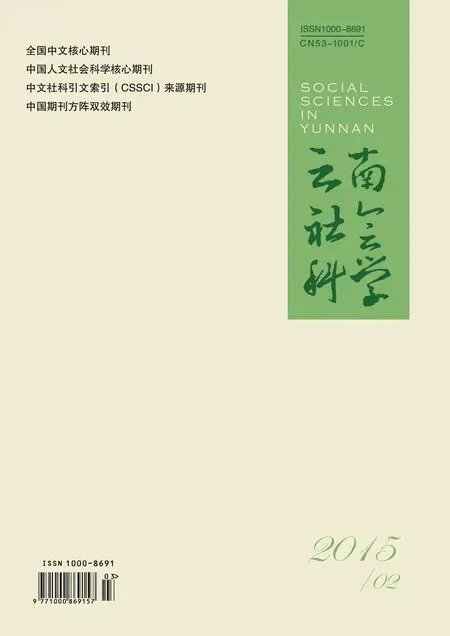重建政統與學統
——明清之際學術轉型的內在理路
劉 宏
在儒學發展史上,明清之際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其之所以特殊,不僅在于出現了政權易主的朝代鼎革,尤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儒學傳統在其內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回首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時,人們往往可以用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明、清代這樣的歷史學時期來區別不同的學術形態*通常的觀念是: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唯獨需要將“明清之際”這樣一個區間提取出來加以重視,這足以說明其重要性。但對于此一時期的學術形態本身卻遲遲未有定論。如果將明清之際的儒學置于學術史的進程中來看,其連接的乃是前期的理學和后期的樸學。關于這三者的關系,學界出現了多種解釋模式,其中較為典型的是以梁啟超、胡適為代表的“理學反動說”和以錢穆為代表的“每轉益進說”。客觀地說,這兩種解釋產生于民國之后的中西文化論爭時期,雙方由于各自的學術背景或是明清之際的反“玄學”和乾嘉的考證方法符合西方的科學精神,或是帶著吾國文化淪亡的悲情注重宋學的漸變和延續。雖然不能否認以上兩種解釋都有各自合理性之依據,但也難免存在“以今律古”之嫌。其后,余英時在其師錢氏的方向上給出了“內在理路說”,然而,余氏又重在史學眼光的省視,對儒家思想觀念的演變相對忽視。在此,筆者愿意接受“內在理路”這一話語表達,重新考察此期儒者的現實關懷和學術走向。
一、天崩地解:政統與學統的雙重倒塌
用黃宗羲的話來說,明清之際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而天崩地解一詞不僅刻畫出了明亡的歷史事件在一個傳統士大夫心目中留下的無限悲痛和憤慨,更突出了這個時代政治的昏暗和主流價值的缺失。向來以先進文化自詡的天朝上國何以又一次被北方蠻族所入主?如此不堪的歷史結局勢必要回溯到晚明社會的復雜現狀。
政治上,腐朽的政體架構一方面不能應付內外的不斷戰事,另一方面激化了執政集團內部各方利益代表的權力爭斗。經濟上,隨著嘉靖、萬歷以來的手工業、商業不斷地發展,在傳統社會的母體內部孕育了以商品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因素,出現了有史以來最為繁盛的市民社會景象。而當時的明王朝對新興的工商業施以各種名義的繁重課稅,使得這種新的社會群體亟待尋求自身利益的合法保護。文化上,科舉時文不再是有識之士唯一的上進之路,變質的理學說教已然壓服不了言論自由的強大呼聲。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詔曰: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多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舒化:《大明律附例》,明嘉靖刻本。
明初取消了丞相制度,使君權失去了相權的制約。洪武、永樂兩朝又通過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關的設置進一步加大了對廷臣的監督,使君權得到空前集中。全國大權如此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身的現象實非歷朝歷代所能比,這預示著傳統的“家天下”政體已然發揮到了自身的極致。
萬歷中后期,神宗皇帝長期不上朝理政,大權旁落于閹寺之手。由宦官掌權的錦衣衛組織成了實際上的國家權力機構,因而激起在野人士清議四起。面對神宗的荒怠,朝中形成秦黨、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等朋黨之爭,而其他各黨基本依附閹寺一黨打壓東林黨,以致出現“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八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的局面。
天啟一朝,以“九千歲”自居的魏忠賢為剪除異己,對作為學術和政論團體的東林黨人肆意開列罪名,釀成眾多慘案。同時,在宮廷內部出現了“紅丸”、“梃擊”、“移宮”三大案。在這些案件的背后,實是君權、閹黨和清流多方力量的角逐。如此,腐朽而松散的政治體制導致北方對滿人的戰事一再失利。明王朝又以征遼練兵為由,派出宦官四處敲詐勒索,釀成了各地的反礦稅斗爭不斷。加上土地的兼并集中和自然災害的發生,最終引發了西北地區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與岌岌可危的政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晚明商品經濟的勃興。明中葉之后,礦產、鹽業、棉紗、絲織、茶葉、陶瓷、刻書等行業逐漸發展,形成了很多無田而富的行商大賈。當時工商業的繁榮在馮夢龍的小說中得到了描繪:“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布具到此市上販賣。”*馮夢龍:《醒世恒言》,明天啟葉敬池刊本。脫離土地的自由民增加了社會人口的流動,逐漸在工商業發達的城鎮聚集。在江南一帶尤其是運河兩岸和長江三角洲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出現了許多的小村鎮和城市,從而造就了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又大大激發了市民階層本為理學說教所壓制的私利追求和情欲表達。因而,在思想觀念上,一方面要求沖破以家族為單位而確立的傳統倫理規范和價值原則,另一方面使得市民階層重組個體之物質富足和精神追求的合理搭配。最終,反映市民生活的傳奇、院本、雜劇、小說等文學樣式在晚明社會流行開來。其中所彰顯的思想觀念一方面引起了保守士人的憂患,另一面卻逼迫著儒學面對既定的社會事實,做出有效的理論回應。
學術上,廣泛流行于晚明社會的乃是陽明學。而王陽明晚年的“無善無惡”之旨卻取消了心體善惡的價值判斷,給良知的泛濫流行打開了沖破道德束縛的缺口。在后王陽明時代,王學為天下裂,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泰州學派。而出身泰州學派的李贄力倡“童心說”:“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而不論“真心”是作為“童子之心”,還是作為“最初一念之本心”,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飽食暖衣等生存條件所需,尚未受到外在倫理規范的影響和制約。可以看出,“童心說”將與孟子所說的“四端之心”相對的自私自利的一面展現了出來。
二、經世致用:明清之際的實學指向
儒學自孔子創立之初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的內圣外王并重之學。雖然這樣的理想并未真正在傳統社會的舞臺上上演,但儒家主觀上卻從來沒有放棄過治世的訴求。儒學發展到宋代,為了應對道家和佛教形而上學的挑戰,將學問的重心轉移到了性理的辨析上,而相對忽視了外王的一面。與朱子同時雖然有浙東陳亮和葉適等人重視事功的言論,但在理學占據正統的時代其呼聲過于弱小。到了明代,王陽明推崇陸象山心學,通過良知理論將天理從形上界拉回到活動的人心之中,打開了心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但卻造成了空談良知的流弊,儒學外王的一面也始終沒有成為正視的課題。
這一時期思想家群星璀璨*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但跳過這些儒者們家庭環境、個人經歷、學術成果等等因素的不同,“經世致用”則是他們共同的呼聲。“經世致用”作為一種學術精神,在不同的時代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含義:有時強調主體的道德修養;有時強調事功趨利;有時強調治國、安邦、平天下;有時強調實行、實用*王杰:《反省與啟蒙:經世實學思潮與社會批判思潮》,《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8年第1期。。很明顯,在社會急劇動蕩的明清之際,“經世致用”的后兩義更加凸顯。另外,就“經世致用”的表現形式來看,在社會穩定、思想一統的年代,如此的呼聲常常暗藏在學術工作的背后,而在社會轉型、思想爭鳴的年代,常常作為為學的目標直接顯現在學者的話語表達之中。在明清鼎革的年代,為了學以用世,治國安邦、實行實用的訴求自然凸顯出來。一時儒者競相批判理學的空疏無用,將自己的為學宗旨定位于“經世致用”。此種言論幾乎是人人盡有,個個提倡,下面僅舉幾例。
如黃宗羲言: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后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側身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猛然開口,如坐云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如王夫之為學:
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于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讀史,讀注疏,于書志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閱之,而更以見聞證之。*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
可見,上述言論是直接受到了“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明亡刺激。他們將理學、心學的章句語錄比之于魏晉年間的老莊清談,從而主張重視當世之務,要求回歸《六經》之旨。在他們的心目中,“欲挽虛竊,必重實學”*方以智:《東西均》,龐樸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可謂是當時的一致要求。
為學之“虛”與“實”成了大儒們嚴辨儒與佛、道的界限。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經世致用風氣下的“虛實”問題。當初宋明理學的出現正是針對佛、道的虛玄而發,當其悄然興起的時候,也曾自我激勵“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也曾自我期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南宋時期,理學經過朱子的集大成之后,成功與政治聯姻而作為治世教民的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謂其不是經世之實學。當朱子構建的天理世界無法再適應時代的發展,陽明學的興起也可謂正是為了挽救天理之虛。縱觀陽明一生,疏劉瑾之奸、平寧王之叛、定四方之亂,豈能不謂之為實學!而晚明市民社會背景下主張“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的異端思想卻也恰恰是最為關注現實的學問。到了明清之際,儒學關于虛實之辨的話頭之所以又一次占據了學界討論的中心,只不過表明了“崇實”一直是儒家初衷不改的價值理念。只是,此時之“實”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涵再度發生了改變。我們雖不能根據儒家某一派的學說就武斷地判定此實彼虛,但卻可以從他們所批判的對象和從事的學術活動中,總結出他們所認為的“實”究竟何指。
從以上諸儒的言論中,不難發現,他們所主張的實學已不再是恒定之天理或活動之心體,而是蘊含在儒學經史傳統之中的地理、兵革、財賦、典制等等形下之學。因此,這一期的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致力于經學和史學的研究。
三、天下為公:重建政統的理論基礎
自秦漢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直是君主專制。在“家天下”的政治體制下,所有臣工之權皆是來自君主的授予,官吏的設置無非是君主權力的下放和擴散。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君主集權制,不僅造成了國家治理成本過大,而且導致了社會運轉效率的緩慢。另外,隨著市民社會所帶來的經濟繁榮,權力的高度集中已不能適應各種新生事物的出現,要求權力的分散落實就成了社會治理的必然呼吁。明亡之后,君權作為政治權力的象征,成了儒學批判的主要目標;分權的政治模式成了重構政體的主要方向。
眾所周知,儒家一貫的政體建構次序是家、國、天下。在儒家推崇的理想社會中,堯、舜、禹、湯作為“王天下”之主,被賦予了“為天下之公利而不為一家私利”的人格。這樣的圣人政治成了后世一直向往的理想形態。漢儒鄭玄在注《禮記·禮運》中“天下為公”時說:“公猶共也。禪位授圣,不家之。”孔穎達疏曰:“天下為公,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圣德,不私傳子孫。”*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可以說,“天下”即是萬民公利的代名詞,“天下觀”即是儒家政治體制建構的理論源泉。
而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作為王乃是有位無權,政治權力已被各諸侯國的國君所竊取。秦漢之后,建立在一家之姓私利上的“國”更是僭越了天下實權。如此,天下不過是一家之天下。在明亡的背景下,儒家的天下觀念再度成為重構政體的理論基石。顧炎武首先區分了“天下”與“國”的觀念:“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像明清易代這樣的現象,歷史上屢見不鮮,自然只可謂之亡國。而要重新建立合法政權,就需要重新秉持“天下為公”的儒學理念。
“天下為公”表明了儒家要求將政治合法權建立在萬民公利的基礎之上。后世居于天子之位的君主作為傳統社會權力的象征,也必然被要求能代表天下萬民之公利。而事實情況卻是:在君權時代,君主一己的利益卻凌駕于天下萬民的利益之上,這樣就顛倒了天下與君的關系,混淆了最高權力的來源應該是萬民而不是君主。正如黃宗羲所批判:“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不能代表萬民利益的君主早被孟子視為“獨夫”“民賊”。(《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子下》)明清之際的唐甄直斥:“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帝之神,皆人也。”*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這樣,君主被拉到了“天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君主的神圣性也就蕩然無存了。面對明末農民起義的形勢,唐甄繼續說到:“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眾,旬日立致。是故陜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為仇敵,賊為父母矣。”*唐甄:《潛書》,1955年。可謂是對君權的絕大諷刺。
關于君與民的關系,歷史上曾有孟子著名的“民貴君輕論”(《孟子·盡心下》),后世對君主的批判也不絕如縷。但明清之際的儒者往往從人性的深度,質疑君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如黃宗羲認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必千萬于天下之人。”*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2005年。與黃氏持相同言論的是顧炎武,顧氏認為:“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2005年。如前文所言,人性之私的觀點在晚明的李贄那里就得到了認可,在當時卻被認作異端思想。但到了明清之際,像黃、顧這樣被一致公認的大儒這里,已經成了儒家理解人性的典型觀念。總之,在黃、顧等人看來,作為人君需要能夠克服自己之私利,明了君主的職分乃是為天下之公利,進而行仁政以滿足天下人人之私利。在天下觀念的指導下,針對不能履行職分的君主,萬民自然有權有易君之舉。
重新構建政體,當然不能僅僅停留于批判的武器上,這與空談的講學形式相去不遠,也遠未達到實學、實用的經世訴求。因此,在提供權力合法性的批判之外,還需針對現實的政體狀況給出具體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方案。《明夷待訪錄》一書闡發了這一時代最高的儒家理想社會藍圖。其中有三點尤為值得注意:一是將君臣關系定位為“君與臣,共曳木之人”。臣之出仕,乃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傳統的君為臣綱的統屬關系被糾正為“共為天下事”*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2005年。的師友關系。二是將君和臣皆設置為國家權力機構之一,主張“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2005年。三是將“天下之是非”公之于學校。學校不僅是國家養士的機構,還當成為國家權力的監督機構,發揮其輿論監督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民間社會的參政議政需求。
四、回歸六經:重建學統的必由之路
有學無位的學者,在重建政統方面,要么是利用言論的武器對現實政治予以批判,要么是在思想的深度重新思考政體的合法性依據。但作為明代遺民的黃、顧、王等人又往往拒絕參與清代政權,這就阻礙了他們的政治理念能在身處其中的清代被貫徹執行。另一方面,作為剛剛取得政權的滿人,唯恐其君權統治不能穩固,自然很難接受帶有現代性色彩的新型儒學理念對自身君權合法性的否定。但現實的政治困境并不能構成儒學理論發展的致命影響,因為學統從來都不是僅僅依附于政統而存在。“經世致用”的訴求也并不因為重構政統的此路不通而被放棄。在重構政統的現實道路不可取的時代,退而回歸經學以待訪無疑是更為可行的選擇。
1.重建學統的方向:由宋學余緒到返回孔孟
明清之際的大儒,在學術上面臨的王學末流所導致的空疏學風。為了救王學之敝,清初時期在理學內部產出了修正王學、黜王尊朱、調和朱王等取向。
王學修正者以黃宗羲最為代表。學宗陽明的黃宗羲,接續其師劉宗周的王學修正路子,將心學中長期存在的本體與功夫之辨明確定位于:“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七冊),2005年。
與黃氏同師劉宗周的張履祥雖然其學脈可以算在王學門下,但其非難陽明的態度可謂是絕不留余地。如他稱:“姚江大罪,是逞一己之私心,涂生民之耳目,排毀儒先,闡揚異教。而世道人心之害,至深且烈也。”*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又曰:“姚江著書立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爍善遁,使人不可把捉,真釋氏之雄杰也。”*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2002年。其為學已走上程朱“居敬窮理”一路,可謂是由王返朱的典型。
另外,面對朱、王之爭,當時大多數學者持的是調和朱王的態度。如與劉宗周齊名的北方大儒孫奇逢嘗曰:“文成之良知,紫陽之格物,原非有異。”*孫奇逢:《四書近指》,清同治刊本。
在朱子話語逐漸壓倒陽明占據上風的情況下,當時尊王反朱者,亦非無有。毛奇齡或許就是其中的一個特例。他痛斥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無一不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毛奇齡:《四書改錯》,嘉慶十六年學圃重刊本。。
以上諸儒,可謂依然依違于朱、王之間。而當時對朱、王都能進行自覺反思的大儒當推王夫之。王夫之猛烈批評王陽明心學,一反朱子對形上之天理的重視。在宋學中,他“希張橫渠之正學”,發揚了張載的氣學思想,而將學問的立足點放在形下世界。其論道器、體用、理氣、知行等,一以后者為據;其論身心、動靜、有無等,皆主兩者交相互用。從王夫之構建的龐大體系來看,整個宋明理學內部的理本論、心本論、氣本論等典型形態都得到了總結。
其后,學界漸漸從依附宋學走向了與宋學決裂的對立面。其中以顏元最為代表。顏元不僅視宋明理學為禪學,更是痛斥漢唐注疏訓詁之無用,其氣魄之大可謂是明清之際的儒者中絕無僅有者。誠如梁啟超所言:“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我們雖不可按學術流派將顏元歸為某派與某派之爭,但顏元體現出來的“爭”之精神卻是比任何一派都為激烈。而顏元所爭者,唯在于孔孟之道。他明確將程朱之學與孔孟之道對立:
歸博來,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圣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餼羊,予本志也。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士下,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終此乾坤,圣道不明,蒼生無命矣。……于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顏元:《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顏元提倡習行有用,對于一切沒有現實效用的學術都欲摒棄之。因而他極為反對朱子的讀書之教,他認為:“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摩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個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顏元:《顏元集》,1987年。從顏元反程朱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宋學已經完全失去了權威。其認為必須跳過宋儒、漢儒,直接回歸到孔孟之道方能重建儒家學統。
2.重建學統的依據:由文本辨偽到回歸《六經》
眾所周知,宋儒對于經典普遍具有疑經精神。與漢唐重視《六經》不同,宋明理學是將其理論建立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四子書基礎之上。而其中對于《大學》一文尤為重視。朱子認為《大學》有斷簡闕文,因而作格物補傳建立起了“即物窮理”的理論。其后,王陽明力圖恢復《大學》古本,將“格物致知”解釋為“致良知”。晚明劉宗周為了修正王學,又從《大學》中汲取營養,發掘出“慎獨”“誠意”諸新論。明清之際,為了推翻宋學觀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對其理論基礎加以重新審查,而《大學》一文首當其沖。陳確首先對《大學》一文的真偽發難,他在《大學辨》中開篇就指出:“《大學》首章,非圣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自此之后,對文本的辨偽工作更是延伸到了《六經》的范圍。如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力辨河圖洛書之非,成為后來胡渭《易圖明辨》的先導。胡渭又作《大學翼真》,明確指出:“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于補。”*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黃宗羲之弟黃宗炎著《憂患學易》一書,考證出宋學開山周敦頤之《太極圖》出自道士陳摶。黃宗羲更因閻若璩之問《尚書》而作《授書隨筆》一卷。其后閻氏作《古文尚書疏證》,解決了東晉梅賾所獻的二十五篇古文真偽的千古疑案。其間雖有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與閻氏抗辯,但隨后惠棟又作《古文尚書考》將此案落實無疑。
不能否認的是,在這些文本辨偽的背后離不開當時的程朱陸王之爭。誠如余英時所言:“清代經學考證直承宋明理學的內部爭辯而起,……一個人究竟選擇某一部經典來作為考證的對象往往有意無意之間是受他的理學背景支配的。”*余英:《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如陳確的《大學辨》主要是對程朱而發,黃宗炎考證《太極圖》與自身的陸王立場相關,而閻若璩辨古文之偽也可以看作是朱子對《尚書》懷疑工作的繼續。毛奇齡之作更是帶有他與閻若璩之間立場不同的意氣之爭。但無法忽視的是,雖然以上諸人在文本辨偽的背后存在著程朱、陸王之爭,但文本辨偽的客觀結果卻是將理學諸多根本觀念推翻了。如既然《大學》并非孔子和曾子所作,其權威性就自然大打折扣,也就沒有必要再將其作為經典來奉行研究,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所有觀念也就隨之失去了神圣性。而通過對理學宇宙論基礎的《太極圖》源出道家而非儒書的考證,更是為其后清人批評宋學援道入儒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至于偽《古文尚書》的定案更是將心學所津津樂道的《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傳心打倒在地。可以說,文本辨偽的初衷是為了爭個程朱、陸王的孰是孰非,卻最終導致了雙方的兩敗俱傷。
通過文本辨偽,一方面使宋明理學所提供的價值觀念失去了權威依附,另一方面為儒學的重回《六經》掃清了文本道路上的障礙。其后,隨著理學觀念的倒塌和清朝文化政策的調整,學界的主流將學術對象鎖定在了以《六經》為核心的訓詁考據上。
3.重建學統的方式:由理學體悟到經學考證
由于宋明理學的學術對象是心、性、理、氣等形上的義理辨析,其學問的交流往往體現在講學的活動中,最終的學問形式結晶在大批語錄的刊行。理學所追求的本體依賴于學者的形上思辨,而不論其主敬還是主靜的為學功夫,都重在“體悟”二字。如程顥曾自稱:“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朱子在《四書集注》中更是一再告誡學者“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這樣的為學方法是從個體內心的是非判斷出發而卻解釋既定的經典文本,經典本身的真偽問題并不構成個體心得的真正來源。當經典與“我”發生沖突時,就不惜疑經乃至改經,朱子的“格物補傳”就是典型的一例。在這里經典失去了對解釋者的約束力,不過成了印證“我”的外在依據,而陸象山的名言“《六經》皆我注腳”*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就成了這種經典解釋模式的合理口號。王陽明雖然有尊經的主張,但經典在陽明學的體系中卻是:“《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亦即在尊經的外表下,實是“尊心”。經典的權威性在王學末流的話語中更是被打破,甚至成了攻擊的對象。
而伴隨著回歸《六經》成為經世致用的必然趨勢,經典的權威被重新認可。新學風下的學術對象不再是超脫于經典之上的心性之學,而是實實在在的《六經》文本。參研經典的方式也就不得不由體悟性的語錄向客觀性的考證靠攏。但這樣的轉向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程朱、陸王依然占據著學界爭論焦點的清初。雖然此時已經有了“征實”的學術態度,但能夠從理學的重圍中突圍出來還需要能夠開風氣的大師出現。如上文所引,雖然當時從事文本考證的學者并不在少數,但真正能夠起到學術范式轉型作用的當推顧炎武。顧炎武的《日知錄》和《音學五書》為后世不僅提供了治學方法,而且開拓了諸多學術門類。另外,顧氏能成為清學開山人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被認為提出了綱領性的口號:“經學即理學。”而這樣的口號實是后來全祖望根據顧炎武的言論所總結出來的。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一文中評價顧炎武:
晚年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全祖望:《鮚埼亭文集》,黃云眉選注,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而顧炎武的原話是:
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而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貼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圣人之語錄也。”舍圣人之語錄而從事于后儒,此之謂不知本也。*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后人對這段話的理解分歧很多,而主要集中于對顧炎武是否要以經學取代理學的問題上:主張肯定說法的學者,傾向于顧炎武是乾嘉漢學名副其實的開山人物;主張否定說法的,傾向于漢學家并未真正繼承顧炎武的學術精神。而這里的關鍵又取決于對顧炎武這里的“經學”與“理學”的理解。從顧炎武認為“非數十年不能通”的“經學”來看,這正是后來乾嘉學者所標榜的漢學特征。而顧炎武所認為的“理學”則相對復雜,從“理學之名”“所謂理學”的語氣中可以看出,顧炎武并不反對“理學之實”,只不過認為雜于禪學的宋人沒有得理學之實。更為重要的是,其實顧炎武在這段話中并未給出確定的理學之實者。在這段話的前文中,他認為古之理學乃是非數十年不能通的漢學,而后文明顯推崇的則是“圣人之語錄”。或許顧氏自身也沒有意識到在這里他自己已將“漢學”與“經學”等而視之了。由此,后來明確標榜漢學的惠棟等人正是承接了顧氏這一不經意間的混淆。由于這樣的簡而等同,顧炎武作為漢學的開山地位也由此確立起來。
其實,顧炎武本人并不能預測自己會被后世推為開山。他區分“理學”與“經學”之別最終還是為了回到孔孟原典以完成他通經致用的學術旨趣。雖然他的大著《日知錄》被后世作為典范來效仿,但后人推崇的還是此書的考證方法。就此而論,乾嘉漢學對顧氏的繼承也只可謂是選擇性的繼承。如顧氏門人潘耒就曾明確指出:“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顧炎武:《日知錄》,黃汝成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但乾嘉學者推崇顧炎武與乾嘉學者在多大程度上繼承顧炎武并不構成矛盾。此外,我們并不能斷定乾嘉學者就毫無經世精神。只是,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經世致用的精神不過是又一次潛藏到了學術工作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