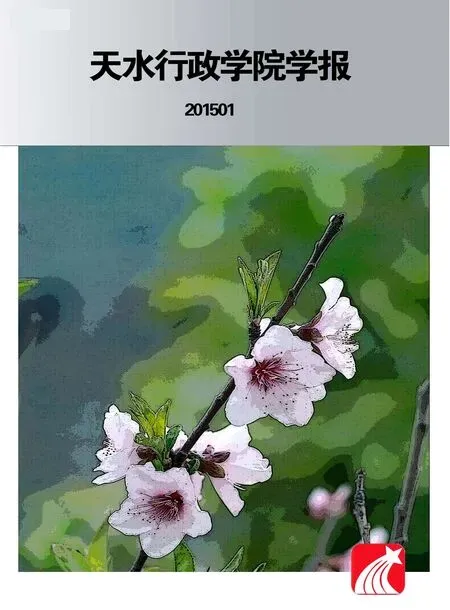論馮友蘭才、力、命思想
馬光耀
(中共天水市委黨校,甘肅天水741000)
論馮友蘭才、力、命思想
馬光耀
(中共天水市委黨校,甘肅天水741000)
馮友蘭先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于《新原人》一書中首次提出才、力、命思想,結合立言、立德、立功三個梯度闡述了對成功的獨特見解。筆者通過對馮先生才、力、命范疇的具體分析,力圖找出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并通過分析、歸納、對比、綜合的方法揭示成功因素的異同,剖析才、力、命思想的不足,探究成功的科學含義,以期揭示出當代人成功的共同性因素。
馮友蘭才;力;命;思想
人人都想成功,但真正成功的人卻不多,這是因為理解成功因素的科學含義的人很少,即使理解到位不能付諸實踐也是徒勞。馮友蘭的才、力、命思想,強調在學問上才占主要地位,在事功上命占主要地位,在道德上力占主要地位,有明顯的機械論傾向,筆者難以贊同,以下分析闡述之。
一、才與力
才,包括才學和天資兩個部分。馮友蘭對才的定義是:“一個人的天資,我們稱之為才。一個人在某方面的才的極致,也就是他的力的效用的界限。到了這個界限,他在某方面的工作即只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質的進益。”[1]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第一,才就是天資、天賦、先天具有的,馮先生是先驗論者、天賦觀念論者,當然這也屬于遺傳決定論的觀點,不盡科學。第二,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潛力也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這與當代科學中生理學所揭示的人的潛力是無限的觀點相反。“才是天授,天授的才須人力以完成之。就此方面說,才靠力以完成。但人的力只能發展完成人的才,而不能增益人的才,就此方面說,力為才所限制。人于他的才的極致的界限之內,努力使之發展完成,此之謂盡才。與他的才的極致的界限之外,他雖努力亦不能有進益,此之謂才盡。”[2]在才與力的關系上,后天的努力只能發展才的方面,而不能增益人的才。這實際上是他不懂得人的才干是在后天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光是頭腦里有才是不能起決定作用的;人必須在實干中才能增長才智。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實踐作為中介溝通了主客體,使人真正成為社會的人,實踐是人的生存方式。
力是指人的努力程度。“一個人的努力,我們稱之為力,以與才與命相對。力的效用,有所至而止,這是一個界限,是一個人的才與命所決定底。”[3]馮先生的觀點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反,他認為才與命決定力,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力決定才,而不是才決定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仍然是力。因為天資再好,不付諸行動仍然無濟于事。在此意義上,馮與孔孟一樣,是先驗論者,也類似西方哲學的天賦先驗論思想。“人的力常為人的才所限制,人的力又常為人的命所限制。”實際上這是他給人力主觀地劃定界限,使之服從于才與命,可見在知行關系上,馮是先知后行的代表人物。這也可以從他的《新理學》中最根本的“理”范疇類似于西方哲學中柏拉圖的“理念”范疇得到映證。
二、命與才、力
命運是表示個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命歷程的范疇,是作為主體的人與客體的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馮友蘭給命下的定義是:“一個人無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或不幸,沒有理由可說。”[4]生活在哪個家庭,哪個時代,不由我們選擇,也就是說個人出生的環境是既定的,這是人賴以生存的前提條件,對人的活動有巨大的制約或影響作用,所以無理由可說。“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制約著他們的一定環境中,是在既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5]生在一個各方面好的家庭,人的遭遇會好點,即幸運;反之,連基本的健康衛生條件都不具備,則算不幸,這里各方面條件指的是經濟條件,家長的智商、情商、教育背景、生活常識、健康衛生條件等綜合因素。他又說:“普通所謂努力能戰勝命運,我以為這個命運是指環境而言。環境是努力可以戰勝的,至于命運,照定義講,人類不能戰勝,否則就不稱其為命運,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遭遇才是命運。”[6]這里仔細分析起來,一方面,馮先生割裂了命運與環境的關系,才造成他最終得出不科學的結論。其實,命運與環境的關系十分微妙。在孩童時期,環境決定命運,而在成人時期,是人改變創造環境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6]因此,實踐是人的本質,人是實踐的產物。另一方面,馮先生認為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遭遇才是命運,也有其合理之處。馮先生又說:“這命不是一般迷信的命,就是機會,也可以說是環境。”在此,他將命解釋為機會,或環境。但一般指的是儒家的命,類似于“天命”,“儒家所講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變,而又非一人之力所奈何的。”并且他重述,“創造環境,爭取機會是屬于努力那方面,與這里的命無關。”從這段話可知,馮友蘭對命的解釋相當矛盾,一會兒說命運就是機會,也可以指環境,一會又說命指儒家的命,但顯然他側重于儒家的命。這幾種解釋顯然不同,如果說命是機會,那就要看你能否抓住它;但他又說,這屬于個人努力方面,與這里的命無關。這同樣割裂了命、環境、機會之間的辯證關系。他的儒家的命無非是對一些事的無可奈何,不可改變。其實人生有許多可以改變的命,而其中也有不可變的命,如先天遺傳決定了人的眼睛、身體是否健康,而后天環境更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健康的眼睛在惡劣的環境下被損害就是例證。總之,命本身是變與不變的統一,但總的規律是變的,這也符合辯證法的規律。馮先生給人人為地劃定一個界限“命”,讓人自守本分,這在本質上與儒家孔孟的宿命論思想一脈相承。周國平教授說:“命運主要有兩個因素決定:環境和性格。環境規定了一個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圍,性格則決定了他對遭遇的反應方式。”[7]筆者認為行為造就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在一定條件下決定命運;而正確的判斷力和果斷的行動才是決定命運的關鍵因素。
馮友蘭說:“一個人的命運的好壞,影響到他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的貴賤。”“一個人命的好壞,影響到他所作事的成敗。”[8]這是馮友蘭的經驗之談,也是常識。人的命運不同,環境不同,起點也就不同,身份地位自然不同,同時,身份地位高的人能辦成的事一般人卻辦不到。有些庸才成功了是命好,不是他的能力強。馮先生認為自然境界中的人對于其所做的事的成敗,亦不必有某種情感,這實際上否認了人是一個知情意的統一體。他把道家所處的境界歸為自然境界,而把儒家孔孟的境界尊奉為天地境界,確實有薄彼厚此之嫌疑,這說明他的立場是儒家一派的,他也以新儒家的代表人自居,企圖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地步。他指出“賢”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圣”是在天地境界中的人。顯然,他的“圣”與“賢”和古代的圣與賢不同。他又提到求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的主要功夫是致知用敬。用敬靠力,致知需才。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于天地境界與自然境界的劃分并不科學,有很強的主觀性與機械性。范鵬教授說:“境界說的理論基礎和前提是錯誤的。其實,沒有社會哪有社會之理,脫離了社會哪有個人之理。境界說的方法是錯誤的,純動機論的抽象繼承法產生了以文害意的惡果,對境界的機械劃分沒能反映出正逆向兩個方向發展的真實趨勢。”[9]很明顯,境界說理論與生活實踐的脫節是根本缺陷;但同時他又給人們設定了道德理想,讓人們明白精神價值尤其是道德價值的崇高地位,對于當代人的道德缺失似乎有所啟示。
三、學問、事功、道德
馮友蘭說“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功、立德。學問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運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10]筆者認為,學問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基本是科學的,已為大量事實所證實,但對于后面的說法不敢贊同。筆者仍以馮先生舉的例子為證來說明理由。“至于事功的建立,則是命運的成分多。歷史上最成功的例子是太祖高皇帝,劉邦因為項羽的不行而成功。”項羽之所以輸給劉邦是因為心機不夠,不會用人,即才力沒有充分發揮所致。對此毛主席有詩為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的評價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而馮友蘭卻將項羽的失敗歸于命運,并引用了項羽的《垓下歌》為證,說“‘時不利兮’是項羽毫無辦法,而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冊上很多,不勝枚舉。”[11]這樣的論證顯然不能成立。其實項羽的命運本來比劉邦要好的多。首先,項羽的叔父項燕是大將軍;而劉邦只是一介亭長。其次,項羽的軍事實力要遠比劉邦強大。項羽之所以會落得“時不利兮”的下場是他自己沒有抓住機會將劉邦置于死地,不會識人,不會用人,一再錯過機會所致。項羽的命運由好變壞是他一次次痛失良機,沒有正確的判斷力所造成的惡果。厚黑學大師李宗吾先生則認為項羽的失敗是因為臉皮不厚心不夠黑。項羽曾經用“破釜沉舟”之計擊敗秦軍,他也是有才的;所以不是項羽的命不好,而是項羽有才、力卻不會用,即沒有正確的判斷力,這導致他最后的命運不好。由此可見,馮先生對命運的定義存在誤解,有偏頗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些道理,有些“庸才”能夠成功的例子確實不少。這是由“命”即家庭環境好決定的。總之,不加分析地說“事功的成就需要命運的成分大”有失偏頗,實際上這是他強調天命而輕視人力,叫人“安之若命”罷了。
馮友蘭又說:“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這種說法未免失之簡單。“普通人以為圣賢需要特別在事功文學方面的天才,那是錯誤的,孔子和孟子成為圣賢和他們的才干沒有關系。”[12]這種說法顯然不對。眾所周知,孔孟之所以成為圣賢主要原因在于他們的才學高,怎么能說才與德沒有關系呢?至于孔孟的道德怎樣,我們當然不能像馮先生那樣不加分析地說是圣是賢,畢竟說是一回事做又另一回事,可能孔孟的道德并不怎么樣,他們自己說得到卻做不到,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道德起源于人們之間的需要,起源于民眾的生活實踐,它是歷史的、也是具體的。歷史的當然有繼承性和民族性,具體的是說時代性和現實性。即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而談道德,這樣的道德是被抽空的,也是不現實的,是強加給人的東西。首先,它貶低人的情感、欲望以崇尚理性,暴露出極端理性的不足。其次,它完全忽視了人的意志自由,只讓人選擇善;但是惡人往往選擇惡,并且以此為樂。由此可見,馮友蘭受孔孟儒學、宋明理學影響之深,他把傳統的道德抽空之后又想在新社會運用,即他所說的“舊瓶裝新酒。”其實道德是具體的、歷史的,離開具體的社會關系談道德必然失之玄虛。馮先生主觀地將道德架空意在以道德為目的,建構宗教式的哲學道德觀,這是不現實、不科學的,目標太高就會不切實際,“道德的實質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13]。筆者認為道德的本質是對人性善惡的反映,是對人心靈美丑的反映。“道德的本質是人格的呈現。”[14]首先,道德是主客觀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特殊意識形態,只靠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道德有其客觀性,不是只有主觀性。即不同的人道德層次不同,境界當然不同。其次,有些壞人也不會努力去成就道德,因為他們認為那樣一文不值,并且他們喜歡做一些不道德的事,還以此為樂。最后,要求每個人都成圣賢的愿望雖好,卻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與現實生活的實際情況大相徑庭。之所以會有這些缺陷是因為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而缺乏科學性。
馮先生對命的認識有個生動的比喻:“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與下棋時,對于一時所有之可能底舉動,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時,則我心中將來打和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預測底。所以,對于下棋之輸贏,無幸與不幸。而對于打牌之輸贏,則有幸與不幸。”[15]這段話中,“下棋對于一時所有之可能底舉動,我均可先知”說法顯然有問題。其實,棋力的高低主要決定于棋理與算路,棋力低的人往往不知棋力高的人下這步棋的意圖。這當然是不可先知的。棋力相當的人,雖可先知,但下棋的輸贏與運氣密切相關,包括當時的身體、心理狀態等因素,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簡單的說“下棋之輸贏,無幸與不幸。而對于打牌之輸贏,則有幸與不幸。”古人曾說過“人生一局棋。”這與馮友蘭“人生如打牌”的觀點截然不同;但其中的真意如何走好人生這盤棋中的關鍵幾步,人如何設計、計算人生的棋路,也有啟發意義。的確,人生由于個人遭遇不同,而不可能像一盤棋那樣雙方機會均等,在此意義上,馮先生的比喻比之更合理。
四、對成功的不同見解
季羨林先生認為,“成功=天資+勤奮+機遇”,并且認為“只有在勤奮努力上下功夫,天資、機遇都是天授的。”[16]王海明教授認為,“欲望與才力命德相一致,乃是幸福或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17]李金水認為,決定人生成敗的十六種因素分別是:細節、心態、品格、選擇、情緒、思考、時間、健康、誠信、目標、行動、說話、關系、自信、潛意識、眼光[18]。筆者認為這些觀點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對成功的理解都不全面。首先,成功是一個包含綜合因素的概念,不是簡單的套套公式就能付諸實踐。因為它所涵蓋的范圍極其廣泛,包括戀愛、婚姻、考試、工作、做事做人等多方面的內容,這就決定了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次,不同的人對成功有不同的理解。季羨林先生強調人力的作用;馮友蘭先生強調,才、力、命在不同方面地位不同;王海明教授強調欲望在成功中的首要地位;李金水強調成功的綜合因素,但至少缺少膽量這一因素。再次,其實成功是一門實踐科學,需要不斷地探索總結經驗教訓,需要經驗的積累,需要膽量和智慧,需要自信作為根基,需要正確的思維方式。這樣才能落實在行動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它更接近行為科學,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國外成功因素的研究中,早就有遺傳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之分,其中行為主義屬于環境決定論;而智商屬于遺傳決定論,情商屬于環境決定論。最后,成功是一個綜合學科的范疇,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解釋。科學主義把成功理解為使用工具理性、科學技術,人本主義把成功理解為滿足人本身的生存利益或心理需求,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有五種基本需求由低到高分別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由于需求層次的不同,成功的層次也就不同。實用主義把成功理解為有用,適應環境。精神分析學派認為成功在于如何發揮人的潛能。現代成功學大師拿破侖·希爾總結了十七條成功的法則,后來當代的潛能成功學大師安東尼奧·羅賓提出人人都有成功的潛能,就在于能否發現和開發這座金山;并提出成功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缺一不可,即想象成功、思考成功、相信成功、采取行動爭取成功[19]。自我心像心理學的創始人馬克斯威爾說:“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自我心像是個人精神上的觀念,或者是他們的自我圖像,是左右個性和行為的真正關鍵。”[20]綜上所述,成功是一個包含主客觀因素的范疇,實踐溝通了主體的人與客體的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就內在統一了主體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兩種觀點。換言之,在相同或相似的環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主體決定;而在不同的環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客體制約所致。這個統一的基礎是人的實踐活動。
[1][2][3][4][8]馮友蘭.新原人[M].北京:北京三聯出版社,2007.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周國平.人生圓桌[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9]范鵬.論馮友蘭的境界說[A].中國現代哲學與文化思潮[C].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10][11][12][15]馮友蘭.新原人[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3]肖群忠.倫理與傳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余瀟楓,張彥.人格之境—類倫理學引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16]季羨林.人生沉思錄[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
[17]王海明.倫理學與人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18]李金水.成敗不是偶然—決定人生成敗的16件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5.
[19]安東尼奧·羅賓.激發無限的潛力[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20]馬克斯威爾.你的潛能[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B261
A
1009-6566(2015)01-0121-04
2014-11-16
馬光耀(1971—),男,甘肅天水人,中共天水市委黨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