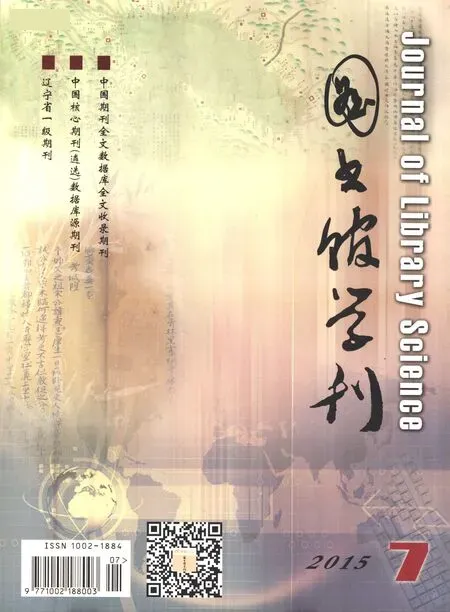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概況及其歷史貢獻
肖小娟 傅榮賢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概況及其歷史貢獻
肖小娟傅榮賢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對清代時期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來源、種類以及利用情況進行了概述,并結合歷史發展過程,對其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
蒙古地區清代寺院藏書
藏傳佛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傳入蒙古地區。當時統治蒙古族的宗教為薩滿教,在蒙古族人民中信眾普多,藏傳佛教也因由種種原因的限制,沒能在蒙古地區立穩根基,并隨著元朝統治的消亡而逐漸消失。16世紀后期。在當時蒙古族封建貴族的大力支持下,藏傳佛教開始廣泛傳播,逐漸有了發展壯大的基礎。在清朝,特別是從康熙到乾隆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優待政策與獎勵措施,扶持、保護和發展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和發展,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藏傳佛教不斷滲入到蒙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對整個蒙古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當時的蒙古地區寺院林立、名僧輩出,蒙古文、藏文佛教典籍的翻譯、著述、編纂、出版與傳播事業發展到頂峰,與之相適應,寺院藏書的內容、數量和規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1]。
1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主要來源
1.1寺院自行購置或抄寫得來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寺院以自己的方式,或從其他地區寺院迎請回各種經籍,或寺院的高僧學者抄寫的佛典以及撰寫或翻譯的與佛學相關學科的著作等。
1.1.1迎請購置得來的藏書
各種佛典經卷是寺院藏書的主體,從其他地區的寺院迎請各種佛教典籍,是蒙古地區寺院增加藏書量的主要途徑。蒙古地區各寺院從北京、西藏和青海等地區佛教圣地迎請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蒙古文《甘珠爾》和《丹珠爾》等的例子有很多。如:巴林左旗昭慈寺創建于康熙年間,轉世活佛共六世。第四世葛根吉格木德扎木蘇,于清光緒末年從塔爾寺(位于青海省西寧市)請回一部手抄本藏文金字《甘珠爾》111函,全書共15000余頁。包裝精美,用純金粉寫在磁青紙上,筆力剛健流暢,布局疏密得體,是罕見的珍貴文獻,現珍藏在赤峰市博物館[2]。
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支持藏傳佛教發展的同時,在經濟上也給予扶持,賞賜給各大寺院大量的錢財、糧食、土地、牧場和牲畜等,這是寺院收入來源之一。各個寺院,尤其是規模較大的寺院,會定期舉辦法會講經,來參加的信眾根據自身的經濟條件捐贈給寺院一部分財物,這是寺院收入的來源之二。此外,寺院的募捐、化緣、出租土地等也是寺院經濟來源的保證。有了經濟基礎,寺院根據自身需要,購買所需的經卷、修學之書等。此為蒙古地區寺院藏書來源的又一途徑。
1.1.2抄寫佛典以及撰寫著作得來的藏書
蒙古地區寺院以多種途徑進行寺院藏書建設,既重視對佛經的搜集,也重視對佛經的抄寫。僧侶、信徒等為做功德或為供奉、念誦經文,進行著名佛典的抄寫。如內濟托音在內蒙古東部區弘揚佛法時,就致力于佛典的抄寫。內濟托音從穆克丹(今沈陽)買來紙、墨、顏料等,召集書手抄寫《甘珠爾》經,依次抄完108函,也作為眾施主及弟子供養對象[3]。除抄寫的佛典之外,另一種藏書來源便是寺內僧侶等的著作。寺院主持、活佛知識淵博,他們以藏文或蒙古文撰寫、注疏或翻譯有關佛學以及歷史、哲學、文學、醫學、歷法、數學等相關學科著作,這些著作也是內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1.2政府頒賜和私人捐贈
清代統治者在政策上尊崇、保護佛教,刊刻了多部藏文大藏經,熱衷于頒賜名寺。如,清代完成滿文《大藏經》的刻印后,存藏多倫諾爾宗寺一部。又如,阿拉善左旗的延福寺,1731年寺內建一亭雙層八角樓,珍藏奈塘版《甘珠爾》全卷,是康熙帝所賜[4]。政府頒賜佛經典籍一般情況下均會作為“法寶”供奉,不會與常用的佛教典籍混排供念誦閱覽,無論其用處如何,頒贈的佛經也是清代內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來源之一。
清代私家刻書已成風氣,一些蒙古族的王公貴族虔誠信佛,熱心于蒙古文佛教典籍、高僧傳記等的翻譯。著述和刊刻出版,并會向寺院捐贈這些佛典,以示功德。這些私人捐贈是寺院藏書的又一來源。
2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種類
2.1佛教經典大藏經
大藏經是佛經典籍的叢書,又稱一切經、藏經和三藏經,是佛教經典——經、律、論3部分的總匯。大藏經分《甘珠爾》《丹珠爾》兩大類。《甘珠爾》稱佛部,是正經,收入經、律和密咒3個部分。《丹珠爾》稱祖部,是續藏,收入贊頌、經譯、咒譯3部分。由于大藏經是藏傳佛經的基本經典,因此對于蒙古地區各個寺院來說,購置一部大藏經是必不可少的。大寺廟每一個經殿都必須購置一部《甘珠爾》經和一部《丹珠爾》經。普通寺廟必須置有一部《甘珠爾》經和一部《丹珠爾》經。較小的寺廟,財力有限,資金缺乏,即便如此,也必須要購置一部《甘珠爾》經[4]。在蒙古地區,清末時期有寺廟1300余座,所藏大藏經1500部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古地區,只使用蒙語念經的寺院不多,在大的寺院中,只有烏拉特前旗梅力根廟使用純蒙古文。雖然也有一些寺廟藏文和蒙古文通用,但總體來說,蒙古地區的蒙古文大藏經數量不多,《甘珠爾》經約20部,《丹珠爾》經約10部。大量的大藏經使用的依然是藏文。
2.2修學用書
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寺院,它有別于其他地區的寺廟的組織機構便是“扎倉”。“扎倉”原為藏語,是“院”的意思,“扎倉”即為蒙古地區寺院僧人的學習之所。蒙古地區寺廟中設置的“扎倉”有“卻伊拉扎倉”(顯宗學部)、“卓德巴扎倉”(密宗學部)、“丁科爾扎倉”(時輪學部)、“滿巴扎倉”(醫藥學部)、“喇嘛日木扎倉”(菩提道學部)。各個扎倉有不同的學習內容,如“卻伊拉扎倉”(顯宗學部),是學習研究藏傳佛教經典教義的學部,要求僧人學習“五部大論”:《薩德麥占》(量釋論)、《溫巴爾道德貝占》(現觀莊嚴論)、《烏瑪爾朱各瓦》(入中論)、《都勒瓦》(戒律本論)、《溫貝勒昭德》(俱舍論)。入部的僧人按照順序研習這些著作,精通內容和理解其精神實質,并能達到會解釋和應用這些教義的程度才能被授予學位,然后進行更深層次的學習。又如滿巴扎倉(醫學部)是研習蒙醫、藏醫的學部。這個學部學習的經書內容很多,包括公元4世紀印度著名醫學家碧嘎備和碧拉孜入藏時傳入的《脈經》《藥物經》等5部醫典,7世紀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4種醫學論著,如《門介欽莫》等。但重點學習基本教典《居悉》(《四部醫典》),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好地掌握蒙醫理論和技術,還必須研習蒙古醫學方面的典籍,主要包括《都德澤色嘎爾》《滿嘎仁親忠乃》等[5]。蒙古地區寺院設立各個扎倉,供僧人學習進修,其所用典籍為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主要類型。
2.3其他佛典以及活佛名僧的著作
蒙古地區寺院藏書中,除上述的藏傳佛教經典大藏經以外,還收藏其他種類的佛教經典著作,如《金剛經》《般若波羅密心經》《回向王經》等。這些典籍與大藏經一起被寺院的僧人或供奉或作每日誦讀之用。與此同時,蒙古地區的寺院藏書中還包括著名的活佛或者名僧撰寫的著作,他們對佛典的注解,對其他語種佛典的翻譯,自身對佛教教義的感悟等。這部分藏書也是構成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種類之一。今在內蒙古阿拉善境內的“廣宗寺”,歷史上也被稱為“南寺”,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寺院。在南寺寺院殿堂中,藏有釋迦牟尼的《三十四本生傳》兩套上百軸,反映宗喀巴生平和傳記的《八十宗喀》3套上百軸,《倉央嘉措傳》1套十幾軸。
2.4唐嘎畫
唐嘎畫又被人們稱作“唐卡”。蒙古地區寺院的唐嘎畫是將蒙古繪畫風格與印度地區、西藏地區、尼泊爾地區的繪畫藝術融合起來發展而成。唐嘎畫通常懸掛在寺院的重要殿堂中,通常以布或者綢為材質,以勾勒、刺繡等方式,加以珠寶等飾品組成畫面,題材包括各類佛像、佛教故事傳記、宗教活動、佛教圣地等。由于唐嘎畫具有工藝精湛、藝術感強、色彩鮮明、內容紀實等特點,成為蒙古地區寺院的重要藝術裝飾品,同時也是寺院藏書中特別的存在。
3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利用
3.1供奉
寺院中所藏的佛典中有一部分是用來供奉的。在蒙古地區的寺院中常被拿來供奉的便是《甘珠爾》。如“福緣寺”于1742年(乾隆七年)建造。清廷賜名“福緣寺”。在大經殿內二層樓上供奉釋迦牟尼銅像和放置《甘珠爾》等經典[6]。被供奉的佛典多是來源途徑較為特殊,或采用的材質上乘。政府頒贈的佛經一般均會被當作“法寶”供奉。
3.2宗教活動所用
蒙古地區藏傳佛教最為常見的宗教活動是舉行法會。一些寺院中影響大、地位高的喇嘛辦講經大會,法會中講經所用佛典之外,寺院會給所來聽經的信眾發放一部分“開光”佛典,由信眾帶回去供奉。另一種利用寺院藏書的宗教活動是“轉經法會”。“轉經法會”是一種化緣形式,把《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中的一種經裝在棚車內,約十幾名喇嘛隨車送行,每到一個村落,就舉行誦經法會,信徒燒香叩頭,奉獻錢財等。在蒙古地區寺院藏書利用中最為普遍的宗教活動便是僧人誦經所用。誦經是寺院僧人每日必修的功課,誦經所用之書是寺院藏書中利用最為頻繁之書。
3.3研習所用
研習用書主要是利用寺院各個扎倉所藏之書。僧人按照各個扎倉要學習的內容,研習各部經典,融會貫通,然后參加考試,取得學位以后,便開始有了宗教地位和社會地位。可以說,蒙古地區寺院藏書的利用中,這部分藏書的使用較為廣泛,涉及內容也較多。
4 清代蒙古地區寺院藏書對蒙古族文化的歷史貢獻
清代,藏傳佛教寺院不僅是蒙古地區重要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更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各大寺院藏書內容豐富,尤其是寺院中設立的各個扎倉學部的藏書,更是包羅萬象。在藏書數量和規模方面為歷代之最,利用也極為廣泛。藏傳佛教寺院的僧人們在扎倉這樣的專業場所里利用所藏之書對宗教、文化、哲學、天文、數學、醫學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學習,把外界的優秀文化傳播到了蒙古地區,對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對蒙古地區的發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4.1文學方面的貢獻
清代蒙古地區在文學方面出現了許多藏傳佛教僧人學者以及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如《黃金史》的作者莫爾根葛根;《蒙古風情鑒》的作者羅布生卻登等。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是這些學者沒有僅止步在對佛教典籍的翻譯上,而是利用這些寺院所藏經典中的資料,積累匯編出了眾多的、流芳后世的經典文學作品。無論是早期的《內齊托音傳》《魔尸的故事》等明顯的以宗教因素為主的著作,還是后來的流傳于蒙古族人們中間的《格斯爾汗傳》,它塑造了一個為人們鏟除惡魔,給蒙古族人民創造了安靜祥和環境的偉大民族英雄的形象,富有濃郁的民族色彩,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蒙古地區民族文化藝術,是廣大蒙古族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但這些作品被創作出來的基本條件是蒙古地區寺院的各類型藏書,這些藏書為蒙古地區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貢獻。
4.2語言文字方面的貢獻
蒙古地區寺院所藏的大量經文多以藏文為主要的語言文字,研習佛法的僧人們為了自身修為的提升,想要接觸更多的佛教典籍就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因此在清朝年間涌現出許多精通蒙古語、藏語乃至梵語的僧侶學者,有力地促進了蒙古語語法研究、修辭研究等語言方面的進步[7]。蒙古“阿力嘎力字母”的創始人阿尤喜固什、“蒙古語法”的編著者阿旺達爾拉然巴都是著名的喇嘛學者,是優秀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在翻譯藏文經卷和相關作品中,蒙古地區的學者借鑒其語言文字的優點,不斷完善蒙古語,同時促進了各民族的語言交流。
4.3教育方面的貢獻
寺院教育是蒙古族的主要教育形式,而佛教的典籍就是寺院教育的主要教材。在清代的蒙古地區,蒙古族的一般教育形式為幼童在就近的寺院進行基本的識字教育,誦讀簡單的經文,稍大一些,接受完基礎教育以后進入較大的寺院開始學習“五部大論”。在研習佛學經典“五論”以外,還會進行其他方面的教育,如數學、歷算、天文等學科,具體教授的學科要看所在寺院開設了哪些“扎倉”。如乾隆三年(1738年)在五塔寺設《丁科爾扎倉》(時輪學部),現存于五塔寺殿內內壁上的石刻蒙文天文圖,就反映出了當時很高的天文水平。無論是學習佛教經典還是對其他學科的研究,其學習過程當中,寺院的藏書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4.4醫藥方面的貢獻
蒙醫有著悠久的歷史。蒙醫是隨著藏傳佛教進入蒙地區的印度、西藏、內地等醫藥技術,融合蒙古本土的醫術不斷發展形成的。而對醫學的發展來說,一部經典的醫學著作便是整個醫學界的靈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蒙醫學是吸收了《四部醫典》的基本理論,結合蒙古地區的特點,不斷調和發展而來的。另外,蒙古地區的大寺院都設立了“滿巴扎倉”(醫學部),其所藏醫學典籍眾多,并據此培養了不少著名蒙醫,這些蒙醫譯著了許多著作,《蒙藏合璧醫學》《醫學大全》《藥劑學》《脈診概要》等均為清代時期的著作,對蒙古醫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烏林西拉.內蒙古圖書館事業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3.
[2]德勒格.內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69.
[3]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蒙古佛經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80-81.
[4]多桑著,馮承均譯.多桑蒙古史[M].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43.
[5]德勒格.內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568.
[6]德勒格.內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224.
[7]寶玉柱.清代蒙古族寺院教育及其語言教育[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5):14.
肖小娟女,1990年生。黑龍江大學2013級圖書館學研究生在讀。
傅榮賢1966年生。黑龍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中心教授,碩士生導師。
G259.29
2015-03-30;責編:徐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