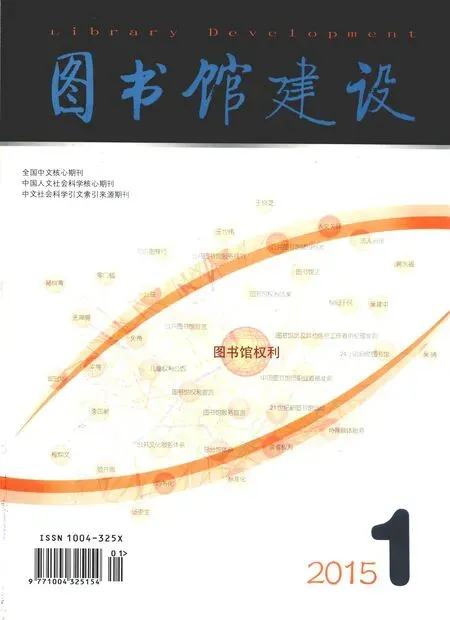《中圖法》G250和G350類目體系的修訂研究
李 敏
(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中圖法》G250和G350類目體系的修訂研究
李 敏
(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G250和G350類目體系經過4次修訂,通過擴張底層類目、增改類組、增加注釋及調整上層結構等方式,最終改為一體化設類,呈現出一個具有兼容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的高質量類目體系。這一體系如實記錄了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學科發展的歷史軌跡,積累了《中圖法》類表結構的改造經驗,構造了圖書情報一體化的理論基礎,描述了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各自的學科結構。繼續修訂既是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中圖法》發展的必然。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圖書館學 情報學 類目修訂
任何一部檢索語言,修訂是不可避免的。修訂的原因,既有可預測的因素,如與科學知識發展保持同步;也有不可預測的因素,如要容納大量的帶有時代觀念和經濟形態烙印的文獻主題。修訂工作,無論是對于被修訂的學科或專業的發展,還是檢索語言本身的進步,都很重要。對于體系分類法來說,每個學科類目體系的修訂,首當其沖的是處于學科第一層次的基礎理論部分類目,因為它要在宏觀層面上高屋建瓴般展示整個學科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發展狀況,準確傳播出該學科的基本觀念、本質、使命和體系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以下簡稱《中圖法》)至今已對G25和G35類目體系中的基礎理論部分G250和G350類目進行了4次修訂,筆者試圖在梳理這些修訂內容的基礎上,總結其修訂特點,進而闡明修訂對兩個學科建設和《中圖法》發展的意義,并提出續修建議。
1 修訂的主要內容
《中圖法》(第1版)編制于1971年2—1975年10月,在G25和G35類目下分設G250和G350兩個類目,子目各有4個和7個。對《中圖法》(第1版)的修訂始于1979年4月,于1980年6月出版了《中圖法》(第2版),修訂較簡單,即停用《中圖法》(第1版)立類不當、按觀點區分的G250類目下的3個子目和G350類目下的6個子目。1984年11月,《中圖法》編委會啟動了對《中圖法》(第2版)的修訂,于1990年2月出版了《中圖法》(第3版)。這次修訂以擴充、加細、增容為主,重新啟用修訂《中圖法》(第1版)時刪去的兩個空號,即G250.7和G350.7,但賦予新類名,并在G250.7下以注釋方式劃分了該類的內容范圍,指示其包含與不包含的內容;同時,恢復修訂《中圖法》(第1版)時刪去的G250.9類號及原類名,并對其增注,也在G250下增注。1996年7月,《中圖法》編委會開始修訂《中圖法》(第3版),于1999年3月出版了《中圖法》(第4版),修訂以局部調整、增加類目容量為主,即將G250.7和G350.7類目下的單一類名改成類組類名,在G250.7下擴出5個子目,豐富G250下的注釋說明。2007年9月,《中圖法》編委會開始修訂《中圖法》(第4版),于2010年6月出版了《中圖法》(第5版),修訂以整體合并、調整為主,兼顧部分類目的加深、擴細。其具體修訂方法有四種:①合并原G350、G250兩類系為G25下的“G250圖書館學、情報學”類目,再分“G250.1圖書館學”和“G250.2情報學”類目。G250.1類目下所設兩個同位類目均由《中圖法》(第4版)“G250圖書館學”類目下注釋生成;G250.2類目下設由5個子目構成的類列,包括由原注釋生成的類目和新增類目。新設的9個子目中的6個子目皆有內容注釋。②修訂部分類名,并增、補和改注,如將《中圖法》(第4版)的G250、G250.7、G250.71、G250.72、G250.9等類目的單一類名改為類組類名;在G250、G250. 71、G250.72類目下增注;補充G250.7類目的原注;改正G250.73原類名的概念語詞和注釋語句。③增新類并加注,如G250.78類目。④僅增注,如G250.74類目。
2 修訂的特點
2.1 改分立式立類為一體化設類,類目體系由分散混亂走向合并兼容。
《中圖法》1~4版皆將“圖書館學”和“情報學”設成性質相同或相似的類列,采用對應的排列方法。理論上,這種分立式處理方法能使兩學科類目分得更細、更清楚,兩類系下分別集中單純的圖書館學和情報學方面的文獻,便于精確檢索。但這也給既有圖書館學也有情報學、或探討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共性內容的文獻信息的歸類帶來一定的困擾。《〈中圖法〉使用手冊》雖有變通措施,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筆者以G250、G350類目及下位類號碼查詢國家圖書館中文書目數據庫,結果顯示:無論是從理論、方法還是技術上兼論兩個學科的文獻,都存在歸類混亂現象,原因與類目重復設置有關。另外,《中圖法》規定內容兼顧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文獻入圖書館學,人為造成G250類系號碼標引頻率遠遠高于G350類系號碼。長此以往,“情報學”類目將有可能失去文獻的保證。《中圖法》(第5版)采用一體化設置方式,將G35類目并入G25類目,下設“G250圖書館學、情報學”基礎理論類組,分子目“G250.1圖書館學”、“G250.2情報學”、“G250.7圖書館工作、信息工作自動化和網絡化”、“G250.9圖書館學史、情報學史等”;G250.1、G250.2、G250.7類目下又繼續細分。這一類目體系既可處理兩學科的共性文獻,也能標引單一領域文獻,真實地反映了兩學科的聯系與區別。
2.2 以底層擴張為主轉向底層擴張兼變動上層結構,加強了類目體系的科學性和實用性。
《中圖法》1~4版,G250和G350兩類系的頂級類目(即4級類目G250和G350),一直各自僅設1個,變化在于5級和6級類目。例如,《中圖法》(第2版)刪除按政治觀點所設的5級類目9個;《中圖法》(第3版)恢復了《中圖法》(第1版)的1個5級類目,增設2個5級類目;《中圖法》(第4版)保留了《中圖法》(第3版)的3個5級類目,在其中的G250.7類目下擴充5個6級類目。總之,類目增刪都針對底層。《中圖法》(第5版)不僅繼續擴張了5級、6級類目,增設7級類目3個,還將4級類目由2個減為1個,首次調整了G250類系的上層結構。這降低了《中圖法》修訂給圖書館藏書和目錄改編帶來的影響,也保持了與科學發展的同步,更適應了文獻增長的需要,滿足了用戶的需求。
2.3 除擴張類目外還以增改類組和注釋等方式提升了類目質量
提升類目質量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強化分類法的完備性,二是增強類目的兼容性和清晰度。如前所述,每次修訂皆有類目擴張,完備性大為提升。至于類目兼容性則主要通過增改類組而得以加強。例如,《中圖法》(第4版) 改G250.7和G350.7兩個單一類名為類組類名,在G250.7類目下新增2個類組子目;《中圖法》(第5版)G250類系中類組的設立已達8個。
另外,《中圖法》還采用了增添大量注釋的方式來提升類目的清晰度。例如,《中圖法》1~5版中G250、G350兩類系下有注釋的類目占類目總數的比例分別為9.1%、50%、80%、110%、183.3%,越來越密集的注釋不斷提高了標引的準確性和方便性。《中圖法》的修訂還注意豐富注釋類型。其中,最基本、最常見的注釋是內容注釋,《中圖法》1~5版中G250、G350兩類系中都有,并逐步增加;分類方法注釋則始于《中圖法》(第3版),《中圖法》(第4版)維持不變,《中圖法》(第5版)略增;類目沿革注釋雖然從《中圖法》(第4版)才設,但是在《中圖法》(第5版)中大增;《中圖法》(第5版)新設類目關系注釋,包括參見注釋3條、交替類目注釋1條。這些修訂提升了《中圖法》類目體系的編制質量和使用效果,也方便了標準化的著錄。
3 修訂的意義
3.1 如實記錄了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學科變化、發展的歷史軌跡
在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已初建自己的圖書館學理論體系,情報學的技術應用研究也已起步,但都偏重于政治立場的批判研究。文革末期出版的《中圖法》(第1版),就設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圖書館學”、“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情報學”等類目。70年代后期,隨著社會政治環境恢復正常,學科理論研究重點回歸到解決其基本理論問題和概念群的建立上,但爭議不斷。至于學科史的研究,圖書館學仍側重古代部分,情報學則歷史太短,皆未能成為支撐或支持現代學科理論的內容。因此,《中圖法》(第2版)刪除了《中圖法》(第1版)按政治觀點設置的類目、概念群類目和學科史類目。
80年代中后期,我國圖情界應用計算機技術在其管理和服務等環節建立了各類自動化系統;兩學科的研究開始走向實證研究階段,學科的研究方法成為熱點[1]。《中圖法》(第3版)就增設了“圖書館工作自動化”、“情報工作自動化”類目;將《中圖法》(第1版)的“圖書館學史”類目恢復,并增注“依世界地區表分”;將“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情報學研究方法”和“比較圖書館學”等納入注釋。這一類目體系基本反映出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基礎理論體系逐漸穩固的良好局面。
20世紀90年代,我國圖情界引入互聯網技術并產出大量的科研成果。CNKI(中國知網)數據庫收錄的發表于1990—1999年標引為“G250.7”的論文就有3 785篇,涉及圖書館集成管理系統、網絡資源開發與利用、數據庫建設和電子圖書館等。為此,《中圖法》(第4版)在《中圖法》(第3版)G250.7類目的基礎上擴建了一個將信息技術應用于圖書館領域的類目體系,改G250.7單一類名為類組類名,下設5個子目,容納已有和將有的有關圖書館工作自動化和網絡化方面的文獻,這表明信息技術的應用研究已成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必須拓展的領域。此時,情報學雖受“情報”改“信息”的沖擊,仍重技術研究,但其分支——文獻計量學已發育成長,既有研究成果,高校也開設了相應課程,并被列入《學科分類與代碼》(GB/T13745-92)中的情報學之下的三級學科。《中圖法》(第4版)在“G350情報學”類目下加注“文獻計量學入此”,及時反映了這一生長點。
進入21世紀,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基礎理論研究呈現三個趨勢:一是圖書情報一體化的研究日益深入,二是與現代信息技術和電子信息網絡環境內在聯系的研究繼續加強,三是關注與人類社會文明建設內在聯系的研究[2]。《中圖法》(第5版)的做法是:①搭建了一體化的類表。②完善圖書情報工作的技術性和網絡化的應用研究類目,修訂G250.7類名并繼續擴細。③掙脫側重于圖書館學和情報學本身立類范式,新設“G250.15圖書館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類目,在注釋中羅列發展中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群;新設“G250.25情報學分支”類目,將成長中的比較情報學和競爭情報學列于注釋中;將信息計量學、信息經濟學和專科情報學列為正式子目。
總之,《中圖法》1~5版對類目的設置及修訂,皆來源并服務于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發展、變化。
3.2 積累了《中圖法》類表結構的改造經驗
分類法為了保持與知識發展的同步及容納不斷增長的文獻,除不定期增補類目外,還需要有計劃地改造類表結構。國外分類法類表改造的成功案例有兩種:一是BC2(Bliss Bibliography Classification,布利斯書目分類法)對BC的改造,直接改變分類法的編制方式;二是DD C(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杜威十進分類法)編制鳳凰表,在保持基本編制方式下,每版徹底重編一至兩個大類,但保留原大類號碼。《中圖法》的修訂一直堅持相對穩定的原則,至今對類表結構的改造共有三次:《中圖法》(第2版)的教育類表由“國家——各級各類教育”列類改為“各級各類教育——國家”列類;《中圖法》(第3版)的法律類在《中圖法》(第2版)以“國家——法學部門”編列的D9類表基礎上,再增第二類表——以“法學部門——國家”編列的DF類表;《中圖法》(第5版)對圖書館和情報學類表的合并是一種新的探索,即將G25的類名改為“圖書館事業、信息事業”,然后通過增新類、改類名、增注釋及設交替類等方式將G350/359類表整合到G250/ G259類表中,同時,新增同位類“G254.9信息檢索”,容納《中圖法》(第4版)的“G252.7文獻檢索”、“G354情報檢索”、“G254.32目錄體系”、“G254.33各種目錄組織法”、“G353.21題錄、索引(編制)”、“G356.6機械化、自動化編索引”以及智能檢索系統、搜索引擎等的組織、構建及檢索方法等內容,刪除G35類表。如此,《中圖法》(第4版)中的圖書館學類表所含的159個類目和情報學類表所含的75個類目合并為《中圖法》(第5版)中的G25類表的161個類目。這種整合,既給體系分類法跟上時代步伐而進行類表改造積累了經驗,也給《中圖法》“瘦了身”。
3.3 構造了圖書情報一體化的理論基礎,為將來圖書情報檔案的進一步融合做了鋪墊。
如果說,20世紀末及之前討論并認知的是圖書情報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中圖法》(第3版)和《中圖法》(第4版)僅在《中圖法》的“G250圖書館學”類目下加注“圖書情報一體化著作入此”是可行的。那么,21世紀,在實踐與理論的不斷匯聚交叉中所呈現的學科間的融合之勢及所形成的學科增長點,分類法應如實給予揭示。因此,《中圖法》(第5版)搭建了一個四層的圖書情報一體化理論框架:首層為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共有的基礎理論(G250);二層是圖書館學和情報學各自的理論基礎(G2 50.1、G250.2)、兩學科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研究(G250.7)及學科史(G250.9);三層是圖書館學研究方法(G250.13)、應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或方法而形成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群(G250.15),情報學研究方法(G250.23)、應用其他學科和情報學的理論或方法而形成的情報學分支學科(G250.25),現代技術應用于圖書館和具體信息工作領域的研究(G250.71/.78);四層是情報學應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或方法而形成的綜合性分支學科(G250.252、G250.253、G250.255)。這樣的理論基礎,既表明圖書館學和情報學融合發展的趨勢,也讓兩學科在某些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發展點,還支持了一體化實踐。更重要的是,“G250”類目下增“參見G270、G203”注釋,將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學、信息管理學捆綁得更加緊密,為將來它們之間的交叉融合、協同研究做了很好的鋪墊。
3.4 描述了圖書館學和情報學深度分化、邊緣綜合、層次拓展的結構體系,指明了今后的發展方向。
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圖書館學學科體系結構的研究進入發展期,提出觀點近40種、模式3種、類型56種[3]。在這種爭鳴不斷的環境中,《中圖法》3~4版對圖書館學結構體系的反映就僅在“G250圖書館學”類目下以注釋的方式簡單羅列了發展相對成熟的分支學科,自然也就沒有層次和系統。21世紀以來,圖書館的形態和研究內容都有很大擴展,跟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有本質聯系的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紛紛被引入,原有的分支學科逐漸成熟,新分支學科也在成長。因此,序化這些日益豐富、充實的分支學科群,進而揭示它們發生、發展的內在規律及相互的聯系,成為《中圖法》(第5版)的任務之一。《中圖法》(第5版)先依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將圖書館學分為兩門類: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應用圖書館學依應用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分三類分支學科群:①應用一般研究方法,正在成長的分支學科,設G250.13類目;②應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或方法而形成的分支學科,設G250.15類目;③應用現代技術而形成的分支學科,與情報學合并設G250.7類目及子目。
20世紀80—90年代,學者們就開始探討情報學的生長點以及易產生新科學的領域,但沒能與實踐充分融合,《中圖法》1~4版也就沒反映情報學的結構體系。伴隨現代信息技術在情報學的廣泛應用,新的學科增長點不斷涌現,將情報學的分支學科和新的研究領域序化成一個有機系統,才能保證情報學的可持續發展。《中圖法》(第5版)完成了這一任務:首先,遵從大多數學者從80年代以來一直贊同的劃分方式——理論與實踐的關系[4],分出情報學的兩大門類,即理論情報學和應用情報學。其次,將應用情報學按應用的不同理論、方法和技術分三個分支學科群:①一般研究方法應用于情報學而產生的研究領域,即G250.23類目。②將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成功地移植到情報學,并與情報學特有方法結合、滲透而形成的情報學分支,以及情報學的理論與方法深入應用到某一具體領域進行專門的研究而產生和形成的特定分支學科,即G250.25類目及子目。③自動化技術、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應用于情報學而產生的新的研究領域,與圖書館學合為G250.7類目及子目。
以上對兩個學科的結構體系的處理,雖不盡完善,但卻貫徹了《中圖法》一貫的從總到分和依學科的應用而列類的原則,基本反映了兩學科體系構成的基本元素、相互配合和聯系以及學科的整體發育過程,指明了它們今后的發展方向和研究任務,滿足了各橫向分支學科和縱向分支學科的研究需要。
4 續修的建議
圖書館學理論部分。首先,“比較圖書館學”是一般研究方法中的比較研究方法應用于圖書館學后產生的分支學科,按其源流應歸入“G250.13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類目下。其次,“圖書館管理學”是管理學理論與方法應用于圖書館學后產生的一門交叉學科,《中圖法》(第3版)最早設于“G251圖書館管理”注釋中,《中圖法》(第4版)照舊,《中圖法》(第5版)新設G250.15類目來囊括其他學科理論與方法應用于圖書館學而產生的分支學科群,但“圖書館管理學”仍被置于“G251圖書館管理、信息工作管理”類目下,難以理解。再次,“專門圖書館學”是應用邏輯方法中的演繹法,將一般圖書館學理論運用于特殊對象而形成的分支學科,包括公共圖書館學、學校圖書館學等。在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合編的《圖書館學基礎》(1981、1991年)、周文俊的《概論圖書館學》(1983、1993年)、吳慰慈的《圖書館學概論》(1985、2002、2008年)和《圖書館學基礎》(2004年),以及錢亞新、沈繼武、黃宗忠、馬恒通等的論文中都給予明確。鑒于該分支學科群的實際研究還未與理論認識完全融合,筆者建議先給其在G250.1類目下設一個交替類目,正式類目則設在“G258各類型圖書館、信息機構”。這既符合分類法立類的發展原則,引起更多的關注、重視和深入研究,達到完善圖書館學的學科結構的目的,也對應了“專科情報學”類目。
情報學理論部分。筆者認為,首先,可在“G250.2情報學”類目下加注“理論情報學入此”,表明理論情報學的客觀存在;其次,同樣也將“比較情報學”改注在“G250.23情報學研究方法”類目下;再次,在“G250.252信息計量學”類目下注釋中增“網絡計量學”。1997年由T.C.Almind提出的網絡計量學[5],是“采用數學、統計學等各種定量方法,對網上信息的組織、存貯、分布、傳遞、相互引證和開發利用等進行定量描述和統計分析,以便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6]。它既是在傳統文獻計量學的基礎上擴展和演變而成,也是信息計量學研究對象和范圍進一步擴展到網絡領域的必然,應在“信息計量學”注釋中加以說明。
此外,《中圖法》(第5版)“G250.74 數據庫建設”類目下僅注“文獻庫的方法”,過于簡單。目前,圖書館和信息機構對于數據庫建設,雖重點針對文獻數據庫(如書目數據庫、專題數據庫和特色資源數據庫等)建設,但還引進各種類型數據庫并與自建文獻數據庫整合以提供數據庫的集成服務,該類目注釋應完整反映這一實況。對于初設于《中圖法》(第4版)的“G250.76 電子圖書館、數字圖書館”類目,《中圖法》(第5版)僅修正注釋是不夠的。我們分別以“G250.71/.74”、“G250.76”和“G250.78”類號查詢國家圖書館的書目數據庫,G250.76的標引頻率為245次,其他5個同位類類號的標引頻率僅在1到2位數之間。依據立類需遵循文獻保證原則的要求,G250.76類目應適當細分以滿足標引的實際需要。國家圖書館所藏數字圖書館文獻的主題主要涉及體系結構、資源建設、服務模式、版權、評價以及項目的研究與建設等,這可作為G250.76擴張子目的依據。另外,筆者以“電子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兩個主題概念查詢CNKI(中國知網)中文期刊數據庫,精確匹配后發現它們在論文中出現的頻次為:1979—1993年,“電子圖書館”11次,“數字圖書館”0次;2000年,使用“數字圖書館”的文獻量為788篇,是使用“電子圖書館”的3倍以上;2013年,“數字圖書館”為1 723次,是“電子圖書館”的16倍。因此,使用“數字圖書館”的文獻已成主流,G250.76類名應及時修正。《中圖法》在為類目配號時,一般會對類目中具有相同內涵的要素配以統一的號碼,這是配號的助記性和邏輯性的要求。例如,學科的研究方法,尾號一般是“3”;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往往特設尾號為“-05”,等等。但《中圖法》(第5版)在配置圖書館學、情報學兩個學科號碼時沒有遵循這一習慣。
綜上所述,筆者的具體建議如下,與《中圖法》(第5版)類表相同的部分用省略號代替:
G250 圖書館學、情報學
......
G250.1 圖書館學
理論圖書館學入此。
G250.1-03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
比較圖書館學入此。
G250.1-05 圖書館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圖書館管理學、圖書館經濟學......等入此。
[G250.12] 專門圖書館學
宜入G258。
G250.2 情報學
理論情報學入此。
G250.2-03 情報學研究方法
比較情報學入此。
G250.2-05 情報學分支
競爭情報學入此。
G250.2-052 信息計量學
目錄計量學、文獻計量學、情報計量學、網絡計量學等入此。
[G250.2-053] 信息經濟學
......
G250.2-055 專科情報學
.......
.......
G250.74 數據庫建設
文獻數據庫的建設和使用方法入此。各類數據庫的整合和使用等入此。
G250.76 數字圖書館
總論入此。電子圖書館、虛擬圖書館和復合圖書館等入此。專論入有關各類。
G250.761 數字圖書館的體系結構
G250.762 數字圖書館的資源建設
數字資源引入、儲存、組織和管理等入此。
G250.763 數字圖書館的服務模式
G250.764 數字圖書館的評估
G250.765 數字圖書館的項目研究與建設……
[2]楊文祥, 周 慧. 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歷屆全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會議回顧與21 世紀圖書館學理論研究思考[J]. 大學圖書館學報, 2008(2):2-7.
[3]馬恒通, 趙衛利. 新中國圖書館學體系研究六十年[J]. 圖書情報工作, 2010(23):23-28,132.
[4]徐 涓, 陳 欣, 李曉菲. 情報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及問題芻議[J].情報雜志, 2008(1):86-88.
[5]Almind T C, Ingwersen P. Informetric Analysis on the World Wide Web: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Webmetric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7(4):98-106.
[6]邱均平, 段宇鋒, 陳敬全,等. 我國文獻計量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J]. 科學學研究, 2003(2):143-148.
Revision Researches on Class Systems of G250 and G350 i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C)
Class systems of G250 and G350 i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C) have been revised 4 times.Through expanding the bottom class, adding and changing the class unit, adding the class annotation, and adjusting the supstructure, and so on, two class systems change into the integration setting class mode, and show the high quality class system with the compatibility, the scientificalness and the practicability. The system truthfully records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ccumulates the reform experience of the table structure of CLC,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ound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both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describes respective subject structure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inuing to revise is the need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CLC.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C);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Class revision
G254.12
B
李 敏 女,1966年生,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信息組織。
2014-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