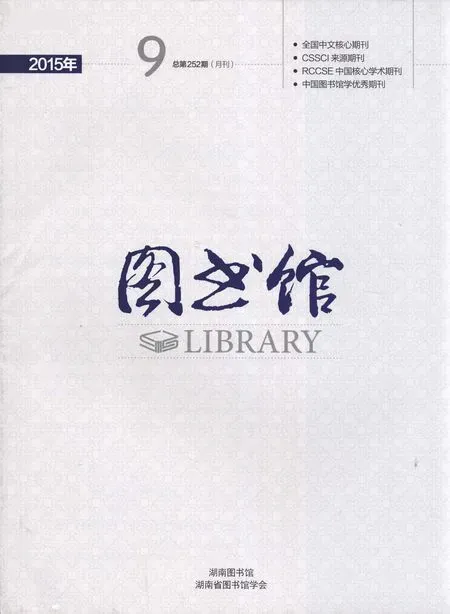對本科圖書館學專業《古典文獻學》課程教材的反思*
傅榮賢(黑龍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爾濱 150080)
對本科圖書館學專業《古典文獻學》課程教材的反思*
傅榮賢
(黑龍江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爾濱 150080)
〔摘 要〕古典文獻學是我國高校本科圖書館學專業必修課,但由于迄今尚無針對本專業的教材,因而只能將文史性質的相關教材直接“拿來”作為教學用書。而文史性質的教材直接施用于圖書館學專業,存在“與其他課程內容交叉重復”、“不能為古代圖書館學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撐”、“無力回應圖書館面臨的現實古籍整理問題”、“沒有達成與現代圖書館學的學理融合”等明顯不足,值得認真反思。
〔關鍵詞〕古典文獻學 教材內容 圖書館學專業
我國高校本科文史哲專業與圖書館學專業都開設了文獻學必修課。同中有異的是,中文、歷史、哲學等專業都有針對各自學科特點的教材,分別是: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而圖書館學專業迄今尚無針對本專業的教學用書,因而只能拿著或中文或歷史或哲學的教材來講授。例如,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張三夕教授主編的《中國古典文獻學》[1]因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而成為近年來圖書館學專業《古典文獻學》課程的首選教學用書。盡管,該書封面明確指出了其“文學史系列教材”的學科背景與專業身份。
筆者從事圖書館學《古典文獻學》課程教學歷有年所,深感在教材選用上因學科背景與專業身份的錯位而導致的教學效率的低下,遂于2013年申請了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面向圖書館學專業的《古典文獻學》教材建設研究”。總體上,該項目研究主要包括兩大基本內容:第一,指出文史哲背景的教材施用于圖書館學專業存在哪些問題?第二,如何建構一部面向圖書館學專業的《古典文獻學》教材?限于篇幅,茲擬聚焦于對第一個問題的討論。而為了行文方便和論述集中,本文主要分析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移植到圖書館學專業教學中存在的問題。當然,這不是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本身的缺失,而是指作為“文學史系列教材”,被生硬地切換到圖書館學專業之后滋生的不足。
1 與其他課程內容交叉重復
“古典文獻學是一門講如何對古籍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學問”[1],內容包括古籍的載體、類型、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等方面。這些內容與文史哲專業開設的其他課程基本不存在交叉重復的現象,因而也具有相對的自足性和合理性。但當為中文專業量身定做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直接施用于圖書館學專業的教學時,則與圖書館學普遍開設的“目錄學”、“書史與圖書館史”、“社科文獻檢索”等專業必修課程存在大量交叉重復的內容,從而導致圖書館學專業課程資源的重復與浪費,也因內容上的似曾相識而令學生生厭,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首先,“目錄學”是古典文獻學的重要內容,在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古典文獻的目錄”也被獨立為專門的一章(第二章)予以介紹。但“目錄學”本身也是圖書館學的專業必修課,武漢大學彭斐章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目錄學教程》[2]則是全國圖書館學專業目錄學課程的首選教材。而彭著《目錄學教程》的內容雖然廣泛延及“西方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書目控制”等方面,但其中作為重點章節的第二章“中國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基本包含了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古典文獻的目錄”的幾乎所有內容。
其次,“書史與圖書館史”也是圖書館學的一門專業必修課,武漢大學謝灼華主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3]則是全國高校圖書館學專業普遍采用的教學用書。正如該書書名所揭示的那樣,謝著包括中國的“圖書史”和“圖書館史”兩大部分。其中,“圖書史”部分廣泛涉及古典文獻的載體形式、古典文獻的傳抄方式、古典文獻的類型、出土文獻等方面,而這些內容在《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基本都有大同小異的介紹。
再次,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中的第七章“古典文獻的標點”、第八章“古典文獻的注譯”與圖書館學專業開設的古代漢語課程;第九章“古典文獻的檢索”與圖書館學專業開設的社會科學文獻檢索課程,也存在基本雷同的內容。
總體而言,現代圖書館學作為西方學科化的產物,是晚清以后“東漸”到中國的。而以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為代表的文獻學教材則基本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學術特色。如何從學科整體的高度合理規劃圖書館學專業《古典文獻學》的學科邊界和內容框架,從而避免與其他課程的交叉重復,值得業界認真思考。
2 不能為古代圖書館學研究提供史料支撐
古典文獻學是一門史料之學,重點討論如何從史料的全面、準確以及可獲得性的角度,為具體學科史的研究提供文獻保障。所以,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在具體章節編排中,十分重視其“文學史系列”的專業背景。例如,在第一章第一節“古典文獻的類型”中,作者“考慮到本教材使用的對象主要是中文專業的同學”[4],因此,對文獻類型的分類“側重于古典文學文獻”[5]。相應地,“總集”、“別集”等明顯屬于古典文學范疇的文獻類型,成為該節討論的重點。甚至所舉例證也緊扣中文專業,如對“專科性叢書”的介紹,主要“就涉及古典文學某一文體和類別的叢書而言”[6]。同樣,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7]則十分重視古代哲學的史料挖掘與梳理,如有關老子《道德經》的版本即涉及河上公本、王弼本等傳世文獻以及上世紀70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甲、乙兩種寫本《老子》。而晚近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則進一步將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老子》甲乙丙三個竹簡本悉數收羅在內。
與文史哲專業的學科史研究一樣,全面挖掘和嚴格考訂史料,也是中國古代圖書館(學)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但是,面向文史哲專業的古典文獻學教材,主要討論有關文學、史學、哲學等學科的史料問題,基本不涉及圖書館(學)史的研究史料。例如,輯佚是古典文獻學的重要內容,而我國古典目錄學的奠基之作——西漢劉向的《別錄》和劉歆的《七略》——皆亡佚于唐末五代,今人所見《別錄》、《七略》佚文,實為自清人洪頤煊(1765— ?)以來包括嚴可均乃至近人章太炎等學者鉤稽輯錄的結果。同樣,現存第一部相對完整的中國古代圖書館學著作——南宋程俱的《麟臺故事》——也是清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從明代類書《永樂大典》中輯佚而出。然而,現有教材在有關“輯佚”章節中,對這些古代圖書館(學)史研究無可回避的重要史料,皆未提及片言只語。又如,1972年銀雀山漢簡、1973年馬王堆漢墓帛書和1993年尹灣漢簡等考古發現中,都出土了“一書目錄”(contents),它們與群書目錄(bibliography)并不等同,從而為研究古典目錄的形制和源起等問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但現有教材亦視若無睹。再如,與古代圖書館(學)直接相關的史料廣泛分布在歷代官錄史志及志書、歷代圖書著錄文篇、私家撰述書目提要、書院藏書章程、名家藏讀敘傳等文獻中,但現有教材對這些直接關涉圖書館(學)史的材料也沒有任何關注。這再次證明,這批教材是面向文史哲專業的,具有明顯的學科傾向和專業“偏見”,因而并不能直接“拿來”施用于圖書館學專業古典文獻學課程的教學。
總之,現有教材的文史哲背景決定了其章節安排和具體內容不能直接回應古代圖書館(學)史的相關史料支持問題。相應地,學生在系統學習了作為史料之學的古典文獻學之后,對于從事古代圖書館(學)史的研究仍無實質性的助益,從而也與古典文獻學“作為一門史料之學”的學科宗旨,形成了頗具諷刺意味的吊詭。
3 無力回應圖書館面臨的現實古籍整理問題
圖書館學具有實踐依賴性,需要直接面向圖書館的古籍集藏、著錄、編目、分類等現實問題。1987年,洪湛侯曾經提出“體、論、史、法”的古典文獻學四大體系[8],其1994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新編》[9]一書即循此思路,將全書分為形體編(文獻的載體、體裁、體例)、方法編(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編纂等文獻整理方法)、歷史編(文獻學史)和理論編(文獻學理論)四大部分。然而,洪先生的“法”或“方法編”,所關注的內容仍是文史哲意義上的,與圖書館面臨的現實古籍整理之“法”或“方法”并不一致。而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等教材,對圖書館古籍整理之“法”或“方法”同樣也措意無多。我們知道,一般圖書館都或多或少收藏有一定數量的古籍,而自2007年文化部委托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推行中華古籍保護文化工程以來[10],全國范圍的古籍普查和整理工作全面鋪開,圖書館古籍工作人員亟需有關古籍著錄、古籍版本、古籍分類、古籍目錄組織、藏書組織與保管等方面的技術方法和業務知識。
例如,古籍著錄事項即包括書名項、著者項、版本項、稽核項、附注項、提要項、版本項等內容,對各“項”內容的分析和著錄都有具體規范和要求。以書名項而言,即存在諸如一書有多卷,各卷題名不同;一書有異名或前后題名不同;書名前帶有欽定、御纂、新刊、繡像、增廣、皇朝、國朝、勝朝、昭代等冠詞;只題篇名而不題書名;原書沒有書名等等,情況十分復雜。但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等教材面向文史哲專業,對圖書館古籍工作人員必須掌握的這些業務技能,根本沒有任何涉及。再如,關于著者事項的著錄,涉及著者朝代的確定(有些還涉及跨時代,如馮夢龍生于明萬歷年間死于清順治年間),著者姓名前冠以籍貫、官銜、職務、封爵、字號、別名,以政府機關(衙署)名編撰的文獻,偽題著者,佚名著者,注解類文獻既有原書著者又有注解者(如《毛詩正義》為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僧侶之作,二人或多人合作,外國作者,合刻多人著作等等,情況同樣復雜,端緒易至茫如。這就需要專門知識技能的學習和培訓,才能勝任古籍著錄工作。然而,張著《中國古典文獻學》等文史教材根本不能提供相關的知識和技術支持。
總之,現有教材因面向文史哲專業而缺乏圖書館古籍整理的實踐指向,系統學習了古典文獻學課程的圖書館學專業的學生,根本不能應付裕如地面對圖書館古籍收集與整理工作的實踐。
4 沒有達成與現代圖書館學的學理融合
作為“圖書的館”的圖書館,既包括圍繞“圖書”而展開的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內容,也包括圍繞“館”而展開的圖書館與社會文化的關系、館員與讀者乃至圖書館建筑設計等內容。就此而言,集矢于“文獻”的古典文獻學,構成了古代圖書館學的核心。但面向文史哲的古典文獻學教材以“史料之學”為基本定位,努力為各自學科的專業研究提供材料基礎,從而確保材料與研究結論之間的直接對應。這樣,文獻之“學”實際上就局限在了“物證”的層次,并體現為一種“材料決定論”甚至“實物決定論”的取向。例如,長期以來,《孫臏兵法》一直被認為是偽書,但1972年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的出土以“物證”的形式證明其并非偽書。然而,材料或實物本身是感性的、不確定的,設想如果《孫臏兵法》沒有出土,那它會不會還被視為偽書?無疑,文史背景的文獻學還停留在亦步亦趨于材料或實物的盲目狀態,本質上是一種受材料或實物左右的經驗論語境下的研究,缺乏足夠必要的表達深度,更遑論建立在概念和范疇基礎上的理論體系的建構。總之,由于缺乏理論自律,直接導致了文史背景的古典文獻學教材之學理積淀的貧弱,這不僅不符合一門“學科”的基本要求,其話語體系也與現代圖書館學嚴重脫節。
而圖書館學是廣義信息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關注信息的生產、傳遞和利用過程。在圖書館學的學科視野下對有關古籍材料進行專業學科范圍內的科學認讀,有助于認識文獻學的本質,提升文獻學的學理層次。例如,現代圖書館學認為,文獻實體結構可以分解為物理形態(物質材料和符號形式)與信息內涵(語法、語義、語用信息)兩大部分。[11]讀者接觸到的雖然是文獻,但其真正接受的卻是信息內涵。因此,文獻利用的實質就是文獻信息的被利用。這一基本思路提醒我們:對古典文獻之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等內容的考察,“不能停留在文本(本、篇、章、節)的層面,而必需深入到文獻背后的知識概念,以及文章的章節、片斷、語句、關鍵詞等信息層次。而現代圖書館學有關信息單元的切分、信息計量、信息傳播、信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保存、信息數據庫等認識成果,無疑為文獻學研究從文本層次深入到文獻信息層次提供了學理依據與技術支持”[12]。又如,從圖書館學意義上的“作者當初構想的文本”與“讀者實際所得文本”之間的關系入手,有助于揭示“偽書”的本質,從而顛覆目前關于“偽書”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再如,從圖書館學意義上的“文獻保障原則”出發,有助于認識文獻輯佚的本質。由此,輯佚也不再只是佚文、佚篇或佚書的搜集問題,而變成了潛在史料與學術結論之間既直接對應又間接相關的辯證“關系”問題。可見,接受現代圖書館學學理規約的古典文獻學既能夠將文史意義上的文獻學提升為一門深具學理品位的學科;也能夠站在圖書館學本科專業課程總體系的高度,強化不同課程之間的意義關聯,古典文獻學將不再是一門與圖書館學專業其他課程貌合神離的所謂“專業”必修課,而是成為圖書館學整體課程框架中的一塊有機拼圖。
總體上,迄今有關古典文獻學的學科體系主要是由文史背景的學者建構的,因而缺乏圖書館學視野,未能從圖書館學的角度說明問題。就圖書館學界而言,學者們亦未形成利用圖書館學成果研究文獻學的學術自覺,而只是處于簡單化地將文史學科背景的文獻學研究成果摘抄、移植到本學科領域中來的初級階段,由此導致文獻學與圖書館學之間兩不相師、互不聞問的分離狀態。文獻學與圖書館學缺乏共通的學術表達方式,兩者的成果無法實現交流與共享。
誠然,“批判舊世界”是為了“建立新世界”。條陳文史背景的古典文獻學教材直接“拿來”應用于圖書館學專業文獻學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是為了構建面向圖書館學專業的、量身定做的古典文獻學教材。至若如何建構,筆者有另文專論。
(來稿時間:2015年4月)
參考文獻:
1, 4-6.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彭斐章.目錄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修訂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7.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2
8.洪湛侯.古典文獻學的重要課題:兼論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杭州大學學報,1987(2)
9.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10.周和平.明確思路,精心部署,努力開創我國古籍保護工作新局面:在全國古籍保護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國家圖書館學刊,2007(2)
11.黃宗忠.試論文獻信息學.圖書情報知識,1999(4)
12.羅賢春,姚明.新時期我國圖書館學研究流派分析.圖書情報工作,2014(9)
〔分類號〕G256
〔作者簡介〕傅榮賢(1966-),男,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信息資源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發文110余篇,研究方向:古典目錄學。
*本文系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面向圖書館學專業的《古典文獻學》教材建設研究”(編號:2013D21)成果。
Reflecting on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Material of Library Science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Fu Rongxian (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is required course of undergraduat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ese University, but due to not yet for this profess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 can only use re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at direct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specialty faces some realistic problems such as “overlapping with other curriculum content”, “can not provide historical data support for 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 “unable to respond to library realistic problem about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can not realize academic fusion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 This is worth of serious reflection.
〔Keyw ords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Library science special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