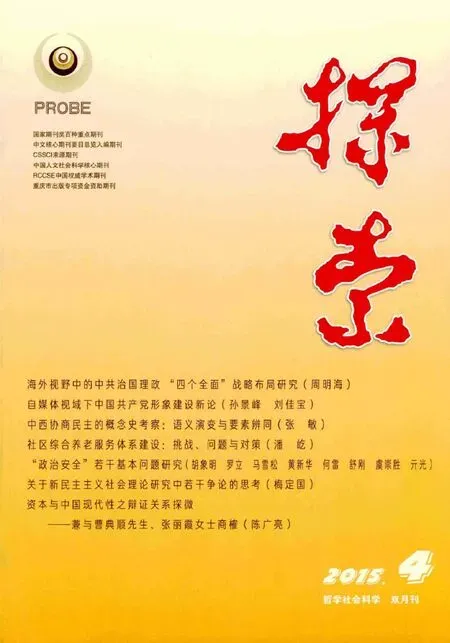馬克思市民社會論域中的人權觀
(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6)
在馬克思人學理論視域中,人自身的發展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制約,經歷如下三個階段:“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1]25這三個階段體現著物的不斷豐富與人的不斷發展的辯證的歷史的統一。“物的依賴關系”階段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按照商品經濟的運行原則,獨立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交換價值之間的交換,必須要遵循自由與平等的原則,承認勞動基礎上的私人利益與私人權利,這構成了市民社會的主要內容。自由與平等的人權原則是商品經濟即市民社會的內生原則。
1
何謂“市民社會”?作為黑格爾法哲學中的特定的概念,“市民社會,這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的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他們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2]197。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作為家庭與政治國家之間的中間環節具有三個基本內容:一是市民社會是由獨立的而又彼此相互依賴的特殊的個體成員所構成的普遍聯合體;二是市民社會是獨立的特殊的個體基于“需要的體系”并通過勞動取得私人利益與私人權利從而形成的物質生活領域;三是市民社會是通過“司法”制度以及“警察和同業公會”組織來保護個體的特殊利益,并維系符合公共利益的社會秩序的“外部的國家”。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沖突著的。在市民社會中,盡管特殊性的個體之間相互依賴,各為另一方而存在,但是,個體特殊性的獨立發展,會使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面臨分解,這直接導致倫理性實體的消失。因此,黑格爾力圖以政治國家來統攝市民社會,使市民社會服從政治國家,使市民社會的個體成員生活在倫理國家中,強調具體自由在于市民社會的特殊利益體系與國家的普遍利益體系的同一性。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黑格爾的深刻之處在于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看作是一種矛盾,但是,他滿足于從表面上解決矛盾,沒有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的根源歸結為私有財產制度。
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時對市民社會所作的界定是直接承繼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把市民社會看作是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社會生活分解成幾個組成部分,但沒有變革這些組成部分本身,沒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會,也就是把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看作自己持續存在的基礎,看作無須進一步論證的前提,從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礎。”[4]188當然,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界定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此基礎上作了發展。綜觀馬克思的著作,主要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過市民社會概念。其一,貫穿于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包括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為標志的市民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3]87-88它“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3]131。其二,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資產階級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私人生活領域。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3]130這時候,“私人所有擺脫了共同體”“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開始與國家相分離,即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分離,“就是說,政治生活……就宣布自己只是一種手段,而這種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會生活”[4]185。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把中世紀的以私人等級為主要標志的封建社會的市民社會稱為“舊市民社會”,舊的市民社會就是政治社會。“中世紀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會的等級和政治意義上的等級是同一的,因為市民社會就是政治生活,因為市民社會的有機原則就是國家的原則”[4]90。但是,歷史的發展使政治等級變成社會等級,“只有法國大革命才完成了從政治等級到社會等級的轉變過程,或者說,使市民社會的等級差別完全成了社會差別,即在政治生活中沒有意義的私人生活的差別。這樣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的分離”[4]100。換句話說,在政治生活中,市民社會的成員“脫離了自己的等級,脫了自己真正的私人地位”[4]101;而在市民社會或私人生活中,“享受和享受能力是市民等級或市民社會的原則”[4]101。因此,真正的市民社會的產生始于它與政治國家的現實分離,它表征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經濟條件下的私人生活領域。
2
既然真正的市民社會表征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私人生活領域,那么,要搞清楚真正的市民社會的本質,就要搞清楚何謂“商品經濟”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市民社會的本質。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商品經濟是以商品交換或流通為基本內容的,作為交換主體的個人的經濟關系存在的前提,商品交換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交換過程的各主體表現為商品所有者”[1]347,或者說,市場主體都必須承認“通過自己的勞動進行占有的規律是前提”,即商品生產“所有權的基本規律”[1]349-350。那么,為什么把通過自己的勞動進行占有的規律看作是交換主體之間經濟關系的前提?這是因為,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只有通過流通,即通過自己的等價物的轉讓,才能成為占有他人勞動——他人的等價物的基礎。二是“交換者交換價值的前提是,不僅先要有一般的分工,而且要有特殊發達形式的分工”[1]351。“特殊發達形式的分工”是相對于工廠內部由于生產環節或工序的不同所形成的“一般的分工”而講的,指的是基于生產交換價值的獨立的經濟主體的私人勞動之間所發生的交換關系所形成的社會分工,具體表現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社會分工使得生產交換價值的生產者在社會交往關系中進行生產,導致社會需要體系愈來愈豐富,私人勞動愈來愈單方面化,從而成為社會總勞動的一環。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5]97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每個經濟主體都是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彼此之間的經濟聯系必然發生利益比較,各方都不吃虧,這就需要把產品當作商品,按等價原則通過交換實現各自利益,通過這種交換連接起來的經濟就是商品經濟。
但是,在馬克思那里,商品經濟并不就是上述的一般規定,商品經濟還具有特殊的規定,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以雇傭勞動制度為特征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很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范疇,還是根本不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做出判斷。”[5]136但是,從古典經濟學家起,資產階級經濟學就形成一個重要傳統,即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成超歷史的永恒的自然現象,“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5]136,自覺不自覺地抹殺商品經濟的歷史特征和制度屬性。對此,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中明確指出:“本書中所用的經濟學名詞,凡是新的都同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中所用的一致。我們所說的‘商品生產’,是指經濟發展中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這個階段從開始為交換而生產的時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即在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出資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工人,并把產品的賣價超出其支出的贏余部分納入腰包的條件下,才獲得充分的發展。”[6]697
既然商品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那么,根植于其中的市民社會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在馬克思那里,市民社會的一般性,指的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人們之間的物質交往形式;就市民社會的特殊性來講,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所賴以存在的以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獨立的經濟主體之間以及資本與勞動之間所發生的以商品交換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關系。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商品經濟才成為獨立的經濟形態,人的存在才表現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商品經濟的發展內在要求私人的物質生產、交換、消費活動擺脫政治國家的干預和強制,成為政治領域之外的自主的經濟活動領域。
3
在確認了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而占有商品的所有權或私有權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之后,馬克思指出:“在流通中就會出現一個建立在這一規律基礎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和平等的王國。”[1]350這意味著,以自由和平等為主要內容的人權作為市民社會的內生原則得以萌發。
關于平等,馬克思認為,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每個商品交換的主體作為社會的個人互相對立,在社會里生產并為社會而生產;他們都必須是以獲得貨幣或商品的交換價值為直接的生產目的;他們生產的商品都必須具備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這種商品總是在他人那里體現為使用價值而在自己這里體現為交換價值,“主體只有通過等價物才在交換中彼此作為價值相等的人,而且他們只是通過彼此借以為對方而存在的那種對象性的交換,才證明自己是價值相等的人。因為他們只有作為等價物的所有者,并作為在交換中這種相互等價的證明者,才是價值相等的人”[7]196。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商品交換的主體之所以能在交換中成為價值相等的人,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于被交換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價值。也就是說,被交換的商品所具有的自然特性能滿足交換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因此,“這種使用價值,即完全處在交換的經濟規定之外的交換內容,絲毫無損于個人的社會平等,相反地卻使他們的自然差別成為他們的社會平等的基礎……只有他們在需要上和生產上的差別,才會導致交換以及他們在交換中的社會平等化;因此,這種自然差別是他們在交換行為中的社會平等的基礎,而且也是他們相互作為生產者出現的那種關系的前提”[7]197。
關于自由,馬克思指出,既然個人之間以及他們的商品之間的這種自然差別是使這些個人結為一體的原因,是使他們作為交換者發生他們被假定為和被證明為平等的人的那種社會關系的動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規定以外,還要加上自由的規定。盡管個人A需要個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這個商品,反過來也一樣,相反的他們互相承認對方是所有者,只是把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這里第一次出現了人格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誰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財產。每個人都是自愿地轉讓財產”[7]198。馬克思從兩個方面進一步闡明了這種自由。一是從商品交換中存在的一般利益或共同利益與個人自私利益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去進一步說明了人的自由性。馬克思指出,進行交換的經濟主體就自我來講是目的;每個人對他人來說都是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但是,交換過程的最終結果是每個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表現為整個交換行為存在著共同利益,但是這種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動因,它只存在于個別利益的背后從而是經濟主體的自由的實現。“主體還盡可以有這樣一種莊嚴的意識:他不顧他人而謀得的個別利益的滿足,正好就是被揚棄的個別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實現。每個主體都作為全過程得最終目的,作為支配一切的主體而從交換行為本身中返回到自身。因而就實現了主體的完全自由。”[1]357-358二是從商品交換中貨幣作為支付手段來說明貨幣制度是平等和自由的實現。馬克思指出,貨幣制度實際上只能是自由和平等的實現。原因在于,在交換中,“誰也不能靠犧牲別人來撈取貨幣。他以貨幣形式得到的東西,只能是他以商品形式付出的東西。一個人享受財富的內容,另一個人則占有財富的一般形式。如果一個人變窮了,另一個人變富了,那么這同他們的自由意志、他們的節省、勤勞、道德等等有關,而決不是由個人在流通中互相對立時發生的經濟關系即交往關系本身造成的。甚至遺產繼承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平等延長下去的類似的法律關系,都絲毫無損于這種社會平等”[1]361。
由此,馬克思把平等與自由的現實存在的基礎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關系,并得出結論說:“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在所有方面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而這種情況也已為歷史所證實。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發展了的交換價值為基礎,相反地是由于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毀滅。上面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產關系,在古代世界還沒有實現,在中世紀也沒有實現。”[7]199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把交換主體之間的交換活動及其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和平等原則稱之為“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1]362。“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商品所有權規律與人權之間的內在關系,即自由和平等等人權是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和“天然”特征。這種自由與平等不是“自然人”的普遍的自然權利,而是市場經濟商品所有權規律的必然要求,是資產階級社會即發達的交換價值的社會的歷史的產物。
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在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體現出來的平等與自由原則僅僅是形式上的,在實質上卻是資本平等地、自由地剝削勞動力,這是資本的特權。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流通區分為“大流通”與“小流通”。馬克思指出:“第一種流通包括資本從離開生產過程到它再回到生產過程這一整個時期。第二種流通是連續不斷地并且總是和生產過程本身同時并行的。這是作為工資支付的、同勞動能力進行交換的那一部分資本。”[1]68很顯然,“大流通”指的是經濟主體之間所發生的商品交換,“小流通”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交換,既包括生產過程前資本購買勞動力所發生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交換,在這里,資本家與勞動者都遵循自由與平等的契約精神,也包括進入到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交換,在這里,自由與平等對于勞動力的所有者來講就蕩然無存了,只是資本的自由與平等,也就是說,“資本不付等價物而獲得了勞動時間——因為這個時間超過了包含在勞動能力中的時間——;資本借助交換的形式,不經交換就占有了他人的勞動時間”[1]69。這意味著,“在交換價值進一步的發展中,……對自己勞動產品的私人所有權也就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而這樣一來,勞動=創造他人的所有權,所有權將支配他人的勞動”[1]192。這里,“勞動等于創造他人的所有權”與“所有權支配他人的勞動”,指的就是在“小流通”中所發生的資本與勞動力之間交換關系的錯位,勞動力作為特殊的商品在與資本進行交換的過程中使資本得以增值,因此,二者之間不是平等的交換關系。這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簡單商品交換所要求商品所有權規律向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剩余價值規律或資本占有規律轉化過程。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揭露道:“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在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的條件都是平等的,把這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5]338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所有權規律向剩余價值規律或資本占有規律轉化過程,就是對資產階級人權的認識由現象到本質的過程。它最終表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權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其實質則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