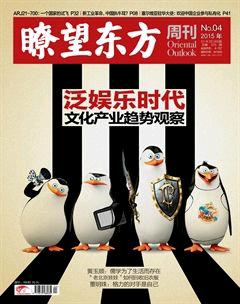騰訊泛娛樂:進化的本能
程瑛+山旭



整整半個世紀前,“先知”或“巫師”麥克盧漢斷言:媒介即訊息,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價值。
此時,迪士尼電影中的米老鼠不僅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雜志,還在洛杉磯的游樂園中載歌載舞。
每每向外界談及“泛娛樂”概念,騰訊公司副總裁程武總難免與如今年近90歲的米老鼠狹路相逢——外人乍看來,這不就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想復制“迪士尼模式”嗎?
但是別忘了,負責“連接一切”的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第一次讓內容生產者和粉絲之間的黏性與互動,達到了不間斷、無邊界的狀態。
這足以改寫一切。
“以前線下也有粉絲俱樂部,但一名作者和他數以百萬計的粉絲,互動是偶發的、間歇的,并沒有日常的溝通機制和情感交流。而現在,作者和粉絲可以利用互聯網,24小時×365天互動,這樣的情感強度以及對內容更新的刺激,與之前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程武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他執掌著騰訊旗下最大的事業群——騰訊互娛。
3個多月前,騰訊互娛宣布推出第四個實體業務平臺“騰訊電影+”;再前推一年,“騰訊文學”創立;2012年3月,“騰訊動漫”亮相。而回溯至2011年,當它看起來還只有騰訊游戲這一個支點的時候,就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泛娛樂”戰略。
2014年,“泛娛樂”已成為中國文化娛樂業的關鍵詞。繼騰訊提出泛娛樂后,BAT全面進軍影視業。
《2014年中國游戲產業報告》將其作為產業趨勢;“阿里數娛、百度文學、小米、華誼等企業巨頭更是紛紛以泛娛樂為開始謀劃內容領域的布局……”
全板塊、全鏈條的“跨界”模式,原本在好萊塢并不新鮮。但中國玩家的互聯網基因,使“彎道超車”成為可能。
任何媒介都是人體的延伸。一家曾經專注網絡游戲的企業,漸次挺進動漫、文學和影視,鋪展開消解邊界、打通上下游的泛娛樂版圖。正如一個人的成長——不是做實驗,不是主題先行,而是從互聯網基因中煥發出的進化本能。
騰訊的泛娛樂布局,核心在于打造明星IP。所謂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產權,在“泛娛樂”語境中,是指一個形象或一個“故事核”——被如潮的粉絲簇擁,影響力強大,能在各種形態的文化產品中穿梭變化。可以是超人、變形金剛,可以是機器貓、孫悟空,也可以是雍正、甄嬛。
強勢IP的陣容,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而在全球范圍內,幾乎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的代表性IP。
互聯網思維、技術變革以及新終端,給了中國人塑造自己的強勢IP的機會。這正是中國最有名的互聯網公司正在推動的娛樂文化產業實踐。
不要“莫名其妙的成功”
程武最早提出“泛娛樂”,是在2011年7月的中國動畫電影發展高峰論壇上。再向前兩年,騰訊互娛——那時還叫騰訊游戲,規模超過盛大,位居中國網游之首。
“我們2003年開始做網絡游戲,2008年、2009年是爆發期。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我們一直在想,騰訊游戲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互聯網游戲平臺?”程武說。
圍繞游戲用戶進行深度調研的結果是:無論年齡、性別,87%的人同時對漫畫感興趣。
“那時互聯網經濟的概念還沒現在這么熱,但我們直覺互聯網和傳統經濟還是有區別的。那時我們就發現,不僅可以從漫畫發展出好的游戲,也應該用網絡平臺去打造有特點的漫畫。”程武說。
后來,用戶調研又顯示,漫畫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網絡文學讀者。
對于互聯網企業進入漫畫和文學領域,騰訊互娛的理論基礎是: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讓作者和粉絲實現了空前的黏性與互動。
黏性——自雅虎在硅谷誕生開始,就是互聯網企業生存的基礎。它所帶來的對用戶體驗的尊重和忠誠,成為互聯網企業的基因,也是騰訊拓展娛樂文化產業的核心動力。
比如,通過用戶調研等種種分析,極力改變過去娛樂文化產品影響力的“不可琢磨”。
對于用戶體驗的重視,也被騰訊互娛市場部高級品牌經理劉智鵬視作騰訊游戲崛起的關鍵。“有人說,在騰訊QQ這個平臺上,插個扁擔就能開花。其實我們內部能看到,在這個平臺上也有很多產品死掉。”
在網絡游戲領域,有一個詞叫“莫名其妙的成功”。
劉智鵬把許多網絡游戲的開發過程形容為“賭未來”,“投入很多資金精力,好像賭博,不知道能否成功。”
到2009年、2010年,騰訊游戲內部逐漸建立起了一套用戶調研方式和工作方法論。這種模式后來也被引入騰訊互娛的其他板塊。
其實,在近年的美劇、韓劇中,通過觀眾調研決定劇情走向的方式已比較普遍。
騰訊則提供了比傳統影視業“更上游”的用戶調研——不僅是某一產品的前期用研,還包括豐裕的歷史積累。總之,基于互聯網傳統的用戶策略以及與之相關的數據研究,是它的“核心能力”。
當然,還有互聯網公司常用的技術手段。比如一個網頁上線前要進行測試,監控分析腦電波、眼球、血壓等等,了解哪些是最能引起測試者興奮的部分。
騰訊互娛影視業務負責人陳英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騰訊未來的電影也會采用這樣的用戶測試,作為影視內容創制的數據參照之一。”
這位中國資深的電影制片人入職騰訊剛剛超過200天。他感嘆:“進來才知道有多大不同!”
大師愛網游
有類似感慨的,還有騰訊泛娛樂的大師顧問團。
在2011年啟動對娛樂文化產業的創造性改造之時,傳統文藝領域的多位大師成為重要推手。那時,騰訊互娛開始努力為網絡游戲“正名”——盡管這個門類被定位于“第九藝術”,也被視作“社會肢體的延伸”,但還是被輿論另眼相看。
程武說,對于當時仍以“網游公司”為標簽的騰訊,這些在音樂、電影、漫畫等領域多有建樹的大師們并無排斥,“他們心態都很開放,很有興趣探究互聯網帶來的創作可能。”
2011年12月,“騰訊游戲中國風·譚盾武俠三部曲”音樂會在上海大劇院舉行。
程武覺得這次與譚盾的合作對于“泛娛樂”思路很有觸動,“網絡游戲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正是大師們的加入,使網絡游戲的文化屬性開始延展。”
2012年3月,騰訊游戲年度發布會上推出了“泛娛樂大師顧問團”:譚盾任首席音樂顧問,蔡志忠任首席動漫顧問,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任首席傳播學術顧問,陸川任首席影視顧問,Micheal Lau任首席玩偶設計顧問,韓國著名玄幻作家全民熙任首席文學策劃顧問。
2013年,圍棋九段古力加盟大師顧問團,騰訊互娛還與中國藝術文化領域最權威的三家機構——中國棋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舞蹈家協會達成戰略合作。
這年9月,騰訊文學創建,一并亮相的是由莫言、劉震云、蘇童、阿來組成的騰訊文學大師顧問團。
在當年底對外發布的主力網游產品《天涯明月刀》中,陳可辛、袁和平、奚仲文、吳里璐成為顧問團成員。
程武認為,大師為互聯網和傳統藝術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思路,也彌補了互聯網企業進入傳統娛樂文化領域的短板。
他最近關注的一個活動是騰訊互娛與中國舞蹈家協會合作的“QQ炫舞大賽”,這是一個由線上同名人氣網游延伸至線下的校園舞蹈賽事。
中國舞蹈家協會駐會副主席馮雙白說,在互聯網平臺上會誕生什么新鮮的、流行的藝術樣式,或者誕生怎樣的藝術新人才,都是不可知的、不可限量的。
1億美元的游戲要講什么故事
時間回到2011年,當騰訊互娛思考“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互聯網游戲平臺”時,它已在內部作了足夠的體制調整。
騰訊互娛市場部在2005年初成立,前身是渠道平臺部,主要做渠道推廣,最初只有幾個人。如今這個部門超過400人。推動其擴張的關鍵因素是:品牌日益得到重視。
后來,市場部設立了品牌經理,專事品牌經營——也就是后來的IP建設。2009年時這個崗位不到30人,現在超過110人。
品牌建設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時騰訊游戲從輕度、休閑游戲向重度游戲轉變。對于重度玩家而言,游戲的品牌和內容建構,已經不再是QQ這個LOGO所能取代的。
于是,騰訊游戲開始醞釀一個高品質的客戶端網游,一名叫今何在的網絡作家成為騰訊員工。這大概也是騰訊互娛第一次比較重要的“泛娛樂”嘗試。
精品游戲的特征之一是研發過程長,一般要三五年;投入大,通常國內一部網游的投入是三四千萬元人民幣。最后這部叫《斗戰神》的3D游戲,研發6年,投入成本遠超業內兩三倍。
最初,它打算以太空科幻戰爭為主題——這是歐美游戲界最流行的題材。
“2007年底做出第一個預研版本,用戶調研時發現國內玩家的接受度非常低。”除了專門的用戶調研部門和外聘公司,劉智鵬他們也會去網吧,“站在玩家背后,看他們怎么玩,聊一會。”
科幻戰爭題材被玩家否定后,騰訊互娛決定做國內市場流行的西游或三國題材,而一般3D游戲都要有“魔法”,西游記顯然更適合。
“當時市場上的西游題材網游很多,幾乎都是Q版的,一說西游游戲就是低幼的感覺。我們也曾經為要不要Q版而糾結。”劉智鵬回憶說,不同風格的西游人物手繪被交由玩家選擇。
最終“出線”的形象代表著玩家心目中的西游氛圍:寫實且較為壓抑。
“西游記是說一個師傅加三個徒弟開開心心打怪嗎?不是的。書里說他們到村里,所有的小孩都嚇哭了。我們設計的這組形象,開始也拿不準,用研顯示玩家非常喜歡。”劉智鵬說。
通常,一部重度游戲要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體系。玩家的體驗,除了玩法本身,還要能被這個“新世界”所吸引,不斷投入時間和精力。
然而,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文學作品,《西游記》的衍生作品并不多,更不要說建立深層次世界觀這樣的復雜問題。
有人提到了今何在的《悟空傳》——一本2001年前后一度風靡的網絡文學作品,從陰謀論的視角構筑了顛覆性的西游記世界。
薄薄10萬字的《悟空傳》給《斗戰神》的世界奠定了基調、氛圍和邏輯——“我要這天再也遮不住我的眼”,整個團隊140多人,都在咀嚼著小說開頭的這句話。
“這次是先找故事,而不是先找玩法。”劉智鵬說,一般的游戲設計更重視玩法,劇情可能就分出半個人力簡單寫寫。而《斗戰神》有8個人的劇情組,文學策劃寫好一章,再交給原畫師去制作。
最終,由今何在和劉智鵬們一起描述的《斗戰神》世界,有超過300萬字的腳本。這也是中國網絡游戲行業最復雜的故事創作。
劉智鵬說,游戲制作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大量的數據調研支持,而最為核心的還是故事建構。
2013年9月,《斗戰神》上線,兩個月內達到60萬人同時在線的速度,創造了行業紀錄。
從《悟空傳》到《斗戰神》,就是一個強勢IP精心雕琢的過程。劉智鵬說,在游戲領域,也有開發者會借用知名武俠小說等IP,但有時只是“買殼”,甚至只把游戲角色改成小說中人物的名字,像《斗戰神》這樣充分演繹、深入解讀開發的并不多。
事實上,游戲的開發過程,甚至刺激著今何在寫出了《悟空傳》的續篇。
如何塑造世界級的Monkey King
現在,《斗戰神》又可能從網游走上大銀幕。程武和陳英杰,帶著對《斗戰神》的寄望去了好萊塢。
騰訊互娛做了針對美國市場的用研,結果顯示Monkey King——美猴王正是最受海外歡迎的中國IP形象。
陳英杰列舉了好幾家有意和騰訊合作拍攝《斗戰神》大電影的國內傳統電影企業。而按照他的想法,這部電影應該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產品。
兩個月前,由程武率隊,騰訊互娛的高管們在好萊塢拜訪一圈,“各大電影公司幾乎都鎖定了這部片子”。而它最終可能由卡梅隆這樣級別的導演操刀,花費兩三年時間完成。
“西游記的IP就在那里,誰都可以改編,為什么好萊塢看重和騰訊的合作?”陳英杰告訴本刊記者,“他們知道騰訊更加了解用戶的喜好,了解中國市場的需求。”
在好萊塢,和電影公司的第一輪見面是禮節性的。陳英杰說,美國人知道騰訊是“很厲害的公司”,但并不了解其業務內容,感覺像不少前來尋求合作的中國企業那樣,“人傻錢多”。
美國沒有網文這個領域,“我們1000字3分錢的收費閱讀模式,注重用戶體驗的游戲免費模式,對他們震動很大。他們說,沒想到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對用戶體驗已經關注到如此細致的程度。”陳英杰說。
第一輪會談后,美國人很快就來預約第二輪會談,“創作總監、高級制片人都很直接,對項目作案例分析,想做什么,想怎么合作。”陳英杰回憶說。
幾年前,陳英杰曾參與過迪士尼與國內幾家影視機構合作的《歌舞青春》中國版電影。1500萬元的制作費用,只收回50萬元票房。“好萊塢之前認為,我的IP沒問題,操作模式也很成熟,比你們有經驗。后來他們發現,對中國市場最大的擔憂是——不了解受眾的喜好。”
程武對于和好萊塢的合作目標清晰:基于中國自己的IP,騰訊有資金,有對受眾的了解,好萊塢出經驗和技術,講一個全球性的故事,在全球獲得收益——而不只是簡單參與或植入。
在騰訊這樣的企業進入影視業前,這個市場的情況是:電影投資在上映之前很難預估成敗,只能是50%對50%。
“這是天時地利人和、多重不確定因素的結果,即使名導演也可能翻船。”陳英杰說,“原來的創作往往是橫空出世,無規律可循,但騰訊的IP背后有充分的用研,有對觀眾清晰的分析和掌握。”
這樣,通過種種“互聯網思維”的努力,“也許能讓50%的成功率稍稍增長一些,一部電影達到60%到70%就足夠了,至少不會賠得那么慘。”這位資深制片人說,“我們在做這樣的嘗試,也期望騰訊的進入能對這個行業有推動或者說幫助。”
不能讓孩子失望
陳英杰第一次感受到互聯網公司做娛樂“不一樣”,是在2012年。那時他作為發行人與騰訊互娛合作《洛克王國2》大電影。
《洛克王國》是騰訊互娛最早打造的“泛娛樂”產品——從一個兒童線上社區,發展為擁有圖書、電影、電視劇和舞臺劇的完整體系。
“當我們告訴騰訊的人怎樣做才能性價比更高、獲得更好的票房收益時,他們卻一直在問一個問題:能不能把用戶的體驗做得更好。”陳英杰說,“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用戶體驗這個概念,覺得虛幻飄渺。”
不過,很快他就被“震驚”了。
出品方為《洛克王國2》準備的200萬份促銷紀念品,隨著電影熱映,兩天內贈送一空。
陳英杰覺得,“這對電影促銷來說很正常,海報上都說了,先到先得,贈完就完了。”但就是這個“小事”,卻讓騰訊和發行方產生了“激烈的沖撞”。
騰訊堅持用戶體驗第一,希望用三天時間做新的促銷物料準備,使每個到電影院的孩子都能得到一個紀念品。
“我說,最快也要七八天,三天不可能。你騰訊公司不能說什么是什么,沒有這樣的案例。”陳英杰回憶說,當時合作的發行公司有些“惱”了。
騰訊互娛團隊在三天內想出了解決辦法:只要觀眾說出曾在哪家影院觀影,就可以用QQ號申請一個贈品,7天內補發。
《洛克王國2》的票房是7000萬元,騰訊送出了超過1000萬個主題道具。
“傳統電影的投資人看的是票房,關心怎樣把人往電影院里趕,追求的是最終的盈利。騰訊關心的是,怎樣不讓孩子失望。”此后陳英杰告訴他所有的合作伙伴,“如果你要做一個兒童影視產品,千萬記住,這個用戶長大以后會成為你潛在的客戶。”
《洛克王國》被程武稱為“前期小規模的單項目嘗試”,這個嘗試印證了“泛娛樂”是一條合理的路徑。
這款“媽媽設計給孩子玩”的線上社區,舍棄了網絡游戲常用的道具等收費模式,每月10元封頂。
“我們發現小孩子在線上社區之余還有很多線下需求。他們要看動畫片、看電影、看書,要用工具,需要玩具。”程武說,“一開始我們就想找授權伙伴,拍電影,出圖書攻略,創造更多不同形式的娛樂作品。”
不過他也強調,這整個體系的每一個支點都應該是精品。
2010年《洛克王國》上線,第二年就有劇團找到騰訊希望獲得授權,被戲劇愛好者程武拒絕。他覺得,如果不能做出“百老匯級的精品”,寧可不做。
又過了一年多,騰訊互娛才通過與北京兒童藝術劇院的合作,推出了舞臺劇,到2014年才“接近打平”。
而《洛克王國》系列電影,三部總票房1.5億元。它又反過來促進了線上社區的發展:最高同時在線人數都是在電影上映時出現的,比如2014年是100萬。
不急于賺錢
在“泛娛樂”布局中,文學、動漫一般被視為上游,是原生的;而游戲、電影是下游,是衍生的。
“要創造強勢IP,必須向上游延伸,比如通過動漫產生好IP,再用于游戲、電影。”騰訊動漫版權運營總監羅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動漫盈利預期不高的情況下,游戲、電影的“反哺”作用不可或缺。
多年來盜版遍地,使得漫畫的網上收費閱讀難以實現,也難有專職作者悉心耕耘。
但在騰訊的“泛娛樂”版圖中,漫畫對于IP的原發效應、對用戶的培養聚集、對用戶體驗的豐富,又是不可替代的。
2012年3月,騰訊動漫正式成立,成為騰訊互娛泛娛樂戰略的重要一環。程武回憶,那時候,“很多媒體朋友問我,你們對變現是怎樣想的?我們說現在不考慮變現問題。”
與文學不同,動漫的根本約束在于產量過低——以通常每周8到18頁的產量,動漫創作本身不足以支撐一個工作室的正常運行,更不要說產量更低的個人作者。
因此,在一個平臺上進行整體商業開發,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基于互聯網搭建一個用戶平臺,用戶反饋的速度和范圍,傳統紙制出版與之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羅浩說。
這個平臺并非簡單將作者和商業資源對接,而是更像“保育院”或“孵化器”。在騰訊動漫的北京辦公室,近30名專職編輯負責對超過300名簽約作者指導溝通——將以自我消遣為主要動力的業余畫手,培養成消費產品的提供者。
問題來了,比如連續性——絕大多數漫畫的生命周期不超過10個月,編輯要幫助作者將一個IP規劃好,并且“撫養成人”。
目前騰訊動漫最受歡迎的國產漫畫作品《尸兄》,累計點擊超過40億,以此IP改編的動畫片點擊量是7億。用程武的話說,一個“高情感寄托、高用戶認知”的IP已經誕生。
《尸兄》的作者“七度魚”是浙江小城麗水的一位原畫師。騰訊動漫先是看中了他的風格,然后通過數據調研,建議他以時髦的僵尸為主題創作作品。“一開始他不相信漫畫能成為職業。”羅浩說。
除了編輯指導這個類似日本漫畫“創作委員會”的形式,平臺還給漫畫提供其他騰訊所擁有的資源。
在2014年8月1日,騰訊動漫宣布《尸兄》被授權改編為手游,這是炙手可熱的手游業內IP授權的最高價。“七度魚”也成為年收入破百萬元的職業簽約漫畫家。
為了激發整個行業的興趣,騰訊動漫將更多權益“讓給產業鏈上的合作方”。同時,“至少未來5年,我們會把大量收益全部拿給作者。”羅浩說,他們的目標是——把平臺做大之后,能夠產生像迪士尼和漫威那樣的強勢IP,價值就絕不是現在這么一點點。
目前這些國產動漫作品和從日本高價引進的漫畫,都在網絡平臺上無償開放閱讀。騰訊動漫更看重的是如何從IP授權和打通粉絲經濟入手,去開拓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后來當騰訊互娛運行第三個獨立平臺“騰訊文學”之時,也為暢銷圖書產品投入了超過4億元人民幣,用于購買傳統文學版權。
“當我們站在外面看互聯網的時候,覺得很新鮮,很有希望。而直到我進入騰訊內部后才發現,此前看到的只是寶藏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像海面下的冰山,那才是所有人最向往、也是最可怕的。”陳英杰說,加盟騰訊200多天來他感到“沖擊很大”。
比如,他發現“網文大神”并非偶然爆得大名,他們的付出比一般傳統作家更多。
他們要不斷與受眾交流,“因為他很清楚,如果不為讀者去寫故事,立刻就沒有人為他埋單,而新人還在紛紛出現。競爭很殘酷,也更加激烈。”陳英杰說,“他們要自己迅速調整,要吸引00后,這都是傳統作家所不具備的能力。”
比如,騰訊擁有一批掌握“方法論”的人——多個自營工作室中,那些跑得最快的人,他們明白怎樣做出一款成功的產品,他們既重視數據參考,更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融通能力。
又比如,“不急于賺錢”的態度——一款精品游戲,并不設定嚴格的時間表,公測日期可能推遲一年又一年;而傳奇影業用8年打造電影《魔獸世界》的案例,也常常被騰訊互娛的高管們帶著仰慕的口吻提及。
“來到騰訊,最深刻的感受是,背后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在推動著你去創新,讓你不會回到老路上去,而是必須向前探索。”陳英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