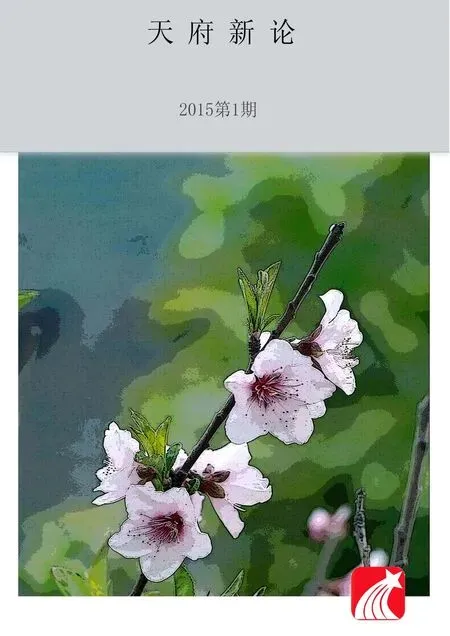文學與文化人類學的跨界之旅——評李左人的長篇小說 《女兒谷:1937》
張建鋒
(作者:張建鋒,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李左人的長篇小說《女兒谷:1937》,以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觀照扎壩鮮水河走婚大峽谷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田野調查的實證與文學想象的虛構雜糅,文學性與學術性融合,具有特殊的藝術價值和學術意義。
一、田野調查與文學想象
李左人長期在走婚的鮮水河峽谷扎巴人和瀘沽湖、利家嘴摩梭人的現實生活中提取素材,結合歷史資料、民俗史料,以文化人類學為學理支撐創作了《女兒谷:1937》。小說還原了1937年扎壩的生活場景和社會現實,成為目前扎壩唯一的歷史生活畫卷和“活”的“文化原生態”記錄,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小說”。
作者將田野調查與文學想象融合起來,記實與虛構二位一體。虛構的人物、故事、情節與歷史事件、生活場景、社會現實相融相生。小說依傍史實,演繹故事,借助人類學立場對歷史縱向的嚴謹考察和文學神游冥想的翅膀飛翔,尋求故事虛構性與社會人文環境記實性的統一,從而回到“1937”(時間)“女兒谷”(空間)的“歷史現場”,“回到”當時當地,以虛擬的人物、故事、情節為線,串聯起清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實施改土歸流、民國年間廢黜土司頭人、紅軍長征過道孚、諾那事變、特派人員在扎壩救災推行保甲制等歷史事實,和扎壩大峽谷的風土人情、扎巴人的走婚、偷婚、母系大家庭、頭人之間的恩怨情仇等世俗生活,重大的歷史事件與豐富的世俗生活構成歷史景象的再現,具有歷史的“現場感”。作者多次深入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及川滇交界處的瀘沽湖實地考察,獲得了真實的體驗和感悟。田野調查讓“虛構”的世俗生活“落地”,讓描寫具有記實性,成為“活”的生活形態。
作者的田野調查,本是出于學術志向,想厘清扎巴族群的文化樣態、文化傳承與轉型的歷程,捕捉走婚原生形態,考察扎壩傳統文化的變遷興衰。從作者發表的《扎巴人的婚姻、家庭和性》、《鮮水河走婚大峽谷調查與思考》、《走婚與四川藏區的“爬墻文化”》、《“走婚大峽谷”:飛檐走壁的浪漫愛情》等多篇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到作者用力之勤,用功之深。而小說創作盤活了作者對扎巴文化的人類學思考,作者把學術上的見解融和進去,探究扎巴人性本質,解讀人類深層的隱秘、人類的文化基因。作者自覺將田野調查與文學想象雜糅在一起,有意識地在文學與文化人類學之間游走,站在文化多樣性立場,將扎巴文化作為非主流的“文化他者”來反映,是對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文化視角的一種顛覆。這是“還原性”書寫,是借他鑒我,而不是像歷史小說那樣記錄歷史、展現歷史,或以歷史題材借古喻今、借古諷今,從而使小說具有了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價值。
二、走婚文化的深度“勘探”
李左人對走婚文化的“勘探”體現出“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視野,小說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和獨特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一些學者懷著對種族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厭惡和對落后國家文化的理解與尊重,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強調尊重文化之間的差別并要求相互尊重,尊重多種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價值,強調尋求理解與和諧共處,不去輕易評判和摧毀那些與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
康藏地區的“走婚文化”,被“外來者”以獵奇的眼光記錄并評頭品足,而李左人從文化傳統、文化環境方面來展現走婚現象,又從理論上揭示走婚文化的實質。小說的主要人物鐘秋果不單是劉文輝的秘書、西康建省委員會特派員,還有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的人類學專業背景,隨身攜帶著他的老師近代藏學研究先驅任筱莊(任乃強)的《西康圖經》。鐘秋果“看” “走婚” (視角),“想”“走婚”(思考),還“行”“走婚”(實踐)。作者沒有停留在“走婚文化”的現象描述上,而是根據自己的田野調查和閱讀的歷史文獻,盡力展現扎壩走婚產生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等背景及其演變形態,揭示出“走婚文化”的精神實質。作者始終突出表現母系社會環境和走婚習俗的文化氛圍對于扎壩人的影響。鐘秋果主動走近母系大家庭,不僅弄清了扎巴人堅持走婚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的嚴重制約和母系文化的強大慣性,而且了解到他們對待婚姻和家庭的觀念與內地完全不同,并對扎壩的多樣婚姻形態持肯定態度。小說從經濟、社會、文化的各方面來揭示“走婚文化”,厘清其文化的源流、體系,說明其歷史的傳承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體現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視野,有助于矯正當下偏狹的或者霸權的各種“文化主義”。
三、凸現康藏女性的文化品格
《女兒谷:1937》描寫走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時時進行藏漢兩地文化的對比。“尼瑪所代表的扎巴性意識,崇尚自由、自主、平等,是一種伙伴關系性倫理。小翠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在她身上體現的依從、被動、依附,是夫權社會男尊女卑觀念衍生出來的性道德。”文化的并置和對照具有明確的借彼為鏡、反觀自身的自覺批判傾向。作者自覺地突出描寫康藏女性的地域文化品格,體現出反思中國正統文化的傾向。
作者立足于扎壩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走婚文化,塑造出了特色鮮明的康藏女性形象,豐富了巴蜀文學的人物形象畫廊。小說中塑造的主要女性形象有嘎瑪卓嘎、巴桑、桑姆、澤仁旺姆、尼瑪、玉珠、志瑪、央金卓瑪、扎西娜姆、巴瑪、阿追等。其中,澤仁旺姆、尼瑪母女的形象具有代表性。母女二人不僅身份特殊、背景復雜、經歷豐富,而且與鐘秋果形成了“三角”情感糾葛。其性格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讓她們的形象更生動、更豐滿,更具有地域文化的特異色彩。澤仁旺姆身上貫注著康藏文化的元素。她說:“憑什么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自己的事自己不能做主?”“為啥子只能守著一個男人,憑什么要女人為丈夫守節?女人為啥不可以多找幾個自己喜歡的男人?”在漢文化圈里人們習以為常的婚姻觀念在女兒谷的“語境”里遭遇“吐槽”。自以為正統的漢文化遭到扎壩人的質疑問難,一時間集體“失語”。澤仁旺姆不只是把“口號”喊得響,而且自覺“實施”自己雄偉的“征服男人”、“征服女兒谷”的計劃。這些品性蓄積著康藏地區的文化基因,又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磨煉出新的特色。
作為澤仁旺姆的女兒,尼瑪在縣城受過一點新式教育,追求自己的愛情更主動,接收新觀念更快。從外表上看去,尼瑪一身小蠻女打扮,活脫脫一個放肆的野丫頭。她對愛情的追求具有高度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堅決果敢,勇往直前,行動任性隨性,語言斬釘截鐵,其大膽是驚人的。尼瑪在女兒谷走婚文化的浸潤下早通人事,曾經滄海更知水為何物,不僅具有少女天生的麗質,還綻放著成熟女性迷人的風韻。在走婚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康藏女性,順著天性,自由自在。作為“世外”之域, “化外”之地的女兒谷,很少受到所謂“文明”的污染,扎巴人沒有被現代社會“異化”失去自然的人格,離人的本我更近,更像真正的人。“藍天作帳,草坡為床,把愛寫在荒野里。原始與現代,野性與文明,火與水,剛與柔,動與靜,生與死,混成天衍大氣,萬代不滅,直至永恒。”正是鮮水河扎壩女兒谷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基因鑄就了康藏女性的文化品格。
四、跨界的限度與未完成的探索
《女兒谷:1937》是一次“跨界”的藝術探索,尋求文學性與學術性的融合。作者游走在文學與文化人類學之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但跨界之旅還有可拓展和深化的空間。小說對扎壩走婚大峽谷的地理環境、自然風貌、山川河流、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等方面的描寫,對扎壩人的體形體質、穿衣打扮、房舍建筑、飲食習性、娛樂方式、交通出行等方面的描寫,都有相當精彩的筆墨,對于展現扎壩母系制婚姻家庭的特點、人物的性格都有渲染、烘托作用,能為扎巴文化鋪墊上厚重的地域底色。但有些描寫還可以進一步加強細節、突出特色、展示亮點,以“活”的“原生態”形式來反映走婚文化的獨特性。小說觸及到走婚文化面臨的生存困境,但對于歷史風云、時代潮流對扎巴人及其走婚文化的影響的揭示還有開拓的空間。比如央金卓瑪的雜貨店,是扎壩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小說對此的描寫稍嫌簡單,沒有完全發揮出“窗口”傳播文化的功能。如果能像描寫鐘秋果的照相機、金筆,澤仁旺姆的雪花膏,還有電燈、電報、電影、廣告等那樣處理,藝術效果會更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