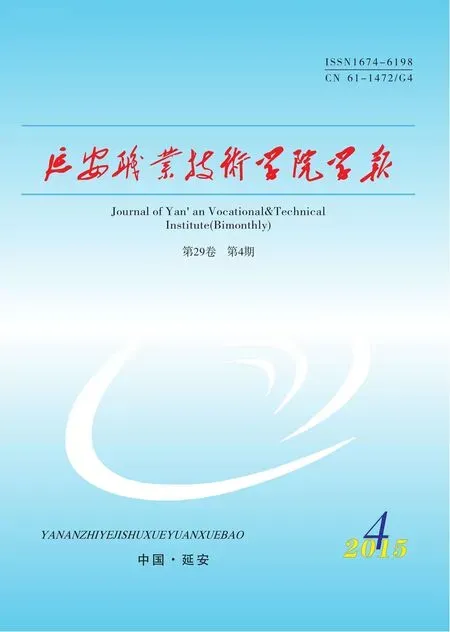《接骨師之女》的女性主義敘事學解讀
陸丹路
(鎮江高等專科學校,江蘇 鎮江 212000)
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以在作品中生動描寫華裔母女關系而著稱。她出版于2001年的第四部長篇小說《接骨師之女》沿襲了這一主題,展現了外婆、母親、女兒三代人之間由沖突到理解的情感歷程,深入表現了華裔女性的內心世界。從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角度看,《接骨師之女》成功實現了女性敘事話語的權威,對讀者具有了權威性。
女性主義敘事學是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有效結合,蘇珊·S·蘭瑟在《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這本書中把女性作家的聲音分為三種類型: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和集體型敘述聲音。她認為“這三種敘述方式都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各種匯合以及不斷變化的敘事技巧常規的表現形式,女性作家要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形成這三種權威。”[1]
譚恩美被美國的《新聞周刊》稱作是“當代講故事的高手”,[2]《接骨師之女》中,她主要使用了作者型敘述聲音和個人型敘述聲音,同時融入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話本敘述模式來實現女性敘事話語的權威性。
一、作者型敘述聲音
“作者型敘述”是指一種“異故事的”、集體的并具有潛在自我指稱意義的敘事狀態。[1]敘述者不是虛構世界的參與者,他與虛構人物分屬兩個不同的本體存在層面。作者型的敘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為虛構,但其敘述聲音又顯得更具有可信度。[3]在《接骨師之女》中,譚恩美通過作者型敘述聲音,樹立了一個無所不知的現實而客觀的講述者形象,為她自己和整個華裔女性作家群體實現了“話語權威”。
在《接骨師之女》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作者型敘事者以真實而客觀的方式進行講述,對人物行為、心情的所有細節了若指掌。
露絲的故事就是使用了作者型敘述聲音,讓讀者清楚地了解華裔女性在美國的真實生活狀況。譚恩美用第三人稱敘事呈現了露絲生活中出現的各種麻煩:每年8月12日的心理性失語;替人“捉刀”、沒有自己聲音的影子作家;和母親之間令人困擾的關系。在感情生活中,她覺得無法與她同居10年的情人亞特坦誠相對、產生共鳴:“(露絲)有點難過地注意到,亞特是說“你”而不是說“我們”打算怎么辦。自從中秋節的聚餐以來,她越來越覺得她和亞特不像一家人”[3]“他們兩人之間溝通如此之差,露絲覺得很是失敗”。[3]這兩句陳述不僅表達了露絲的感受,同時也達到了加強敘述者客觀性的目的。
在敘述寶姨的愛情故事時,茹靈成為了作者型敘述者。她描述了母親和父親之間第一次相遇的場景:“寶姨在里屋,透過簾子看得到他。小叔當時二十二歲,身材瘦削。五官生得很標致,儀態自如,不卑不亢。”[3]她聽到了她母親內心的聲音:“況且,何必讓未婚夫疑心,以為她做了什么對不起張老板的事呢?反正好多人都說她性子倔,凡事自作主張。”[3]
對茹靈而言,她似乎和母親生活在了同一時期,目睹了不同事件,記錄下了所有的事情。茹靈所扮演的作者型敘述者的角色加強了敘述其母親故事的生動效果,和茹靈一樣,讀者似乎也處于寶姨出現的相同的場景。作者型敘述者置身敘述時間之外,因此,所有事盡在掌控之中。通過茹靈對寶姨經歷的敘述,譚恩美想強調的是寶姨在劉氏父權家族中真實、沉默的處境。
二、個人型敘述聲音
“個人型敘述聲音”是指敘述者講述自身的故事,講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該主角以往的自我。[1]個人型敘述聲音里的虛構在形式上與自傳難以區分,從而使得其敘述聲音的權威往往名正言順。[4]
在譚恩美的小說中,女性的個人敘事聲音能夠傳達過去的隱秘,暗示不同女性角色經歷過的受壓制或扭曲的情形,是展示不同女性體驗的主要方法。敘述者“我”的再現表明了華裔女性的需求得以表達和傾聽。同時,女性個人聲音的使用也拉近了讀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
《接骨師之女》通過個人型敘述聲音講述女性的經歷,表達其獨特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展現出女性的性別優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男性話語權威的否定。茹靈的個人聲音公開、顯著、引人注目。“我知道這一切,但有一個姓氏我卻記不起來了。它藏在我記憶里最深的一層,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曾成百上千次地記起,那個早上,寶姨把那個字寫給我看。那時我才六歲,聰穎過人。我能寫會讀,知書識數,也懂得記事了。”[3]自傳開始時的肯定語氣用于聲明茹靈在敘述過程中的權威角色。“我知道”,“我能”,“我懂得”,“我記得”表明它是茹靈自己的故事,沒有人有權取代她成為最可靠的敘述者。
在肯定茹靈在其自傳中主要聲音的過程中,譚恩美還希望揭示茹靈在敘述中的復雜感覺,以確立更為立體的茹靈形象。在以下這一段落中,譚不斷地變換代詞。“寶姨,我們到底姓什么?我一直想找回那個姓氏。快來幫幫我吧。我已不再是個小孩,不再害怕鬼魂了。你還生我的氣嗎?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茹靈,你的女兒。”[3]這里,代詞“我們”、“我”、“你”、“你的”的改變成功闡明了茹靈的復雜情感。通俗用語和直接引語的使用建立了一個茹靈在同寶姨真正對話的場景。
三、話本敘事模式
(一)說故事
話本敘事源于“說書”這樣一種古老的“極具敘述話語權威”的中國民間藝術形式,而由話本發展而來的話本小說敘事自然也沿襲了“話語權威”的優勢。《接骨師之女》中,譚恩美吸取了這一中國特色的敘事模式,通過“說故事”的敘事形式,使小說中的女性們能夠暢所欲言,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不僅增添了作品的獨特性和新鮮感,也自然建立了女性敘事話語權威。這樣的敘述對華裔女性有著特別的意義:它變成女性自我肯定的一種重要形式。
小說中,母親就試圖通過“說故事”這種傳統的敘事形式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寶姨對其臉上駭人傷疤的眾多解釋為例。從表演食火藝人演出的失誤,到幻想的掃把星掉到嘴里,寶姨又編了一個“吃了燒菜用的火炭”的故事。在這里,譚利用了情節懸念,讓讀者好奇寶姨是怎么傷到臉的。直到在茹靈自傳中,譚恩美安排茹靈作為作者型敘述者講述了寶姨的故事,才揭開了形成傷疤的真實原因。
(二)話本敘事結構
《接骨師之女》包括了話本敘事結構中除了“入話”之外的四個部分:篇首、頭回、正話和篇尾。這種有意識的模仿和套用就是為了借用話本敘事的優勢,實現女性敘事話語的權威性。
小說開端作者介紹了小說的寫作目的:“母親在世的最后一天,我終于知道了她還有我外婆的真實姓名。僅以此書獻給她們兩位。”[3]類似于篇首,這一部分揭示了故事的中心和外婆、母親、女兒三代之間的關系。
接下來譚恩美以“真”為標題作為小說的序幕,擔任著話本敘事結構中“頭回”的角色。以“這些事我知道都是真的”開始,茹靈用個人型敘述聲音講述了童年經歷,一個真實、典型的中國故事——奇異、神秘、吸引人。就像話本敘事結構中的“頭回”,這一部分的敘事目的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引導他們進入主要章節。
如同話本結構中的“正話”,小說的正文部分包含三大部分,系統性地講述了三代人的故事。第一部以作者型敘述聲音講述了露絲和母親茹靈在美國的生活。第二部分則分別以“心”、“變”、“鬼”、“命運”“道”、“骨”、“香”為題通過茹靈的個人敘述型聲音講述舊時在中國的生活。在茹靈的故事中,寶姨的故事同時被呈現,蜿蜒曲折而動人心魄。第三部分又回到了露絲和母親的現代生活,以作者型敘述聲音全知而客觀地“說故事”。
類似于話本模式中的“篇尾”,“尾聲”重新回到了小說的主題——母女三代人的關系。從自傳中露絲最終意識到外婆和母親的力量,激勵她實現個人成長,開始執筆為自己、為親人創作,確立了另一種女性話語權威。“露絲下筆寫作的時候,想起了這些。故事寫給她的外婆。還有那個將成為自己母親的小女孩。”[3]p334
通過話本敘事結構,“說故事”的人扮演了權威說教者的角色,小說的主題——母女關系開頭被提及,在尾聲又得到重申。由于有說教的效果,話本敘事結構成為了權威的象征,能夠取得權威敘事聲音。這也正是譚恩美在小說中采用這一敘事結構的重要原因。
結語
《接骨師之女》中,不同敘述模式的運用使小說獨樹一幟、與眾不同。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與話本敘事模式的融合使小說的敘事聲音充滿了信服力,能夠吸引和打動讀者,目的就在于使女性、尤其是美國華裔女性獲得敘述話語的權威。
[1](美)蘇珊.S.蘭瑟,黃必康,譯.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美)譚恩美.灶神之妻[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3](美)譚恩美著,張坤,譯.接骨師之女[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4]陳妍.實現敘述聲音的權威—從女性主義敘事學角度解讀譚恩美的作品[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09(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