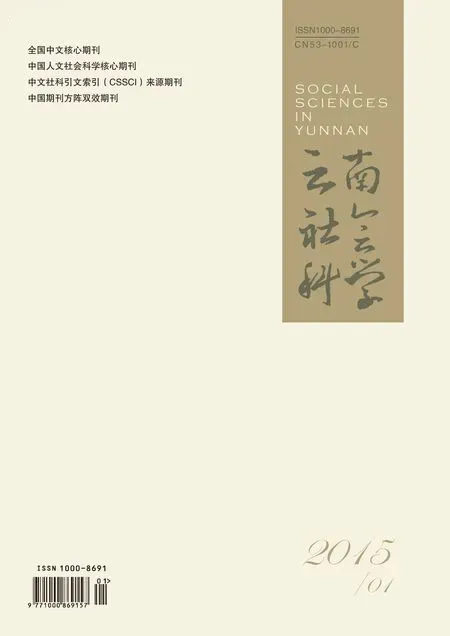地方合作轉型、治理重構與邊疆民族地區長治久安
柳建文
20世紀90年代,中國地方之間自發的、互利的經濟合作開始興起。目前,涉及邊疆民族地區的合作組織已達40多個,如川甘青藏滇毗鄰地區民族友好經濟協作會、西北五省區經濟技術協作聯席會、絲路重鎮經聯會等。一些與邊疆民族地區相關的經濟合作區域也開始浮現,如“陜甘青藏經濟圈”、“絲綢之路經濟帶”等。由于地方合作組織和經濟合作區域均由若干核心地帶向外擴散(如上海、杭州對于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廣州、深圳對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組織;北京、天津對于環渤海區域合作市長聯席會等),因此學術界關注的大多是北京、上海、廣東等核心地區。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滯后,往往處于合作區域的邊緣地帶,這一變化鮮有人關注。歷史上看,經濟聯系的密切能夠促進民族交流與融合并增進國家認同。在當代,通過提升地方合作的層次,可以加深邊疆與內地的社會經濟聯系,提高國家一體化程度。本文試圖建立起“地方合作轉型、區域一體化與邊疆長治久安”的分析框架,同時為中國區域治理的調整和創新提供必要的依據。
一、文獻回顧
邊疆民族問題始終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歷史上看,相對黃河、長江中下游等“中心”地帶,新(疆)、藏、滇等地區“地勢險阻,道路不修,民智閉塞,農產鮮少,兼與中央相距過遠,政令不能下逮,民意亦未上達”,從晚清一直到民國時代,旨在實現上述“邊緣地帶”的國家認同和全國社會經濟的融合始終是中央政府的一項艱巨任務[1]。由于邊疆地區的特殊性,早在民國時期就形成了研究邊疆問題的“邊政學”。20世紀40年代,楊成志較早提出建立邊疆與內地的經濟紐帶,認為邊疆政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采用何種切實方案使生產率逐日增加及產物運輸暢達無阻”[2]。其后,費孝通提出“地方聯合”思想。比如,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四省(區)可以構成一個協作區,成為西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心。甘南和黃南兩個位于甘、青兩省的藏族自治州如果聯合發展起來,就有可能把藏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相對東移,這有利于漢藏交流[3]。新中國成立后,邊疆地區在政治制度上與內地的一體化已經完成并且得到鞏固,但經濟發展差距與文化差異仍然存在,為此,國家長期實行對口援助政策。在對發展援助有效還是無效的爭論中,經濟學家們歸納了這一模式的若干弊端:首先,援助帶來依賴,當地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受到影響,削弱輸出商品的競爭力,制約負責任的公共機構的發展;其次,大量援助可能延緩制度變革,甚至導致制度的僵化;最后,援助的收益是趨于遞減的,并可能損害當地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為“獲得財政援助的區域也可能習慣于接受援助,可能不急于建立自己的積累和投資習慣,以便有朝一日使自己的資本供給達到自力更生”[4](P140)。鄭長德的研究顯示,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民族地區政府自我發展能力指數、區域創新與學習能力指數和區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指數均位居后列[5]。靳薇的調研發現,“以援助促進發展”的思路導致了“制度依賴”,依賴者一方面要依賴,另一方面厭惡依賴的事實;被依賴者不堪重負,屢屢提及要依賴者自立。這對民族地區與國家關系的良性互動十分不利[6](P117)。方盛舉認為,目前的邊疆治理與國家發展階段的轉變不相適應,“即使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發展主題的今天,政府系統乃至全民對邊疆治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歷史條件和思維慣性下,而沒有開辟和發展出新的邊疆治理觀,更沒有形成全新的成熟的邊疆治理模式”[7]。周平提出,新的邊疆治理策略需要在民族間、民族與國家間建立合理的利益關系,“要在邊疆治理中淡化民族主義取向的治理方式,強化區域主義的治理方式”。所謂區域主義的治理方式,一是必須調整民族政策的價值導向,將原有的民族主義的價值導向轉變為國家主義的價值導向;二是在現實對邊疆地區的幫扶政策中改變單純的以民族作為扶助對象,確立起民族身份與區域發展協同并重的治理模式[8]。周星認為:“多民族國家經濟的一體化程度與國家內部民族構成中異質程度的差異成反比。作為民族國家經濟,它是以控制、整合或同化其中的民族地區經濟成分,不斷提高國家經濟層次上的一體化程度為指向的,只有這樣才能鞏固超民族的國家經濟生活與政治體系的穩定性。”[9](P122~123)如何促進邊疆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發展,是邊疆治理面臨的重大課題。2014年,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實現新疆長治久安需要推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互惠型的地方合作是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動力,同時,這種合作方式可以確立合理的民族利益觀,形成新的邊疆治理模式。
二、邊疆民族地區的地方合作及其轉型
邊疆民族地區的地方合作可歸納為對口支援式與平等互惠型兩類。1979年“全國邊防工作會議”提出“要組織內地省市實行對口支援邊境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并確定北京支援內蒙古,河北支援貴州,江蘇支援廣西、新疆,山東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寧夏,全國支援西藏。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確立了全國19個省市分別援助新疆12個地(州)市的82個縣(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2個師。在援助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中央政府的動員和協調至關重要,這使得對口支援具有鮮明的動員性和政治性。“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積極完成中央的幫扶任務和支援,其工作得到中央的肯定,進入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評價。因而這類地方合作的進行可以使得支援一方的地方政府官員在政治上獲益,也就因此而獲得維持的動力”[10]。對口支援的另一特點是無償性,包括資金無償援助和物資無償援助。前者主要通過地方間的財政轉移支付進行,被稱為“交支票”援助;后者包括直接贈送(如設備)、建成后移交(如建筑物)等多種方式,被稱為“交鑰匙”援助。由于對口支援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訊、生活設施等方面,還具有基礎性特點。作為一種單向度的經濟援助,對口支援處于地方合作的最低層次。平等互惠是各方基于共同利益需求的一種市場化行為,屬于較高層次的合作形式。隨著經濟發展和基礎實施的改善,邊疆的地方合作正從對口支援向平等互惠過渡。
與對口支援相比,平等互惠合作具有自發性。青藏鐵路格拉段動工后,西藏首次提出利用青藏鐵路的交通優勢構建“青藏鐵路經濟帶”的提議。2005年,西藏與青海、青藏鐵路公司簽訂了《旅游合作協議》,成立了協調領導機構和定期磋商機制。互惠型合作要求各方均能從合作中獲益。2010年,新疆與重慶簽署能源戰略合作協議,重慶協助新疆建設準噶爾盆地東部地區至重慶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新疆則支持重慶能源投資集團在新疆開展煤電一體化項目,支持重慶企業參加“疆電外送”基地建設等[11]。互利性還體現在地方共同應對區域公共問題。黔、川、滇、藏、青等多省交界地帶民族結構復雜,邊界地帶治安問題突出。2010年,西藏、貴州、云南、青海與四川、重慶共同簽署“泛西南地區警務合作協議”,明確以情報信息互享、重大行動互援、執法辦案互助、治安管控互動、警務保障互補等5大機制為主的合作框架。2012年,新疆、西藏、青海通過《中國四大自然保護區協作會備忘錄》,提出建立“高原生態保護協作聯盟”協調“阿爾金山、羌塘、三江源和可可西里”四大自然保護區相關工作,并構建聯合、聯動、聯防的合作機制。國家援助的力量較為單一,主要來自政府和國有企業,如果沒有中央支持很難維持。平等互惠合作的推動力量相對多元,還包括私營企業、民營企業、社會組織等,合作更可持續。對口支援的投資大多來自政治上的需要,經常出現投資數量波動的情況以及投資無計劃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和“投產即虧損”現象。統計表明,至2009年,對口援藏單位累計建成援藏項目6300個,但超過70%運轉困難[6](P127~140)。2004年后西藏通過招商引資與內地進行產業合作的資金保持了穩定增長。截至2010年,招商引資金額已是援藏資金的3.4倍[12]。平等互惠合作大多簽署有正式協議,能夠較好規范合作主體的相關行為。因此,合作質量也較高。
在經濟區域化的推動下,中央把鼓勵互利合作作為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積極性的一種新手段。2011年,習近平在拉薩召開的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對口幫扶與互利合作相促進,努力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13]。為促進發達地區與邊疆民族地區開展經濟合作,中央通過官員對調、干部互相交流掛職等人事管理手段來加強地方聯系。2000年以來,廣西領導人調任四川以及湖南領導人調任新疆等人事安排都透視出中央對促進地方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構想。從效果看,人事調整后領導人的原任地和現任地之間的合作明顯增多。為推進互利合作,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根據資源條件和產業結構互補性調整了部分地區的結對幫扶關系。例如,東北三省對口支援資源氣候條件相似的北疆塔城、阿勒泰地區;山西對口支援同樣擁有煤炭資源的阜康市等地;重工業發達的山東則對口支援有色金屬礦藏較為豐富的喀什地區疏勒縣、英吉沙縣等。
由于國家戰略選擇重點與區域協調手段的局限性,形成我國發展格局中的“中心”與“外圍”二元區域結構,處于“外圍”的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需求容易滯留在國家體制外,無法整體進入國家發展戰略系統[14]。近年來,一些邊疆地方政府頻頻通過合作努力推動地方發展規劃進入國家戰略層面。比如,藏、滇、川聯合申報的“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已被列為國家重點旅游開發區域,三省正在共同爭取“川滇藏國際大旅游區”納入國家規劃;青、藏聯合擬定的《青藏經濟帶建設規劃大綱》已經上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云南與四川提出共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共同爭取國家生態環境建設投入和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對邊疆地區而言,采取“抱團”競爭策略意義重大。“民族地區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大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將可能在‘東西對話’和民族地區與中央的‘對話’中用同一個聲音說話,成為平衡經濟利益關系中‘在野的’不可忽視的一股政治力量……聯合的政治力量借助于非政治的組織載體對外發言,無疑具有更靈活的空間”[15]。
三、邊疆民族地區地方合作轉型的意義
平等互惠合作充分體現了地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以為邊疆地區的生產性活動提供激勵,也有利于邊疆對發達地區先進制度的借鑒和模仿。“從經濟發展來看,一個民族經濟進步的程度取決于他們所能獲得的向其鄰居們的經驗學習的機會的多寡,彼此接觸的方式越多樣化……那些最易與外界接近并有機會與其他民族集團發生相互影響的人們總是最有可能在經濟技術領域中躋身前列”[16](P83)。作為一種政治安排,對口支援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設計,面臨從政治任務向法律義務的轉變、協調支援方與受援地兩個積極性以及如何定位該制度下的地方政府間關系等難題。從國外經驗看,“除了優待政策之外,還存在其他的選擇,這些選擇在實行中可能起初代價大一些,而在實行一段時期后代價會減小。而且還會帶來較大的生產上升和民族和諧方面的利益”[17](P449)。自發、互利合作的基礎是經濟的互補性,地方根據發展需要投入資本、技術和設備,可以保障合作的可持續性。從長治久安的角度看,邊疆民族地區的不穩定有外源性因素,但規避邊疆安全風險的根本策略在于形成內源性發展動力。“與外控型穩定硬是用外在力機械地維護某種確定性不同,內生型穩定能使社會生活本身有機地生長出一種確定性,從而使社會穩定有牢固的內在根據”[18]。
多民族國家存在內部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如何相互交融的問題。地方合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融合經濟的發展。而且,合作領域越全面,區域一體化的程度也越高。2004年,廣西、貴州、云南等邊疆省區與福建、廣東等省共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建立了廣泛、全面的合作關系。目前,泛珠三角合作區域內有74個民族自治縣和蒙古、回、藏、苗、彝、壯等35個世居少數民族。西南經濟協作區成立后,地方聯合修補斷頭公路49條近千公里,跨區域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根據青海、新疆簽署的《關于加強兩省區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兩地將通過實施“西煤東運”戰略打通庫爾勒至格爾木的鐵路運輸通道。貴州、云南、西藏、新疆、內蒙古等與四川、陜西、甘肅等內陸省份簽訂了“中國西部道路運輸區域合作框架性協議”,正在聯合完善省際間的交通網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發布的《宏觀經濟周報》指出,中國各地區之間開始出現經濟趨同效應,驅動因素包括基礎設施改善和沿海企業轉移等,主要受益省區包括西藏、新疆等邊疆民族省份。正如歷史學家拉鐵摩爾探討中國邊疆問題時指出的,中國的統一性來自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經濟上的互補共生關系,中國是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動的“產物”[19](P298)。在互利合作加強的同時,地區與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日益密切,他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共同因素也會越來越多,因為“當邊遠集團開始參與全國的經濟體系時,它的結構關系將導致現代的以實效為中心的普遍主義的價值”[20]。
地方合作的轉型也有利于政治整合。“國家幅員遼闊通常會帶來多樣化的資源稟賦、巨大的潛在市場以及對外國原料和產品依賴較少的優勢。但同時也產生行政控制、民族團結和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問題”[21](P31)。由于我國地區差距的擴大,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已成為政治整合的一大障礙,“國內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加大并被固化,極有可能導致兩類地區對立和沖突”[22]。互利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扭轉地方政府“一畝三分地”的觀念,制約地方主義的增長,同時也可防止少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被邊緣化。邊疆省區地域廣闊且人口稀少,通過地方合作,還可以在不觸動行政區劃的條件下,改變政區面積過大導致的各種發展問題。
四、繼續推進邊疆地區的合作轉型
平等互惠型合作在邊疆地區還處于起步階段。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和專門的執行和監督機構,很多合作沒有具體的實施措施和配套政策,影響了合作的實際效果。從“西南五省區六方經濟協調會”“川甘青藏滇毗鄰地區民族友好經濟協作區”“華南和西南地區經濟合作區”的運行情況看,其合作成效低于“長三角城市經濟聯合會”“珠三角區域合作協調會”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我國沒有《政府間關系協調法》或《政府間合作法》,憲法中也沒有類似美國聯邦憲法中約束州政府合作行為的“協議條款”,地方合作缺乏法律規范,增加了邊疆省份開展跨區域合作的難度。
在激勵地方合作方面,中央可利用的手段有法律規范、政策誘導、資金支持以及地方的政績評價導向等。針對邊疆民族地區地方合作的特殊性,可由全國人大依據實施情況考慮制定一部《邊疆與內地合作法》或《邊疆內地合作條例》,為邊疆地區推進互惠合作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一些學者根據我國地方合作中存在問題提出中央應設立一個綜合性權威機構“區域協調管理委員會”。該機構由發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和區域管理專家組成,其基本職能包括協調不同地區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并約束地方政府行為、組織實施跨區域重大項目、審查和監督地方自主達成的合作協議和執行情況等,可考慮在此機構中單設負責推進邊疆地區開展地方合作的部門。邊疆地區推進地方合作時還面臨資金制約。比如,西藏昌都規劃的“茶馬古道”旅游合作戰略已經啟動很長時間,但進展不大,原因是沒有實施經費。國家應設立專項資金加大對邊疆開展互惠式合作的扶持力度,獎勵那些積極合作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在政績考核上鼓勵那些在互惠合作上取得成效的干部。
互惠合作的動力主要來自地方經濟差異,經濟互補性越強,兩地開展合作的可能性越大。2010年我國專門從少數民族發展資金中安排試點資金5700萬元支持邊境9省區的12個邊境縣開展興邊富民補助資金支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試點。邊疆民族地區應以國家資金支持為依托,重點培育和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為擴大互惠合作奠定經濟基礎。由于經濟發展是考核地方官員的主要指標,因此,邊疆與內地的合作大多集中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能夠直接促進經濟增長的領域。邊疆地區在推進與發達地區的地方合作過程中需要加強公共服務領域的合作,擴大合作的惠及面,這反過來也有利于地方合作的持續、健康發展。加強公共服務領域合作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能夠將經濟收益轉化為社會、政治效益,提升地方合作對邊疆長治久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