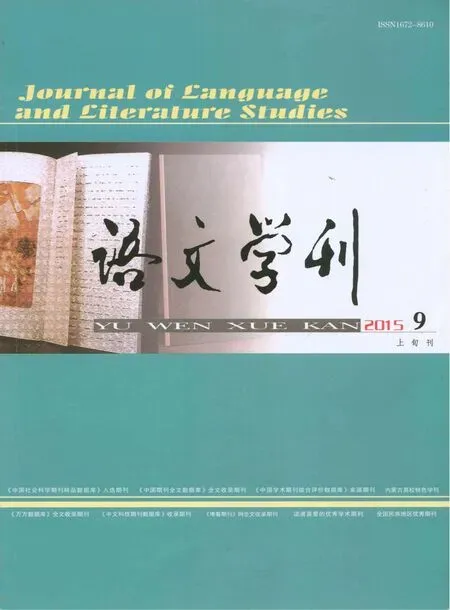慷 慨 激 昂 情 懷 家 國——讀吳奔星詩歌《湖南人進行曲》
○范果
(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湖南 益陽 413000)
吳奔星(1913 ~2004)先生是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湖南安化縣人。上個世紀20 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早在30 年代便發表了不少詩作,為現代派詩歌的重要成員。吳奔星先生倡導新詩現代化,畢生追求新詩的藝術探索,又將關注國家現實、民眾悲苦的襟懷融入詩歌創作之中,使他的詩歌創作具備現實的深度和廣度。《湖南人進行曲》正是這樣一首襟懷開闊、情懷家國的佳作。
1937 年11 月25 日《火線下三日刊》第5 期發表了吳奔星先生的新詩《湖南人進行曲》。吳奔星先生在這首詩后注明“寫于國府遷都重慶后二日”。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和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后,8 月14 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11月中旬,上海淞滬抗戰失敗已成定局,在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脅的形勢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自料南京無法堅守,遂決定依照既定方針,做出了遷國民政府于重慶辦公的決定。1937 年夏天,吳奔星先生從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畢業,正逢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吳先生回故鄉長沙后在母校長沙修業學校擔任教職,之后應任職于浙贛鐵路局的堂舅張自立先生邀請,擔任浙贛鐵路職工巡回教育隊隊長,宣傳抗日。[1]68-69這首詩正是在這種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創作而成,在高昂的愛國熱情之中又始終貫穿著濃濃的湖湘情懷。
我們來看這首《湖南人進行曲》:
我是湖南人,我是中華民,/我有高似衡岳的品格,我有浩若洞庭的胸襟;/我消閑時,許如岳麓秋風之長吟;/我鼓舞時,便如湘江浪波之狂奔。/目前大敵已來臨,肩頭責任有千斤;/我要如波浪之狂奔,無復如秋風之長吟,/進!進!進!填尸太平洋,阻擋敵艦西行!/四面謳歌聲:“若要中國亡,除非死盡湖南人!”/湖南人,不怕死,不驕矜,果敢,沉著,進行,進行!(寫于國府遷都重慶后二日)
此詩一開篇就飽含詩人作為湖南人的自豪之情,作為中華民中的湖南人,我有著“衡岳的品格”、“洞庭的胸襟”、“消閑時,許如岳麓秋風之長吟”、“鼓舞時,便如湘江浪波之狂奔”。詩人一開篇就用飽滿的故鄉情懷奠定了全詩慷慨激昂的基調。“消閑時,許如岳麓秋風之長吟”、“鼓舞時,便如湘江浪波之狂奔”。詩人運用擬人的寫作方法和形象生動的比喻,將一位胸懷家國、心憂天下的知識分子形象生動地呈現出來,為下文的抒情奠定了基礎。接下來,詩人直抒胸臆,“目前大敵已來臨,肩頭責任有千斤;/我要如波浪之狂奔,無復如秋風之長吟,/進!進!進!填尸太平洋,阻擋敵艦西行!”國難當頭,詩人感到責任與使命,于是直接抒發出要如波浪狂奔般積極進取的豪情壯志,要“填尸太平洋,阻擋敵艦西行”,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保家衛國抗戰中去的英勇悲壯的情懷。最后,詩人寫到“四面謳歌聲:“若要中國亡,除非死盡湖南人!”/湖南人,不怕死,不驕矜,果敢,沉著,進行,進行!”結尾處詩人用充滿力度的語言號召民眾要肩負起抗日救亡的使命,將濃厚的鄉情抒發到最高點,昂揚的愛國情懷中蘊含著濃厚的湖湘精神。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詩言志”的傳統,詩人往往能夠通過簡練的語言概括出現實經驗和歷史風貌。當國家民族面臨危難和戰爭的時候,詩歌往往能更加深入現實來反映對現實的批判和對外敵英勇抗爭的精神。而這種“詩言志”的優良傳統在不同的區域也呈現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湖南地區古稱荊楚,楚地獨有的地理特征、民情風俗,先賢圣哲的經歷形成了湖湘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湖湘文化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重經世致用”、“重踐履”。以屈原為代表的濃厚的愛國主義激情和憂國憂民的情懷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楚地人民集中體現了百折不撓的堅韌和不屈服于強人的性格特點。生于斯、長于斯的一代又一代湖南人深受這種文化沁潤,尤其是湖南籍的知識分子和文人們受影響更為深遠,湖湘地域文化特征在他們的創作中隨處可見。
吳奔星為湖南安化人,自幼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中濃重的民族情結和經世致用的學風融合在一起,使作者以經世致用作為治學和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在國家民族面臨危難時期必然體現出湖南歷代士人身上所體現的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因此吳奔星創作于抗戰爆發時期的這首詩作中蘊含有濃厚的湖湘文化意蘊。詩作中衡岳、洞庭、岳麓、湘江等詞語的運用不僅體現出湖湘特定地域標志和用語,同時也是具有深厚湖湘文化特質的象征物。“衡岳”即南岳衡山,“洞庭”即洞庭湖,岳麓山、湘江,這些都是湖湘特定地域的標志,同時也是湖南地域產生的特定用語。衡岳一詞象征著視野開闊、胸懷天下的高尚品格;洞庭一詞象征著磅礴的氣勢,博大寬廣的氣度胸襟;湘江作為湖南境內最大的河流,千百年來,奔騰不息,歷來就是湖南文人學士吟詠歌頌的母親河;而岳麓山承載了湖湘文化的發生發展和延伸過程,自古以來就傳承湖湘文化的精氣神,是湖湘文化的圣地。詩作中湖湘特定詞語和象征物的運用,凸顯出濃厚的湖湘文化意蘊,使全詩呈現出崇高壯美、深沉渾厚的氣度。
湖湘文化以經世致用為立身處世基本原則、以政治為人生第一要義的價值取向,逐漸形成“湖南存則中國存”、“天下一日不可無湖南”的強烈社會心理。而吳奔星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湖南革命斗爭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輩出、湖湘文化發出灼灼光輝的特殊歷史時期。這種“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邁精神已經深刻地影響著湖南的政治、軍事人才,同時也影響著湖南的知識分子和作家群體。于是詩人在此詩的結尾處壯懷激烈地寫道“進!進!進!填尸太平洋,阻擋敵艦西行!/四面謳歌聲:“若要中國亡,除非死盡湖南人!”/湖南人,不怕死,不驕矜,果敢,沉著,進行,進行!”。詩人將自己的命運與民族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這種內心深受湖湘文化浸染而蘊含的強烈愛國情結一經與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相結合,詩人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以社會政治功用為創作的第一要義,用手中的筆抗爭,弘揚出時代的主旋律,顯示出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和奮發進取的鋒芒。
抗日救亡的時代,關注現實的詩歌往往有著強烈的政治色彩,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吳奔星先生的這首詩歌不同于同時代常見的關于抗日題材的標語口號詩,形象生動的比喻與擬人的寫作手法讓全詩具有較強的藝術表現力,愛國情懷中融入濃厚的湖湘地域文化特征使全詩具備極強的感染力。此詩可謂時代的號角,生動反映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期知識分子以文字為武器并身體力行投身于抗日戰場,擔起文人肩頭的氣節和血性,在復興中華民族征途上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努力。
[1]吳星海.吳奔星新詩中的故鄉情懷[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
[2]吳心海.暮靄與春焰——吳奔星現代詩鈔[M]. 昆侖出版社,2012.
[3]田中陽.湖湘文化精神與20 世紀湖南文學[M].岳麓書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