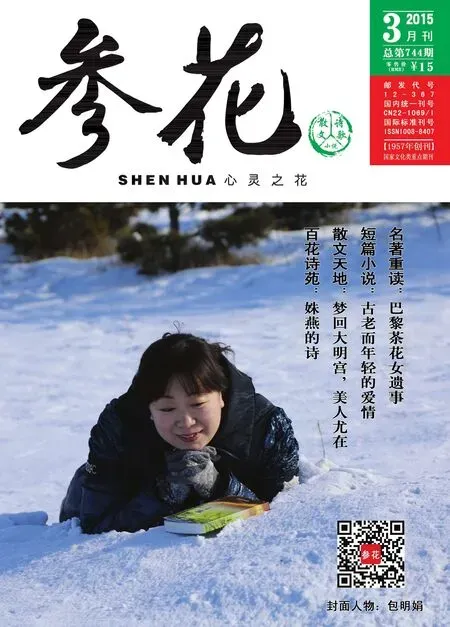古老而年輕的愛情
◎陳旸
古老而年輕的愛情
◎陳旸

徐旸正忙著結(jié)婚前一系列的準(zhǔn)備工作。整日穿梭在商場(chǎng),影樓,酒店,使她嚴(yán)重內(nèi)分泌失調(diào),長(zhǎng)了一臉的痘痘。就在她忙得昏天黑地,不知所為的時(shí)候,高中時(shí)的死黨打電話來,說她準(zhǔn)備跳槽,以后就不做麗江的包機(jī)了,如果最近有空,就趕緊趁她還沒跳槽,去麗江玩一趟,可以節(jié)約兩三千大洋。這樣的好事徐旸當(dāng)然不想錯(cuò)過。還好,未婚夫蕭力是個(gè)很會(huì)體諒人的男人,當(dāng)徐旸提出要去麗江時(shí),他笑說:“就沖你臉上這一臉的痘痘,我也得放你出去歇會(huì)兒,要不結(jié)婚那天人家還以為我接錯(cuò)了新娘。”
在家人的千叮嚀萬囑咐下,徐旸到了麗江。她走在這座石木古城里,踩著近千年的石子路,伴著潺潺的溪流,很快就融入到古城的氣氛中。
古城人很多,雖是三月初的旅游淡季,可還是熙熙攘攘。徐旸拖著大紅色的ELLE行李箱走進(jìn)一間叫做“吉祥吧”的小店。店中央站著一個(gè)高個(gè)兒小伙子,頭發(fā)一根根豎著,可能沒想到有人會(huì)在這時(shí)候進(jìn)來,愣了一會(huì)兒,徐旸沖著他微微笑了笑。他看了看她,說:“你替我看看店吧,我回來幫你安排住的地方。”然后望向她手上的行李箱。徐旸對(duì)他說的話并沒有思想準(zhǔn)備,本能的拒絕。可他并不理會(huì)徐旸的推辭,從吧臺(tái)后面拿出一些吃食,并把菜單遞給她。“找不到的就說沒有,我一會(huì)兒就回來。”然后匆匆離開了。留下徐旸一個(gè)人呆站在那里。
徐旸坐在臨溪的藤制秋千上,嚼著那個(gè)男人拿出來的魷魚絲,端詳著眼前的吉祥吧。
和大多數(shù)古城里的酒吧一樣。吉祥吧裝修很樸素,但卻很溫暖。一些綠色植物環(huán)繞在灑紅色的桌椅間。每張桌上的玻璃瓶里插著一枝康乃馨。吧臺(tái)邊,有一個(gè)黑色的書架,擺放著時(shí)尚雜志,隨筆,小說。墻壁上掛著刻了各色圖案的瓢和一些黑白照片。她希望能在照片上找到和剛才那個(gè)男人有關(guān)的東西,可沒有。如果這店不是他的,怎么辦?真希望現(xiàn)在一個(gè)客人也不會(huì)來。徐旸暗暗祈禱著。
如徐旸所愿,在那個(gè)男人回來之前,店里沒有來一個(gè)客人。他笑說,那是因?yàn)樽谇锴系娜瞬皇撬P鞎D也笑:“是啊,我長(zhǎng)得是很安全,所以才敢一個(gè)人出門。”
吉祥吧的老板叫黎振宗,兩年前從廣州過來的。之前做什么他沒說。他告訴徐旸,淡季,生意不好的時(shí)候,他就這么坐在秋千上,擺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態(tài),來吸引路過的客人,尤其是些單身女客人,她們大都眼神迷惘,如果哪位男孩想上前搭訕,就不要猶豫,麗江素有艷遇之城的封號(hào)。
黎振宗很熱情,他說徐旸可以每天到他這來吃免費(fèi)的晚餐,條件是下午三點(diǎn)替他看兩小時(shí)的店子。徐旸說沒問題,只要他不怕他的店提前關(guān)張就行。
黎振宗給徐旸安排的住處,在古城的一個(gè)高坡上,并不是徐旸希望的在水邊。他說,如果長(zhǎng)住的話,流水的聲音會(huì)讓你睡不著覺的。徐旸想想也是。
住的地方很干凈,白色的床單,白色的被子,白色的枕頭,透著新鮮的太陽的香氣。推開房間的窗子就是古城黑色的瓦頂,徐旸很滿意。告別黎振宗后,她開始給家里人發(fā)短信報(bào)平安。
收到蕭力的回復(fù):第一,注意安全。第二,不準(zhǔn)亂放電。
她回復(fù):遵命,大人!
第二天清晨被古城的雞叫聲喚醒,徐旸梳洗打扮了一番,開始在麗江古城游走。
來之前,對(duì)麗江的感覺都是道聽途說,而現(xiàn)在,徐旸要做的就是用眼睛,用腳,用心去觀察,欣賞古城,享受古城。
沒有去熱鬧的四方街,而是走到了古城深處,孩子們背著書包上學(xué),納西老人在樹下抽水煙,納西姑娘在院子里梳頭,還有阿貓阿狗的嬉戲。累了,隨便找間店吃一碗米線,然后又漫無目的地在古城里閑逛。對(duì)感興趣的店就多看兩眼,尤其是蠟染的桌布,長(zhǎng)裙,手刻的納西文字碟……特別喜歡的,和老板砍砍價(jià)。這些都讓徐旸覺得快樂。
中午,徐旸回到吉祥吧,遵照約定,她要幫黎振宗看兩小時(shí)的店子。吉祥吧一如既往的無人光顧。黎振宗看見徐旸很高興,從廚房端出一盤黑乎乎的丸子:“這是魔芋丸子,我加了蟹粉在里面,你嘗嘗。”
“有點(diǎn)咸。”徐旸嘗了一個(gè)說。
“是有點(diǎn),明天我少加點(diǎn)鹽。”黎振宗說。
黎振宗又去廚房做了納西炒飯端出來。很辣但很好吃。
徐旸覺得很奇怪,在古城里和人交往是這么容易。
三點(diǎn),黎振宗出了門。徐旸還是坐在臨溪的秋千上曬太陽,不一會(huì)兒就睡著了,等黎振宗回來,她還沒醒,也不知道這期間是否有客人來過。
上玉龍雪山是徐旸第三天的安排。因?yàn)槠鸬帽容^晚,沒趕上去雪山的大巴士。租了一輛小車,司機(jī)安排她去牦牛坪。
到牦牛坪,徐旸才真正體會(huì)到什么是旅游淡季。上山的纜車上只有徐旸一個(gè)人。偶爾看見一兩個(gè)游人坐在對(duì)面下山的纜車?yán)铩K麄儗?duì)著徐旸喊著:“很冷的,上面很冷的。”說話間還把脖子往衣領(lǐng)里縮。徐旸也喊:“是很冷,我跟你們一塊兒下去吧!”對(duì)面?zhèn)鱽硭实男β暋?/p>
從纜車上下來,是個(gè)平臺(tái),雪山就在左前方。沒有想象中壯觀,也就沒什么特別感受,草還沒來得及變綠,望不到邊的一片黃,很安靜。整個(gè)牦牛坪就一條路,是用原木做的棧道,順著棧道瀏覽,就是觀賞牦牛坪的方式。
沒有想象中成群的牦牛,整座山上唯一的一頭牦牛,被它的主人拴在柵欄上,披著一塊紅布,招攬游人合影。一個(gè)男人正蹲著身子,給牦牛拍照。他皮膚白皙,手指修長(zhǎng),左手的小拇指上戴著一枚亮閃閃的白金鉆戒。徐旸想,他是絕不知道大米白面多少錢一斤的。那男人拍完照,和耗牛的主人聊了會(huì)兒,便朝前走去。徐旸也跟著往前走。這一走才發(fā)現(xiàn),整座山,只有他們兩個(gè)人。
徐旸跟著他看山,他在哪拍照,她也在哪拍,他在瑪尼堆上放一塊石頭,她也跟著放一塊。他還沒走到棧道的盡頭就往回返了,徐旸也就跟著他往回返。徐旸就這么遠(yuǎn)遠(yuǎn)地跟著這個(gè)男人,開始只是覺得會(huì)比較安全,不久就發(fā)現(xiàn)這其實(shí)是件很有趣的事。
估摸著那男人已經(jīng)坐上下山的纜車了,徐旸才走進(jìn)纜車檢票口,可沒想到那男人站在纜車的入口處,一支手撐著入口的圍欄。徐旸沒有退路,只能裝作什么也沒發(fā)生過,走到入口處,很友善地朝他笑了笑。沒想到那男人突然說:“我下午去瀘沽湖,你也跟著嗎?”
徐旸臉紅了,呵呵地傻笑起來。那男人也跟著笑。兩個(gè)人坐同一輛纜車下了山。男人很主動(dòng)地介紹說:“我叫崔承德,昨天從北京來的。”
徐旸說:“我叫徐旸,從武漢來的,在麗江呆了三天。”
崔承德說:“呆了三天,真讓人羨慕,我明天下午就回北京,總共也只能呆三天。我還是從公司溜出來的。下午我真去瀘沽湖,一塊吧?”
徐旸笑著說:“我可不是跟著你去。”
崔承德笑著說:“那就當(dāng)我跟著你吧,畢竟你比我來的時(shí)間長(zhǎng)。”
徐旸想了想,瀘沽湖也是計(jì)劃內(nèi)的行程,于是點(diǎn)點(diǎn)頭:“好吧,我?guī)闳o沽湖。”
有了新目標(biāo),下山的速度就快起來。徐旸給黎振宗打了電話,告訴他晚上不回他那兒吃飯了,她要去瀘沽湖。黎振宗說他會(huì)另找人幫他看店。
徐旸其實(shí)很納悶,她很想知道為什么黎振宗每到下午三點(diǎn)都要找人幫忙看店。可黎振宗對(duì)他的離開總是只字不提。
在古城里買了炸雞和可樂就上路了。司機(jī)是當(dāng)?shù)厝耍漳尽{惤镜厝耍恍漳揪托蘸蹋渌男蘸苌佟?/p>
從麗江到瀘沽湖大約六小時(shí),絕大部分都是山路。在耗牛坪消耗了一些體力,兩個(gè)人在車上很快就睡著了。等徐旸睜開眼,看見十八彎的山路,覺得自己對(duì)司機(jī)太信任了,于是睜大眼睛,一旁的崔承德卻睡得很香,嘴角時(shí)不時(shí)還蠕動(dòng)一下,很可愛。
木司機(jī)按照慣例在瀘沽湖的觀景臺(tái)前停了車。快到傍晚時(shí)分,觀景臺(tái)上沒別人。司機(jī)說,這是觀賞瀘沽湖全景的最佳地點(diǎn)。徐旸叫醒崔承德,拉著搖搖晃晃的他下了車。
太陽還沒退隱,沒有風(fēng),湖水很平靜,泛著點(diǎn)點(diǎn)粼光。四周的山如同一個(gè)堅(jiān)強(qiáng)的臂膀,環(huán)抱著他心愛的姑娘。他們都沒說話,不知道是因?yàn)檎也坏胶线m的形容詞,還是擔(dān)心自己的聲音會(huì)破壞這平靜的畫面,一直沉默著。
“走吧,到湖邊還有一段距離,天晚了,路就不好走了。”木司機(jī)對(duì)他們喊道。
雖然有些責(zé)怪木司機(jī)的審美疲勞,但想著能近距離地一睹“睡美人”的芳容,心里又無比興奮起來。懷揣著無限的期盼,兩個(gè)人瞪大了眼睛,等待著睡美人的出現(xiàn)。
住的屋子離湖不到二十米,這讓他們很滿意。這是個(gè)由四棟兩層樓房組成的四合院。所有的住宅都是用原木交叉搭建的。房東說,這叫木楞房。院子里很熱鬧,三只雞,一條高大的黑狗,兩只貓。
圍坐在房東家古舊的火盆邊,徐旸和崔承德像兩個(gè)虔誠的求道者,傾聽房東講述摩梭風(fēng)情。而在摩梭風(fēng)情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摩梭人的走婚習(xí)俗。正規(guī)地說應(yīng)該叫阿夏異居婚。阿夏就是指親密的情侶,異居婚也就是男女雙方婚后并不在一起生活,男不娶人,女不嫁出,男阿夏只有在夜晚到女阿夏家居住,早晨便返回母親的家中勞作。建立阿夏關(guān)系,完全依靠雙方的感情,是不受地位,財(cái)富的影響的。“這點(diǎn)倒是比現(xiàn)代城里人要可靠得多。”徐旸聽完房東的介紹對(duì)崔承德說。
崔承德笑著說:“那你就留在這里吧,我也留下。呵呵。”
房東太太準(zhǔn)備好晚飯叫他們,餐桌上擺著剛剛談話時(shí)提到的豬膘肉。可能是一路上太累的緣故,加上湖邊氣溫又很低,兩個(gè)人吃得都很多。崔承德的臉在酒足飯飽后漲得通紅。徐旸說總算在他臉上看到了點(diǎn)人氣。
被房東拉著去參加當(dāng)?shù)氐捏艋鹜頃?huì)。一路步行,碰到一些和他們一樣趕去晚會(huì)的游人。
滿天星斗的時(shí)候,篝火在另一個(gè)院子里燃起,散落在落水村的游客團(tuán)聚在一起。村里的青年們也換上艷麗的本民族服飾。
崔承德牽起徐旸的手加入了舞蹈的隊(duì)伍。火光映紅了每個(gè)人的臉,洋溢著幸福的微笑。有節(jié)奏的舞步,歡快的歌聲,彌漫,擴(kuò)散,漸漸消融在寂靜的湖里。
篝火漸燒漸弱,人群也逐漸散去,一切又重歸于平靜。在湖邊的圓木上坐下,背靠著背,傾聽湖水拍打岸邊的聲音。心緒漸行漸遠(yuǎn)。記憶里那些深深淺淺的人像湖水一般,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涌上岸來。
是崔承德打破了寧靜:“這兒真好,不用趕時(shí)間,像中了大獎(jiǎng)一樣,時(shí)間可以任由我揮霍。”
徐旸笑說:“明天有些人就得回北京了。可能只是個(gè)末等獎(jiǎng)吧。”
崔承德笑了,突然問道:“你結(jié)婚了嗎?”
徐旸淺淺的笑了:“實(shí)話說,我馬上就結(jié)婚。”
崔承德說:“馬上,明天嗎?”
徐旸說:“明天和誰結(jié)呢,除非今天能在這里找個(gè)阿夏,而且,而且得忘掉家里的那個(gè)阿夏。”
崔承德顯然有點(diǎn)失望:“那你家里的阿夏是怎樣的?”
徐旸笑說:“中國人,男性。呵呵。”
崔承德笑了。又是一陣沉默。徐旸陷入了深深的回憶里。
“好吧,滿足一點(diǎn)你的好奇心。講講我家里的阿夏。”這樣的環(huán)境讓徐旸有了傾訴的沖動(dòng)。
蕭力,她回家就要嫁的人。求婚的時(shí)候,是在她家所在小區(qū)的街心花園里。當(dāng)徐旸還在為要不要嫁而猶豫不決的時(shí)候,是他的一句話讓她下了決心。“你不嫁我,誰來照顧你呢?”
讀書的時(shí)候,蕭力比徐旸高一屆。那年,徐旸生日那天,正逢每周一次的鋼琴課,徐旸出門時(shí)發(fā)現(xiàn)下雪了,覺得騎自行車會(huì)比較好玩,就騎車去了,來回騎了近三個(gè)小時(shí)。回家看見姐姐站在門道里——她忘了帶鑰匙。門口堆著一堆年貨,姐說是單位發(fā)的。當(dāng)一件一件地往屋里搬年貨的時(shí)候,徐旸發(fā)現(xiàn),有一棵盆景,用閃亮的玻璃紙包著。冬天能看到綠葉紅花,讓徐旸眼前一亮。“姐,你們單位還發(fā)這個(gè)呀?”
姐說:“哪是發(fā)的,是你一個(gè)同學(xué)送的生日禮物。”
徐旸說:“我同學(xué)送你的生日禮物?”
姐說:“你怎么那么笨吶,送你的,一個(gè)叫蕭力的。”
徐旸看著這個(gè)盆景,發(fā)起呆來。
姐說:“長(zhǎng)得不錯(cuò)喲,像高倉健。”
徐旸傻愣愣地看著這個(gè)盆景,心里說不上是什么滋味。
每天,她都很細(xì)心地去照顧它。澆水,剪枝,孰不知冬天不宜澆太多水,這盆叫不出什么名的小花,沒過多久就夭折了。
雖然有了這盆景,可徐旸和蕭力見面也僅僅是限于同學(xué)間的點(diǎn)頭微笑而已。直到夏天,蕭力畢業(yè),要回海南他的家鄉(xiāng)。臨行前,他才鼓足了勇氣去了女生宿舍。
學(xué)校后面的人工湖旁,雖沒有瀘沽湖這么壯觀,卻也和今晚一樣平靜。
蕭力對(duì)著湖,并不去看徐旸的眼睛:“我過兩年就會(huì)回來的,希望你能等等我。”
徐旸看著他的背影,什么也沒說。她不清楚這叫什么。
蕭力轉(zhuǎn)過身,看著徐旸:“等我,好嗎?”
“為什么要等?我不會(huì)等的。”徐旸抬起頭,看著他,語氣堅(jiān)定。
片刻,沒了聲息。徐旸等不到他的回答,扭頭離開了。
再見面已是兩年后,徐旸因腎結(jié)石復(fù)發(fā),在家休息。蕭力敲響了她家的門。
姐姐開了門,一眼認(rèn)出蕭力,立馬跑進(jìn)房對(duì)徐旸說:“那個(gè)高倉健來了。”
徐旸納悶,問她:“哪個(gè)高倉健來了?”
“雪中送花的那個(gè)!”姐姐笑道。
徐旸下意識(shí)地看了看放在窗臺(tái)上的那個(gè)空花盆,種花的那缽?fù)吝€在里面。姐姐笑她:“你明明知道嘛!”
兩年沒有任何聯(lián)系,突然站在自己面前,徐旸有點(diǎn)恍惚。這個(gè)比兩年前更黑,更壯的青年,曾經(jīng)送過一盆花給她。也許還試圖在校園后的人工湖邊向她示愛,可終究沒有說出口。
蕭力給她講述著這兩年的生活。說他用兩年時(shí)間,成為公司駐漢辦的經(jīng)理,就是為了能常遇到同學(xué)們。姐聽他這么一說,笑了:“不是吧,是想見我妹妹吧。”
蕭力和徐旸尷尬的臉紅了。
第二天,蕭力又來了,帶來一株茉莉花,種在那缽?fù)晾铩?/p>
在適宜植物生長(zhǎng)的春天,茉莉花長(zhǎng)得特別旺盛。正如他們倆的愛情。
崔承德問:“那你還是等了他兩年?”
徐旸說:“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他,至少?zèng)]有刻意去等,時(shí)間很快就過去了。過去的兩年總讓人覺得很快,可未來的兩年,人們會(huì)覺得很漫長(zhǎng)。”
崔承德說:“他求婚的那句話,好經(jīng)典,是從哪本書里抄的吧。”
徐旸笑說:“ 也許吧,呵呵,這句話很受用,你可得好好記住。”
崔承德說:“我還沒地方說呢。”
徐旸問他:“總會(huì)有的,北京女孩很漂亮的。不過,你好像不是北京人吧?”
崔承德說:“我是福建人。”
徐旸笑了:“聽口音就是南方人。福建人很有錢喲,都有生意頭腦。”
崔承德說:“我們家是很有錢。呵呵。”
這兩聲笑卻透著些無可奈何的意味。
徐旸拍拍他的頭:“有錢總比一無所有強(qiáng)啊。”
“可能吧!”崔承德低下了頭。
崔承德的家有多大,他到現(xiàn)在還不清楚。父親是福建省某個(gè)地稅局的局長(zhǎng)。母親在當(dāng)?shù)刈畲蟮囊患曳b公司做會(huì)計(jì)。他哥哥十歲的時(shí)候,母親懷了他。八個(gè)月的時(shí)候被人告發(fā),當(dāng)時(shí)正在風(fēng)頭上,影響特別大。父親所在地的地委書記親自找他談話,希望他放棄這個(gè)孩子。但父親沒有服從領(lǐng)導(dǎo)意志,而是安排最可靠的人把母親送到湖南,在當(dāng)?shù)匾患倚♂t(yī)院,生下他。
他一出生,父親的官職被撤了。父親索性離開了地稅局,利用以前的關(guān)系做起了外貿(mào),十幾年時(shí)間就發(fā)展成一個(gè)跨國經(jīng)營的公司。
十五歲,崔承德初中畢業(yè),被父親送到澳州念書,他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在澳州的太太和他兩歲大的小妹妹。
父親在菲律賓還有個(gè)太太,崔承德沒見過,只知道那個(gè)太太替父親生了對(duì)雙胞胎弟弟。這都是母親告訴他的。
崔承德今年從澳洲回國,到北京找到十幾年沒見的哥哥。哥哥幫他安排到現(xiàn)在的這個(gè)貿(mào)易公司,就沒再與他聯(lián)系。哥哥說,很忙。
“你爸不會(huì)是摩梭族吧?”徐旸開玩笑說。剛說出口,覺得這話確是有點(diǎn)傷人了。
“我媽說,我爸到哪都有人照顧,這不是很好嗎?”崔承德輕輕地說。
為了打破尷尬的氣氛,徐旸問道:“說說你喜歡的女孩子吧。”
“我第一個(gè)喜歡的女人,是我的小學(xué)美術(shù)老師。呵呵,我那時(shí)候就不老實(shí)了。跟蹤老師回家,給她男朋友的自行車放氣。那是我至今唯一有想法的女人,我那時(shí)候真打算長(zhǎng)大和她結(jié)婚的。”崔承德認(rèn)真地說。
徐旸哈哈大笑起來:“會(huì)有合適的女孩等著你的,適合做你老婆的不是只有那個(gè)美術(shù)老師一個(gè),只是你還沒碰到罷了。”
月光照著斑駁的樹影,和靜靜的湖水一道傾聽著這對(duì)年輕人的故事。
“回去吧,明天早晨看日出去。”徐旸站起來。
“回去嘍!”崔承德對(duì)著湖面喊道。
轉(zhuǎn)身離開的時(shí)候,徐旸撿起一塊石頭,輕放在經(jīng)幡下的瑪尼堆上,默默地祈禱著。遠(yuǎn)遠(yuǎn)地看見家家戶戶的窗前映著溫暖昏黃的燈光。
沒有像預(yù)計(jì)的那樣看到日出,等徐旸睜開眼,推開向湖的窗子時(shí),朝陽的光輝已經(jīng)灑滿整個(gè)湖面,給湖水映上了燦爛的色彩,也給這只晚起的懶豬無比的滿足。
房東說,沒坐過豬糟船,就等于沒來過瀘沽湖。叫上崔承德,去湖面泛舟。這是徐旸的第一個(gè)想法。
劃船的摩梭女臉上掛著兩朵高原紅,普通話講得很好。旁邊幫忙搖漿的是個(gè)四川女人,相比之下,她的普通話就顯得有些笨拙了。
崔承德笑說:“一看你就是剛來的,你看你的高原紅都沒曬出來。”
四川女人笑了,笑得很燦爛,露出兩排潔白而整齊的牙。
“你們真幸福,能天天在湖上劃船。還能掙到錢。”崔承德羨慕地說。
摩梭女笑著說:“如果不是為了掙錢,在湖上劃船會(huì)更快樂的。”
徐旸看著這個(gè)摩梭女,她說的話真有道理,和經(jīng)濟(jì)搭上邊就沒有了純粹的快樂了。
四川女人說:“覺得好就留下來吧,像你這種斯斯文文的男孩子,在我們這兒是很受女孩子歡迎的。”
徐旸看著紅著臉的崔承德笑說:“您這句話他聽懂了。”
崔承德無話可說,接過徐旸手里的漿劃起來。船上的三個(gè)女人卻笑得合不攏嘴。
因?yàn)榇蕹械乱s下午的飛機(jī)回昆明,泛舟也就顯得有些匆匆了,豬糟船在落水村靠岸。岸邊,竟有幾匹健碩的馬。馬夫朝他們揮著手:“騎馬吧!”
崔承德有些躍躍欲試。徐旸卻有些害怕,她從沒騎過馬。
“它不會(huì)把我摔下來吧?”徐旸緊張地問。
“不會(huì)。”馬夫牽過一匹年幼的白色小馬,“我們牽著呢。”
徐旸在崔承德的幫助下艱難地爬上馬背,可還是有些膽怯。馬夫騎著另一匹馬走在前面。
“千萬別跑,就這么慢慢地走,很好。”徐旸說。
馬夫說;“走慢了,屁股會(huì)疼的。”
徐旸急了:“疼就疼吧,總比從馬背上摔下來好。”
崔承德騎著另一匹馬走在旁邊,教她:“腳用力往下踩,用力夾住馬肚子,屁股稍稍翹起來一點(diǎn),身子往前面傾,把馬鞍上的扶手抓牢就沒問題了。”
正如徐旸不理會(huì)崔承德一樣,馬夫也不理會(huì)徐旸的反對(duì),牽著那匹小馬跑起來,徐旸大聲叫著:“快停下來,快停下來。”
崔承德跟在后面喊著:“腳用力往下踩,手抓牢就沒問題。”
徐旸試著做了,感覺馬匹走得比較穩(wěn)了,馬夫松了韁繩,馬越跑越快,徐旸的心開始嘭嘭亂跳起來。手腳全然不聽使喚,那匹還沒長(zhǎng)大的小馬受了驚,一路狂奔起來,眼看著徐旸的一只腳就要從馬鐙里掙脫出來了。崔承德和那馬夫都有些著急了,快速追上去。可怎么也抓不到那匹馬的韁繩。徐旸騎在馬背上手足無措地亂叫著,崔承德也沒多想,迅速從馬背上跳下來,跑上去,抓住了那匹小馬的籠頭,那馬總算在主人的安撫下,平靜下來。徐旸此時(shí)倒像是粘在馬上了,說什么也不敢下來。崔承德一把抱住她,把她從馬背上扛了下來。
徐旸被剛才的險(xiǎn)情嚇呆了,即使穩(wěn)穩(wěn)當(dāng)當(dāng)?shù)卣驹诘孛嫔希蛇€是覺得不踏實(shí),渾身的骨頭像散了架一樣,腦子里一片空白。是怎么上的回麗江的車,她都記不起來了。
到麗江已經(jīng)是下午三點(diǎn)多了,崔承德從車上下來的時(shí)候右腳腫得已經(jīng)不能著地。原來他從馬背上跳下來的時(shí)候,扭傷了腳。徐旸剛剛放松的神經(jīng)又緊繃起來。趕緊送崔承德上了醫(yī)院,拍片結(jié)果,右腳根骨骨裂。打上石膏,纏上繃帶,去昆明的飛機(jī)已經(jīng)飛走了。
徐旸只好帶著崔承德去了吉祥吧。
當(dāng)徐旸扶著打著繃帶的崔承德走進(jìn)吉祥吧時(shí),黎振宗正忙著給客人們調(diào)酒。店里多了個(gè)穿著納西服裝的小阿妹。找了個(gè)靠門的位置坐下來,小阿妹給他們倒了兩杯茶。
沒做過多的解釋,黎振宗很爽快地安排崔承德在店里和他同住。崔承德很感激。
一切安排妥當(dāng),徐旸回到住處,洗完澡發(fā)現(xiàn)手機(jī)上有條短信,是蕭力的:你選的藍(lán)色窗簾已做好,下午我親自把它裝上了,等你回來欣賞。
徐旸回復(fù):辛苦你了。今天很累,先晚安了。然后倒頭就睡。
太陽爬上古城的屋頂,徐旸才起床,古城里的各色店鋪大開其門開始迎接八方來客。四方街上,穿著納西服飾的少婦正在跟游人討價(jià)還價(jià)。
徐旸沒有停留,直接去了吉祥吧。要為崔承德買機(jī)票,租車,送他上飛機(jī),她甚至還考慮,是送到機(jī)場(chǎng)還是索性送他到昆明轉(zhuǎn)機(jī)。她為自己這些想法感到好笑。怎么到了麗江就成了活雷鋒了。
走進(jìn)吉祥吧,吧臺(tái)后面的黎振宗就沖著徐旸揚(yáng)了揚(yáng)頭,順著他的目光,徐旸看見崔承德正和三個(gè)老外交談。一人拿著一支太陽啤。
“一大早就喝啤酒呀?”徐旸對(duì)黎振宗說。
“現(xiàn)在不是一大早了,如果你現(xiàn)在還躺在床上,是不是說現(xiàn)在天還沒亮呢?”黎振宗打趣地說。
“不用這么損吧,我好像跟你還不是很熟吧。”徐旸說。
“哈哈,原來不熟呀,小姐這邊請(qǐng),您需要點(diǎn)什么呢?”黎振宗指著吧臺(tái)近處的一張桌子對(duì)徐旸說。
“我要這個(gè),這個(gè),還有這個(gè)。”邊說,邊在菜單上一陣亂點(diǎn)。然后兩人笑作一團(tuán)。
啤酒喝完,老外起身告辭。很禮貌地跟吧臺(tái)前的黎振宗他們道別。
崔承德對(duì)他們喊道:“HAVE A GOOD DAY!”
一個(gè)扎著黃色頭巾的年輕小伙子轉(zhuǎn)過頭,笑著說:“EVERYDAY!”
徐旸好奇地問崔承德:“你們聊什么呢?”
“什么太極呀,八卦,陰陽呀,這些我都不太清楚,而且那三個(gè)是法國人,說的英語我都聽不太明白,只能應(yīng)付應(yīng)付了。”崔承德說。
“我看你們有說有笑的,挺好的嘛!”徐旸說。
“我可是搜腸刮肚找了很多內(nèi)容,為了黎哥嘛。”崔承德得意地說。
“算我的免費(fèi)食宿沒有白費(fèi)。麗江的外國人當(dāng)中最多的就是法國人,法國人浪漫。”黎振宗說。
“而且很優(yōu)雅。”徐旸附和道。三個(gè)人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起來。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徐旸突然問道:“你還不去收拾一下,等會(huì)兒我送你去機(jī)場(chǎng)。”
“現(xiàn)在想起這個(gè)了,早買不到機(jī)票了。我不走了,跟著你啊。”崔承德說。
徐旸蔫蔫地說:“跟著我干什么?”
“別開玩笑了,”還是黎振宗關(guān)鍵時(shí)候給徐旸解了圍,“等他腳好了再走,先在我這住著,早上已經(jīng)跟他們公司請(qǐng)好假了。”
“那我是不是也要扭傷腳呢,可以在這多待幾天。”徐旸羨慕地說,“在這里可以吃黎哥的納西炒飯,魔芋丸子,喝黎哥調(diào)的不知道叫什么酒的酒。最主要的,是不用付錢。呵呵。”
“不用扭傷腳也可以給你吃,給你喝。是吧?”崔承德說著望向黎振宗。
“我可沒說。我跟這位貴婦也不熟。她是要付錢的。”黎振宗笑著說。
“我?guī)退丁!贝蕹械绿统鲥X夾往桌上一拍。
“毛病!”徐旸給了他一個(gè)大白眼。
徐旸每天起床后就到吉祥吧報(bào)到,陪著黎振宗去市場(chǎng)買菜,幫著招呼店里的客人,跟黎振宗學(xué)習(xí)調(diào)制他說不出名的那種酒。
也許福建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崔承德建議黎振宗用一串串小葫蘆做成弧形窗簾,掛在臨街的窗上。窗子中間掛上象征吉祥的中國結(jié)以吸引游人的注意。果不其然,很多游客因?yàn)橄矚g這景致,會(huì)停下來拍照,每每這個(gè)時(shí)候,崔承德都會(huì)招呼他們進(jìn)來坐一坐。他總說:“進(jìn)來參觀一下吧,吉祥吧,免費(fèi)參觀的。”
崔承德的這些做法,為黎振宗招攬了很多客人,這些客人走進(jìn)店里,然后就會(huì)叫上一壺茶,一點(diǎn)小吃,或者品嘗黎振宗調(diào)的酒。當(dāng)然也有人只是看了看就要走的。碰上這樣的客人,崔承德會(huì)說:“坐會(huì)兒歇歇再走吧。”有些客人會(huì)被他的盛情留下。只點(diǎn)了茶的,崔承德會(huì)讓黎振宗送一碟瓜子。碰到單獨(dú)來進(jìn)餐的客人,他會(huì)送去一杯熱茶,或者兩個(gè)黎振宗做的魔芋丸子。客人們臨走的時(shí)候,他會(huì)祝福那些客人吉祥如意。
他為酒吧帶來很多回頭客。每當(dāng)他的“改良”舉措收到效益的時(shí)候,他都會(huì)得意地朝著徐旸他們搖頭晃腦地笑笑。
黎振宗每天下午三點(diǎn)照例會(huì)獨(dú)自出門,五點(diǎn)左右回來。他從不說他出去干什么,每次面對(duì)徐旸他們疑惑的雙眼,他總是報(bào)以燦爛的笑容,來打消他們的疑慮。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徐旸的假期很快就要結(jié)束了。她沒有按計(jì)劃去香格里拉,沒有去虎跳峽,每天在古城的吉祥吧里享受古城的慢生活。
臨行前一天,徐旸去聽了納西古樂。從演奏廳出來,徐旸突然有種莫名的情緒。有些傷感,有些郁郁寡歡。
古城的布局也很有意思,演奏廳對(duì)面就是現(xiàn)代的酒吧一條街,每天從四面八方來的阿哥們隔著酒吧門前的溪水與當(dāng)?shù)氐陌⒚脗儗?duì)歌。喧囂的酒吧街被高高掛起的一串串紅燈籠包裹著,如同披上一層紅色的細(xì)紗,火紅的一片。狂放的歌聲和來自唐代的靡靡之音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人們用不同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感。
回到吉祥吧,正是生意最好的時(shí)候,納西小妹忙著給各桌的客人端茶送水。黎振宗在吧臺(tái)后面忙著調(diào)他的招牌酒。
各式各樣的人聚在一起,他們可能剛剛才認(rèn)識(shí),可能是戀人,可能是朋友。在昏黃的燭火里,幽暗的燈光下,用不同神態(tài),不同姿勢(shì)交流著自己和別人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崔承德坐在溪邊的位置,看著從上游漂流下來的河燈。一個(gè)長(zhǎng)發(fā)女孩因?yàn)楹ε滤暮訜舫寥胨铮恢备:訜艉雒骱霭担目呐雠觯诤拥乐新h(yuǎn)去。女孩子也跟著消失了。
“你說結(jié)果會(huì)怎么樣?”崔承德問徐旸。
“什么結(jié)果?”徐旸說。
“那個(gè)女孩的河燈呀?”崔承德說。
“不知道。總會(huì)漂到盡頭的吧?”徐旸怏怏地回答。
“要是我,就到盡頭把它拾起來,再送給別人放。呵呵。”崔承德看起來特別開心。
“呵呵。你怎么這么高興呀,我明天就走了,你也該表示出一點(diǎn)點(diǎn)的依依不舍吧,讓我好過一點(diǎn)吧!”徐旸說。
“對(duì)啊,好舍不得呀,不走吧。”崔承德把臉湊到徐旸跟前。
“是啊,好舍不得呀!”黎振宗學(xué)著崔承德的腔調(diào)走到徐旸跟前。三個(gè)人頓時(shí)笑成一團(tuán),惹得酒吧的客人們側(cè)目。
“納西古樂聽得怎么樣?”黎振宗問她。
“很好吧,我對(duì)音樂沒多少研究,別人都是用耳朵聽,我是用眼睛看。都是六十到九十歲的老人家。每曲演奏完,他們都會(huì)閉上眼睛休息一會(huì)兒。嘴角還掛著那種似有似無的微笑,很祥和。”徐旸說。
“其實(shí),那些演奏的老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黎振宗說。
“那你的故事是怎樣的,我明天就要走了,告訴我們吧,每天下午三點(diǎn)你出去干什么?”徐旸終于忍不住地問道。
黎振宗看著徐旸和崔承德,想了想,說:“我去民航大樓等機(jī)場(chǎng)大巴。一個(gè)朋友要坐三點(diǎn)的機(jī)場(chǎng)大巴來麗江,我去接她。”
“每天都去接朋友嗎?”崔承德問。
“每天都去接,每天都沒有接著。”黎振宗說。
徐旸和崔承德面面相覷。
黎振宗三年前到麗江旅游。認(rèn)識(shí)了一個(gè)北京女孩。在麗江這樣一座古城里,初次相見時(shí)的喜悅,就像碰巧落地的菌絲,幾天就能長(zhǎng)成一個(gè)大蘑菇。即使是一點(diǎn)點(diǎn)曖昧的感覺,也能釀出甘醇的美酒來。
徒步虎跳峽回來,黎振宗確信自己愛上了這個(gè)北京女孩。女孩得知后,消失了兩天。
兩天后,她找到黎振宗的住處來,看到女孩深陷的雙眼,黎振宗當(dāng)時(shí)就有一種不祥的預(yù)感。女孩說:“有些事我必須告訴你,因?yàn)槲蚁矚g你。”
黎振宗說:“喜歡就夠了,我不想聽別的。”女孩繼續(xù)說:“我是個(gè)未婚媽媽,有個(gè)女兒,是剖腹生下來的,現(xiàn)在肚子上還有一道疤。”
黎振宗愣愣地站在房間里,不知道說些什么。等他清醒過來,女孩已經(jīng)離開了。
女孩回北京之前,留下她的E-MAIL。
看到她的郵箱地址,黎振宗知道,女孩說喜歡他是非常認(rèn)真的。
回到廣州,黎振宗就給女孩寫了信,結(jié)束了廣州的業(yè)務(wù),來到麗江。
“那天終于收到她的信,說她會(huì)坐第二天的飛機(jī)來麗江,坐三點(diǎn)的機(jī)場(chǎng)大巴到古城。”黎振宗說。
“她沒來嗎?”崔承德問。
“沒來,我等到最后一趟大巴的乘客全部下了車,也沒看到她。”黎振宗搖搖頭。
“我給她E—MAIL留了言,說我在古城等她,總得給點(diǎn)時(shí)間讓她明白。”黎振宗說。
“等了兩年嗎?她沒回信呀?”崔承德問道。
黎振宗沒有回答,只是說“每天下午去民航大樓已經(jīng)變成了我的習(xí)慣了,不管她來不來,我每天都會(huì)去看一看。”
“是啊,接不到北京姑娘,接個(gè)上海姑娘也行。”崔承德打趣地說。
徐旸瞪了崔承德一眼。
黎振宗低下頭,微微地笑了。
熱鬧的酒吧安靜下來。納西小妹已經(jīng)回家休息了。月色輕柔地?fù)崦懦堑钠唔敚齻€(gè)坐在水邊的年輕人靜靜聆聽著流水的聲音,內(nèi)心里黯淡的情緒也隨著這流水慢慢遠(yuǎn)去。
在民航大樓的院子里,站著黎振宗和徐旸。崔承德因?yàn)槟_不方便,沒有來。這讓徐旸多少有些失望。
黎振宗笑笑,對(duì)徐旸說:“來麗江這么多天,知道麗江有三多嗎?”
徐旸說:“不知道,哪三多?”
“‘雕’民多,‘瓢’客多,賣‘銀’的多。”徐旸笑了。
大巴司機(jī)催著徐旸上了車,徐旸微笑地朝他揮了揮手,沒有什么比笑著分別更好的了。徐旸心里想著。當(dāng)大巴駛出民航大樓的院子時(shí),徐旸看見了拄著拐杖的崔承德,他站在院子的大門口,目光跟著大巴移動(dòng),徐旸臉上的笑容凝滯了,她本能地朝他揮著手,崔承德?lián)P了揚(yáng)頭,笑了。可徐旸卻哭了。
新郎在等我,還有我的藍(lán)色窗簾。徐旸不住地提醒自己。
回到武漢,生活并沒有多少改變,還是那間辦公室,還是那張辦公桌。每天早晨在上班的巴士站上,見到的還是那些相同的情景,巴士一來,人們還是爭(zhēng)先恐后地上車。
新房的家具送來了,和預(yù)訂的顏色有些偏差。蕭力和送貨的小工爭(zhēng)論起來。徐旸拉著蕭力,說這個(gè)比預(yù)訂的那個(gè)好看。倒不是真的覺得這個(gè)好,只是現(xiàn)在她提不起任何興趣。斜靠在剛剛送來的大床上,看著她千挑萬選的藍(lán)色窗簾,這就是她即將生活的家。
蕭力打發(fā)走小工,一反身把徐旸抱起來,像抱著個(gè)孩子一樣,用手臂托著她:“老婆,這窗簾是我掛上的,我能干吧?”
徐旸高高地看著他:“能干,誰能比我們家力力能干呢。”雖然笑著,可徐旸心里知道,這笑容多少是有些不真實(shí)的。
婚期越來越近。第二天徐旸就要去婚紗店挑選婚禮當(dāng)天穿的婚紗了。說好在結(jié)婚前要給崔承德報(bào)喜訊的。吃過晚飯,徐旸打開郵箱想給崔承德寫一封信,可她卻在未讀郵件里,意外地發(fā)現(xiàn)有崔承德的一封信。郵件里有好多她的照片。全是崔承德偷拍的,有在牦牛坪燒香的,有在瑪尼堆上放石子的,還有為了不讓崔承德發(fā)現(xiàn),在棧道上裝著左顧右盼的。還有幾張是在落水村騎馬時(shí)和馬夫一塊聊天的……
崔承德在信里說:“這些都是你跟蹤我的證據(jù)。嘿嘿,沒想到吧。
我的腳傷快好了。這就意味著我在麗江待的時(shí)間不長(zhǎng)了。一直沒有收到你的信,不會(huì)這么快就把我們忘了吧。
你說回去就結(jié)婚的,結(jié)了嗎?雖然從你那得知,你的未婚夫是個(gè)很好的人,你會(huì)很幸福,可還是希望你沒結(jié)婚。我真這么想的。我也是個(gè)好男人。
昨天陪黎哥去了民航大樓,黎哥還是沒有接到他的北京女孩。我當(dāng)時(shí)真希望,你會(huì)從那大巴上下來。真的!如果你說你要來,哪怕只是說你想來,我也會(huì)像黎哥那樣天天在民航大樓的院子里等你的。”
徐旸看著這封信,突然有了再去云南的沖動(dòng)。她站起來,抬眼看到放在窗臺(tái)上蕭力送的茉莉花。初春,那株茉莉花已經(jīng)發(fā)了新枝,嫩芽。她呆呆地看著那缽花,又坐回到桌邊,關(guān)掉電腦,雖然知道眼淚是最沒有用的東西,可她還是無助地哭起來。
“怎么啦?旸旸,你怎么了?”姐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進(jìn)來的。
“姐,我怎么辦吶?”徐旸擦了擦眼淚,無助地看著姐。
“什么怎么辦?又長(zhǎng)痘痘啦?”姐姐看著徐旸的臉問。
“沒有。”徐旸別過臉去。
“那什么怎么辦?”
“我,我不想結(jié)婚了。”
“是現(xiàn)在不想,還是一輩子都不想啊,你不會(huì)是婚前恐懼癥吧?”
“姐,我好像,好像喜歡上別人了。”
“哪個(gè)別人?誰啊?你想嫁別人,不想嫁蕭力?”
“不是,我沒說要嫁別人。”
“那不就成了,你又不想嫁別人。”
“姐,我說的是真的。”
“你不喜歡蕭力?”
“不是。”
“那就是說,你喜歡蕭力也喜歡他。”
“姐,怎么一到你嘴里,就聽起來那么別扭呢。”
“不是我說的別扭,你自己想想,這事本身就別扭。好吧,你告訴我,他是誰,你們同事?”
“不是,是在云南認(rèn)識(shí)的。”
“一個(gè)云南人?”
“不是,是福建人。”
“在云南認(rèn)識(shí)的福建人,干什么的?”
“做外貿(mào)的吧,不是很清楚。你干嘛老問這些呀?”
“傻丫頭,你不知道這些怎么去和他生活。喜歡上一個(gè)人其實(shí)很容易,尤其在麗江那點(diǎn)小地方。那是去度假的,除了玩,游人還做什么?結(jié)婚就像坐火車一樣,到那站才能下車。不能說,每一站風(fēng)景都美,你每一站都下吧。今天去麗江認(rèn)識(shí)一個(gè)福建人,不想結(jié)婚了,明天認(rèn)識(shí)一個(gè)廣東人怎么辦?”
“我到麗江沒有玩。姐,我不是那樣的人。”
“姐沒說你是那樣的人。我是說適合做你丈夫的其實(shí)有很多,可人們不總在追求那個(gè)唯一嗎?你一輩子會(huì)碰到許多優(yōu)秀的人,可能你們還會(huì)互相欣賞,可那只是欣賞。即使是有那么一點(diǎn)心動(dòng),你也該考慮清楚,你的方向是什么。結(jié)婚前碰到這種事算你幸運(yùn)。現(xiàn)在你好好想吧,誰會(huì)是你想要的那個(gè)唯一。”
“姐就是我的唯一。”徐旸摟住姐姐,不想去考慮這個(gè)問題。
“算了吧,肉麻死了,是誰幾個(gè)月前決定要搶在姐之前結(jié)婚的,你快嫁出去吧。讓爸媽也早點(diǎn)省心。嫁對(duì)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不知道才煩。”
“自己的事自己怎么會(huì)不知道,我去睡了。明天如果去選婚紗,就早點(diǎn)叫我。”
說完,姐姐離開了。
沒有麗江的月亮,沒有古城的瓦頂,窗臺(tái)上,只有蕭力送來的那盆茉莉花,在晚風(fēng)中招搖。徐旸把那缽花拿進(jìn)屋來,放在床頭柜上。想起在婚紗店排隊(duì)拍照時(shí),蕭力曾向她計(jì)劃過他們的未來:“兩年內(nèi),買一輛國產(chǎn)車,這樣老婆懷孕的時(shí)候,就不用再擠巴士上班了。然后,爭(zhēng)取在五年內(nèi),買第二套房,在郊區(qū)買,周末的時(shí)候就帶著一家老小去郊外垂釣。”
崔承德難道不會(huì)為我做這些嗎?在麗江那地方,幫黎哥看著他的吉祥吧,也會(huì)很滿足的。
各種各樣的念頭在徐旸的腦海里變換。可不管怎樣,她都沒想過要現(xiàn)在結(jié)婚。逃吧,現(xiàn)在就逃吧。徐旸從床上爬起來,收拾了簡(jiǎn)單的換洗衣物,悄悄溜出了家。
街上幾乎沒有人,現(xiàn)在去哪兒呢?昏黃的街燈把她的身影拉得好長(zhǎng),她站在十字街頭,沒有了方向。一輛晚歸的的士緩緩?fù)T谒媲埃緳C(jī)探出頭來,問:“小姐,去哪兒呀?”
徐旸上了車,“濱江花園”四個(gè)字脫口而出。那里有她的新房。那是她現(xiàn)在唯一能去的地方。
“濱江花園”小區(qū)里,只有一家的燈還亮著。等她看清才發(fā)現(xiàn)是自己新房的燈。難道白天離開的時(shí)候沒有發(fā)現(xiàn)燈是亮著的。
徐旸小心翼翼地打開那扇門,卻看見蕭力蹲在客廳里。她的梳妝臺(tái)放在客廳的中央,客廳的地板上鋪著牛皮紙。“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呀?”徐旸看著蕭力問道。
蕭力像做了錯(cuò)事被發(fā)現(xiàn)一樣:“沒干什么。”
“沒干什么,我難道有幻覺了。這梳妝臺(tái)怎么回事,還有這油漆,這刷子。”徐旸打量著地板上亂七八糟的一堆說。
“沒有什么,我知道你不喜歡家具的顏色,所以在家居市場(chǎng)看見有你喜歡的那種木紋貼紙,就買了一些。我跟木工們打聽過了。先把這貼紙貼在家具上,然后刷上清漆,就和成品家具一樣了。可惜不能把整套家具都換上你喜歡的顏色。知道你最愛臭美,梳妝臺(tái)先換件衣裳吧。你看我都貼好了,嚴(yán)絲合縫的,一眼看不出來。再刷上清漆就好啦。”
徐旸看著眼前被蕭力重新包裝的梳妝臺(tái),都不知道說什么好了。蕭力得意地說:“很不錯(cuò)吧?”
“回去休息吧,很晚了。”徐旸憐惜地看著蕭力說。
“刷上了清漆就回,很快的,否則新娘結(jié)婚那天就沒梳妝臺(tái)用了。”于是蕭力拿起油漆刷一點(diǎn)點(diǎn)地刷起來。徐旸站在一旁,呆呆地看著。“對(duì)了,你這么晚到這兒來干什么?”蕭力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來了,揚(yáng)起頭問她。
“幫你刷油漆呀,呵呵!”徐旸戴上地板上另一只手套,和他一塊兒刷起來。
第二天一大早,徐旸就敲響了姐姐的房門,“姐,快起來,我要去選婚紗了。”
姐從床上坐起來:“還是結(jié)婚啦!”
“都說今年是六十年才一次的金狗年,當(dāng)然要結(jié)婚。”徐旸斬釘截鐵地說。
“是跟蕭力結(jié)嗎?”姐打趣地問她。
徐旸沒閑心理會(huì)姐姐的調(diào)侃,掀起姐的被子,把她拉起來:“快起來吧,今年結(jié)婚的那么多,去晚了,好看的都被別人挑走了。”
(責(zé)任編輯 象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