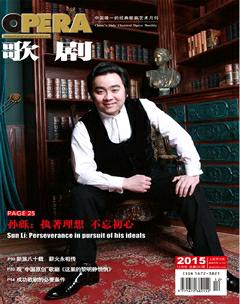突顯宗教訊息 救贖靈魂不易
周凡夫
作為法國歌劇經典的《浮士德》,無論是演繹處理、制作設計,還是內涵解讀,都給后人留有頗大空間。但無論如何取舍。作為歌劇迷。首先聚焦關切的,仍是作為歌劇藝術核心所在的音樂。這次作為今年澳門國際音樂節閉幕節目的歌劇《浮士德》,卻可將演繹、制作和內涵解讀的取向結合音樂的表現一起來評說。
全是大教堂外觀“變奏”
將靈魂出賣給魔鬼來換取人世間欲望的滿足,是激發無數藝術家創作出不少文學藝術作品的西方傳奇故事,歌德的偉大詩劇更將其影響力提升,使之在哲學與宗教的深度上成為后世藝術創作的靈感泉源。古諾的《浮士德》其實是當年眾多相同題材歌劇中能留存于樂史上唯一的一部,但歌劇腳本只取材于歌德詩劇第一部分,而且重點放在歌德添加進去的浮士德與瑪格麗特的愛情故事(故事重點亦放在瑪格麗特)。為此,德國上演該劇時常易名為《瑪格麗特》,不但在于更清晰地展示古諾歌劇的重心,更有對歌劇并非展示“浮士德哲理”的異議。
事實上,很多導演對此劇的處理都將重點放在浮士德與瑪格麗特始亂終棄、帶著矛盾罪惡感的愛情故事。這次制作的導演——活躍于美國歌劇界的卓斯·雷德-史爾巴(ChasRader-Shieber),不知是出于偶然還是刻意,從第一幕開始,無論是布景的設置、演員的表演、音樂的處理和導演的手法,處處都突顯出這部歌劇所帶有的強烈宗教訊息,展示出作為虔誠教徒的古諾的宗教信念。劇中情節更呈現了人間善惡之爭、利欲圣潔之爭、沉淪救贖之爭。
羅伯特·帕茲奧拉(Robert Perdziola)五幕七場的布景,無論是浮士德的書房、城門口,還是瑪格麗特家的花園,甚至監獄,全部是大教堂外觀的“變奏”:不僅如此,好幾個場景的設計,都突顯鮮明的宗教象征,如第二幕以耶穌像代替了原設計酒館掛著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招牌、第三幕花園中的圣母像、第四幕第二場教堂內的告解壇。還有最后一幕的“天梯”,都具有很明確的宗教色彩。
首兩幕善惡爭逐交鋒
古諾在每一幕都將世人追逐權力欲望、寧愿屈從魔鬼、離棄上主的矛盾作為主題,雷德一史爾巴亦通過不同方式將這一主題突顯出來。第一幕浮士德與魔鬼梅菲斯特的交易奠定了這一重要主題的前提,奈何飾演浮士德的男高音迪亞高·施華(Diego Silva)的唱功一般,音色較為單一,欠缺男主角應有的迷人魅力;相對而言,扮演魔鬼梅菲斯特的低男中音韋恩·泰格斯(Wayne Tigges)的音色變化則較豐富,亦較有穿透性和戲劇色彩,在第一幕兩人的對手戲中,便占了上風。但即使如此,第一幕的表演處理仍嫌拘謹,兩人背負的善惡之爭的戲劇性矛盾沖突亦未見突出。
相比之下,第二幕的宗教主題處理更為突出明顯。先是華倫丁唱起有名的歌謠曲“全能上帝”(又名“告別家門”):“當我即將走向戰場時,把妹妹拜托給上帝,請求上帝永遠守護著她。”為宗教訊息作鋪陳,梅菲斯特打斷瓦格納所唱的“老鼠之歌”,唱出劇中第一首動聽的詠嘆調“金牛犢之歌”(Le vuaud'or est toujours debout),泰格斯便很能唱出歌詞中對世人追逐名利權欲的諷刺,對人世間追名逐利的嘲弄;與此同時,華倫丁對妹妹瑪格麗特的擔憂,及妹妹向他送上象征宗教力量的十字架飾物作戰場護身符,則表現出世人對魔鬼攻擊的警惕;及后華倫丁拔劍與梅菲斯特相斗,劍被折斷后,仍以象征宗教力量的劍柄十字逼退梅菲斯特。如果說第一幕浮士德簽下出賣靈魂的契約是魔鬼的勝利,第二幕便是宗教力量再占上風:在這一幕中,飾演華倫丁的男中音特洛伊·庫克(Troy Cook)帶有戲劇性色彩的歌聲與演技已展露出光彩。他和梅菲斯特的對手戲,亦能擦出矛盾的戲劇性火花。
第三幕邪惡力量猖狂
第三幕由女中音亞歷山德拉·申克(Alexandra Schenck)反串演唱愛慕瑪格麗特的愛人席貝爾的一曲“花之歌”(Faites-luime8 aveux),雖然音質稍欠渾厚,但仍能唱出患得患失的心情:從開始手觸鮮花時發現果真如同梅菲斯特的咒語所示,鮮花頓時枯萎而驚惶失措,到嘗試在圣水盤中洗手得以破除惡咒,最終將鮮花留在瑪格麗特家門,同樣彰顯了正邪相爭邪不勝正的宗教力量。申克年紀不大,假以時日,累積更多經驗,歌聲和處理應會再上層樓。然而,在這一幕中才讓女主角發揮其歌唱技巧的名曲“珠寶之歌”,卻是一首與“金牛犢之歌”呼應的諷刺歌曲。女高音佐治亞·雅文(Georgia Jarman)很能把握女性面對熠熠生輝的珠寶時難以把持的情感——既興奮、有點忘形,但又有點遲疑。她融合了抒情和花腔特點的歌聲,結合豐富的身體語言,可謂將“珠寶之歌”這首名曲發揮得淋漓盡致,盡管并未達到光芒四射的效果,但聲音甜美,而且懂得掌握表達劇中人物的心理變化。
第三幕女主角瑪格麗特面對珠寶和浮士德甜言蜜語的誘惑,最終跌入梅菲斯特所設的情欲陷阱,而女中音艾琳·莫里納莉(I.Molinari)飾演的瑪格麗特之友馬塔,在得知丈夫陣亡后,亦被梅菲斯特的假言假語弄得神魂顛倒。兩人唱得傳神,都唱出了世人在物質情欲誘惑下淪落的寫照。
接下來第四幕華倫丁在梅菲斯特的“作法”下分神,死于浮士德的劍下時,更全面宣示了魔鬼邪惡力量的猖狂。而庫克所扮演的華倫丁在臨終前的一大段痛責瑪格麗特的唱段,再度發揮其聲音與情感的完美結合,讓人聽來動容。
宗教救贖訊息被打消
歌劇后段,在教堂中瑪格麗特祈求上主寬恕,梅菲斯特假扮成接受瑪格麗特告解、蒙著黑頭巾的神父,如此設計將宗教包羅了上帝與魔鬼的兩面特性呈現,更加強了宗教性的色彩;由此,將劇情發展推進到宗教性色彩最濃的最后場景——在監牢中的瑪格麗特終得到救贖,在天使伴隨下靈魂升上天堂,全劇在戲劇高潮中結束——按理聲勢效果都應不俗,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究其原因,是這次制作在第五幕第二場囚牢中瑪格麗特獲得救贖前,采用了法國大歌劇插入芭蕾舞的形式來打造華麗場面。這次插入的芭蕾舞段由上海戲劇學院附屬舞蹈學校的十多位女舞蹈演員擔演,但編排的并非當年古諾為巴黎大歌劇院改編時取材于歌德《浮士德》原劇第二部分華爾普吉斯之夜(walpurgisNight,即五月一日之夜)舉行的魔女歡宴傳說中的各種舞蹈。其實舞蹈是否配合劇情發展已無關緊要(法國傳統大歌劇中的舞蹈場面幾乎全是僅為打造華麗場面而設,常常與情節內容全無關系),這亦正是現在通常演出《浮士德》時一律刪掉這些場面的原因。很難理解這次澳門的制作為何要以“復古”之名多花一筆舞蹈演員的制作費,還徒然拖慢了演出節奏。
不僅如此,這一大段無關痛癢的芭蕾舞跳完,舞蹈演員退場后(首場演出還發生了點“意外”:其中一位舞者,側身邊跳邊退場時。臺位出現誤差。險些整個人撞到場邊的側墻上,引得觀眾發出很不合時宜的笑聲)、瑪格麗特重現舞臺時,大幕竟然于音樂聲中徐徐落下。最后齊齊停止!好幾分鐘后,大幕才在再度響起的音樂中升起。這一落幕中斷,是因為要在原來的監獄場景正中。加上向上延伸的天梯,好能演出最后的場景。梅菲斯特不斷壓迫掙扎著的瑪格麗特,一再高唱她已遭天譴!最后,在場外代表天使的合唱唱出她已被寬恕的歌聲中,瑪格麗特一步一步走上天梯,象征她已得到救贖,并升入天堂。浮士德很艱辛地走上數級梯級便痛苦地停下來,而冷眼旁觀的梅菲斯特則變得無比痛苦。此時大幕落下,音樂亦停止,全劇結束。然而,相信好些觀眾仍在期待著后續,原因是應有的救贖高潮與基督得勝的氣氛仍未出現。就這樣,一場芭蕾舞和一堂大樓梯場景,便將整晚四幕不斷營造的宗教救贖訊息打消了。這的確是這次制作的最大敗筆!果真是靈魂的救贖不易!
舞臺特技驚喜全欠奉
為求突顯宗教氣息,劇中不少可供發揮“舞臺特技”的場面處理,都采用了較平實的手法,并未有讓人驚喜的效果。如第一幕安排梅菲斯特于停尸床上揭布而起(和通常的處理有點不一樣);浮士德背對觀眾而坐,還由梅菲斯特站在椅后遮擋,讓其脫去大衣,然后以重返青春的面貌面對觀眾:第二幕雕像取酒、第三幕梅菲斯特于花園水井中以升降臺來去(全無劇場特效),只需“一揮手”便將園景由白晝變為燈光閃閃有如繁星的浪漫黑夜(這個點很是驚喜!);最后一場暗示瑪格麗特殺死自己的孩子的戲份也省去了,至于以高大長梯級來作為升上天堂的設計更極具象征意義……可以說,如期待會有舞臺特技的驚喜的觀眾,便準保失望!
至于擔任合唱部分的西西里島抒情合唱團,雖不至讓人失望,但表現只算合格。第四幕著名的《士兵大合唱》,歌者們靜止著“排排唱”的處理形式非常呆滯,混聲合唱效果亦稍顯不足,使得最后一場的合唱效果與宗教性色彩同樣不夠。
為這次《浮士德》的演出擔起骨干作用的澳門樂團,在歌劇經驗豐富的音樂總監呂嘉的指揮下,既能將樂池的音樂與舞臺上的歌聲頗為準確地連結起來,對劇情推進的節奏掌握亦很不錯,有好些場景的氣氛營造很有效果。前三幕的場景很不相同——第一幕浮士德的書房陰沉詭異:第二幕城門口不同人物不同感受和欲望交織:第三幕瑪格麗特家的花園從日間到夜晚的浪漫迷情——樂隊都提供了很好的音樂氣氛,睢第四幕的教堂場景較弱,而第五幕囚牢所帶有的宗教性色彩同樣顯得較為薄弱。
“心水清”的觀眾當會留意到,該制作是世界著名的芝加哥抒情歌劇院(Lyric opera of chicago,香港文化局中譯為“芝加哥歌劇院”并不準確)和澳門國際音樂節的聯合制作,但仔細看后發現,參與演出的歌唱家基本上沒有在芝加哥抒情歌劇院版中演出過,合唱團、樂團亦與芝加哥無關。看來只是將芝加哥的布景服裝等買來(或租借來),再組班演出:在這種情況下,由同一卡司連演三晚,對演員體力及嗓子是莫大的挑戰,這亦正是筆者再三思量下,放棄觀賞11月1日音樂節的閉幕演出而選看第一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