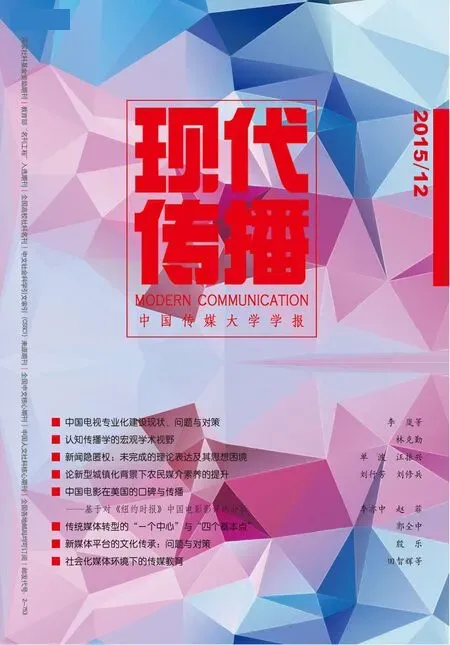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電視劇審美形態的變遷*
■ 熊文泉
大數據時代電視劇審美形態的變遷*
■ 熊文泉
中國電視劇已然建立起一整套與電視傳媒相適應的審美形態,即“與日常生活同質同構”的話語秩序和“分集敘事、長篇連續”的電視文類、“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的“三貼近”創作原則、“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和諧”的“三性統一”精神向度和“國家調控”“藝術自律”與“市場調節”三個系統“沖突與共謀”的藝術生產范式。進入大數據時代以后,電視劇的審美形態勢必進入新一輪的變遷,及時就其文本形態、審美范式等方面的變遷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大數據;電視劇;審美形態
中國電視劇從誕生之日起,其審美形態一直在變,歷經了“戲劇化”“小說化”“電影化”“電視化”“商品化”“快餐化”“娛樂化”“家庭倫理化”“日常生活審美化”等一系列萌動、喧囂與升華,已然結晶出自身獨特的審美形態:文本形態①方面建立起“與日常生活同質同構”的話語秩序和“分集敘事、長篇連續”②的電視文類;在創作原則上形成了以“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實際”為基本導向的現實主義風格;在精神向度上確立了“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和諧”的“三性統一”結構;在藝術生產機制上則生成了“國家調控”“藝術自律”與“市場調節”三個系統“沖突與共謀”范式③。
然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類生活正在發生新的變革,2013年被稱為大數據元年。影視行業,以好萊塢電影《點球成金》《少數派報告》和美劇《紙牌屋》的巨大成功為標志,奏響了大數據進行曲。對中國電視劇來說,大數據既是機遇,更是壓力與挑戰,因此,對其審美形態領域即將產生的變遷進行及時的、必要的理論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身份的危機:從影響的焦慮到文本的形變
何謂大數據?何謂電視劇的大數據?有論者認為,影視行業的大數據,主要是指用戶大數據、內容大數據和渠道大數據。④還有人指出,大數據的戰略意義在于專業化的數據“加工”,以實現數據“增值”⑤。上述概論都對,又都不盡然。對于電視劇審美形態而言,大數據將人類的全部知識與經驗完整地呈現在面前時,一如整個星系撲面而來,令人瞬間掉入一種白洞,其背面是將宇宙“歸零”的黑洞。這種黑洞式的“零度審美”與大數據對審美經驗與審美創造的“歸零”,是一個全新的臨界點,既是制高點,又是新的最低點,人類的審美模仿史因此具有無限可能。
大數據不只是海量的數據,更是一種新的方法論、新的觀念、新的生態環境。
面對大數據時代的挑戰,中國電視劇的反應略顯倉促而凌亂。電視劇藝術工作者普遍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曾經由制片人捧著票子擠破頭“加磅”的戰爭題材劇突然間就風光不再了,原本“得婆婆媽媽者得天下”的家庭倫理劇也日漸失寵了,編劇藝術的創新也變得越來越艱辛,一直財大氣粗主宰市場的省級衛視一下子集體成了“弱勢群體”!
中國電視劇的變革勢必加速,從近兩年中國電視劇的生產與收視境遇來看,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2013年電視劇熱點零落,在央視和省級衛視播出的800多部作品中僅有2部的收視率超過2%”,呈現出“收視困境”和“創新乏力”⑥的疲態。
一方面,傳統的類型化道路已漸漸后繼乏力,舉步維艱——抗戰劇已成了“雷劇”“神劇”的代名詞,諜戰劇需要國家安全部門的批復,家庭倫理劇亦已乏善可陳,“一劇兩星”的“首輪發行”規則倒逼電視劇進行降低成本多出精品的改革……,2014年以來,要是沒有《長沙保衛戰》《平凡的世界》等幾部厚重的作品,對于左右傳統電視收視率的大爺大媽和主導劇評的中年精英來說,恐怕鮮有能看得懂的,更別說“點贊”了。
另一方面,電視劇網絡化道路卻初露端倪,威力驚人。2013年以來,網絡小說改編劇風景獨好,贏得了年輕人的追捧與學界熱議。《裸婚時代》《步步驚心》《花千骨》《瑯琊榜》《云中歌》《華胥引》《盜墓筆記》等都取得巨大成功,盡管故事單薄、情節簡單、人物蒼白、思想膚淺、語言生猛,完全脫離了傳統好劇的評價體系,但它們火了!
這一退一進,絕非偶然,乃至有論者驚呼——“要變天了!”雖然還有待于時間與實踐的檢驗,但電視劇的電視媒介屬性正受到越來越嚴峻的考驗,是不爭的事實。整個電視傳媒都在加快與網絡的融合,所以,電視劇網絡化,甚至變成網絡劇,就是大勢所趨了。
網絡傳媒的媒介屬性比電視媒體更平等、更自由、更開放、更虛擬、更個性、更私密、更民間……,而我國電視傳媒是一種主流媒體,肩負著建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發揮輿論導向功能的重任,并內化為電視劇的美學特質。
如是,網絡化的電視劇文本將發生哪些變化?歷經幾十年風雨鑄就的電視劇審美形態將何去何從?
首先,基于傳統電視媒介建立起來的“分集敘事、長篇連續性”文體將失去存在依據。從理論上說,網絡媒介屬于時間上無間斷、空間上無區隔的流媒體,不存在間斷性,也就無所謂連續性,每個網絡中的個體可以根據自身條件自由出入。電視臺的頻道制與播出的時效性,決定了電視時空的碎片化存在方式和單向性。所以,網絡化之后的電視劇,“連續”二字就顯得沒有必要,為了生產的方便,定義為長篇、中篇、短篇即可,一如小說文本。當前網絡上出現的所謂網絡劇大都難以和電視劇的質量相提并論,每集10分鐘左右的容量更像是網絡小說“燴”段子。但其碎片化的短平快風格以及大膽的表達方式預示著某些電視劇網絡化的未來發展。
其次,電視劇中包含了主流意識形態屬性、大眾文化特性和藝術家的審美追求,“三性統一”的精神結構正是這種復雜意識形態的歷史選擇。電視融入網絡之后,電視劇的“三性統一”結構必將打破,在自由化、個性化、多樣化、多元化道路上漸行漸遠。
再次,電視劇是一種家庭收視、民眾集體參與的日常審美活動,深深扎根于現實生活的土壤,故形成了“日常生活審美化”敘事風格以及“溫暖現實主義”的審美語態等特質。網絡的虛擬性、私密性、開放性等媒介特性將賦予網絡化電視劇新的敘事風格與言說方式,“網絡寫作的匿名性”與“眾聲喧嘩”必將打破“主旋律協奏”模式,從而呈現網絡文學所具有的一切“后現代文化特征”,即“歷史理性的顛覆”“反對權威拒斥中心”“主體零散化”“距離感消失”⑦,等等。
如此,電視劇的名稱是否合法?電視劇的身份是否要變?電視劇是因電視媒介而生的審美活動,所以,電視媒介與互聯網之間的融合與裂變,直接決定電視劇的存在方式和命運。
若電視傳媒徹底被互聯網吸收,電視劇勢必改弦更張,完全成為網絡劇。目前,我國網絡劇市場方興未艾,騰訊、愛奇藝、優酷等各大視頻門戶網站先后發布宣言,向自制、定制網絡劇市場進軍,很快就凝聚了一大批在電視劇圈內具備話語權的制作人、導演、編劇,網絡劇的“力量”與“野心”足見一斑。
無論電視劇的身份如何變遷,傳統的電視劇藝術生產方式必然要經過一番揚棄以順應新時代的要求,既要克服傳統的經驗主義,又要力戒技術決定論。如何合理運用大數據,進行市場預測和“期待視野”分析,甚至深入到文本形態、審美結構的選擇,是當前學界的重要課題。然而,電視劇創作畢竟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活動,需要創造出“陌生化”的藝術語言和“活的形象”,以折射出藝術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情感追求,這些,決不是大數據可以“算”出來的。
二、模仿的位移:從現實模仿到虛擬模仿
電視劇,誕生于機械復制時代,因屬于大眾文化而飽受批判,如“削平深度”“快餐消費”“垃圾文化”“藏污納垢”,等等,甚至有些取得收視率佳績的作品也不例外,能夠被稱為優秀電視劇的大都是對日常現實生活的模仿,遵從現實主義的藝術模仿律,可謂之現實模仿。
真實再現客觀現實生活,創造出豐富完滿的典型,是現實模仿一以貫之的美學追求。進入現代工業技術時代,由于以手工為基礎的古典模仿變成了以機械復制為手段的現代模仿,影視藝術作品雖然失去一點“靈暈”,但依然以現實為摹本,模仿律的根基并沒有動搖。本雅明所說的客觀事物是有“靈暈”的,是指某種能夠刺激藝術家頭腦中產生靈感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受此時此刻的制約”,當然不會轉移到復制品中,也就“不可能被模仿”。⑧靈暈的消失對于攝影藝術來說,也許是一種遺憾,但對于主要語言為敘事材料的電視劇來說,似乎很牽強。電視劇是一種復合藝術,模仿的核心是通過演員的表演與語言藝術講故事、塑造角色。
大數據時代,機械復制技術已翻篇為數字模擬技術,藝術模仿進入了“數字虛擬”時代。盡管電視劇審美形態的外部狀態已經發生了諸多變化,但其審美本質沒變,依然是一種融合了多種單一藝術形式的復合模仿藝術。審美模仿的對象更加豐富復雜,模仿的技巧也更加高超,真正達到了視通萬里、思接千載的境界。如同弓箭得到了光子火箭的幫助,能瞬間集合人類文明的海量信息,并根據需要進行科學的分析計算。在空間上,可以虛擬出宇宙里的任何星體;在時間上,可以穿越到任何時代。這極大地豐富了電視劇審美模仿的技巧和境界。
大數據可以幫助藝術家進行現實模仿。目前,大數據給中國電視劇審美模仿帶來的最大變革,莫過于運用大數據,為參與這場敘事模仿的接受者建模,然后對劇本創作、審美風格、投資規模、播出渠道等發出一整套指令。這將促使中國電視劇探索新的生產模式,開拓出新的天地。然而,對于審美價值的創造和情感敘事來說,大數據又實是一把雙刃劍,審美模仿是一種受多重因素制約的情感體驗游戲。在機械復制時代,本雅明就明確指出,表演者與市場隔離,“他的全副心靈與精神投入這一市場,而市場是不可捉摸的”,這導致一種“壓抑”或“焦慮”⑨。在大數據時代,則導致另一個極端——市場已經為藝術家所知,他的藝術創造變得毫無懸念。然而,事實上,他的心里卻多了一整套冷漠的數字化指令,時時刻刻在提醒他,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的藝術情感體驗勢必得不到自由釋放。
大數據給當前的中國電視劇帶來的最大“紅利”,是歷史劇。從前需要藝術家窮盡一生才能達到的歷史認知境界,現在只需要短短幾個月甚至幾天便可以實現,《瑯琊榜》《羋月傳》等作品皆出自90后之手,足見大數據的巨大威力。在具體的情景設置和語言對白方面,大數據也能讓編劇有如神助,打通古今界限,制造超常的戲劇性張力。例如,新版的《笑傲江湖》,令狐沖與老頭子第一次喝酒,老頭子關于酒的臺詞,簡直是一部中國悠長的酒文化史詩,散發出奇妙的審美效果。
大數據時代的互聯網精神及其培育的虛擬世界,已經進一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對虛擬世界進行模仿,可謂之虛擬模仿——各種無視經典現實主義積累起來的模仿律的模仿活動,例如無厘頭、戲仿、拼貼、互文游戲、超文本鏈接⑩等。
在虛擬模仿里,模仿的主客體以及接受主體與途經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按照后現代主義文化邏輯,虛擬藝術與日常生活不再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真實再現關系,而是“界限被消解了”,藝術作品也被“符碼混雜的風格”消解了,“贗品、東拼西湊的大雜燴、反諷、戲謔充斥于市,對文化表面的‘無深度’感到歡欣鼓舞;藝術生產者的原創性特征衰微了”,最后,“藝術不過是重復!”(11)
這樣的描述,雖然道出了虛擬模仿的部分特質,但絕不能將之泛化為虛擬模仿的全部。所以,我們首先應該肯定這是人類模仿史的進步,然后再質疑模仿律在變遷中是否有異質的東西介入。況且,藝術模仿是重復,本無可厚非。“一切社會的、生命的和物理的重復,也就是模仿的、遺傳的或振動的模仿(讓我們只考慮最明顯的、最典型的重復形式),都源于某種革新,就像一切光線都是從中心發射出來的一樣”。(12)
虛擬世界依然是由實實在在的人按照網絡精神構筑起來的現實,與虛假或虛幻世界不同。鮑德里亞所批判的“物的零度”和“社會走向零度化的存在”就是一種虛假的幻想,是消費邏輯對自在之物的“綁架”,導致“語言和言說成為現實生活的原件”,而日常生活“倒成了它們的復制品”(13)。
在虛擬模仿里,生活邏輯的作用較微弱,“這樣的模仿可分為兩大類:輕信和順從,即信念的模仿和欲望的模仿”(14)。網絡世界里的個人身份很容易失去,蛻變為“網上幽靈的玩偶,脫離了肉體的束縛”(15),導致虛擬世界充斥著力比多,虛擬模仿也因之備受批判。
去除成見,互聯網精神中的自由、平等、解放元素,給虛擬模仿注入了新鮮血液。
虛擬模仿并非要磨礪我們辨別虛構與真實的能力,而是注重模仿的可逆性與解放性。在現實模仿里,誠如塔爾德所言,“上層階級提出或接受的革新很容易被傳播到下層階級”,永不停息,最后達到趨同,“一切社會的變化和進步都是相互關系取代雙邊關系的結果”(16),也就是說,現實模仿的模仿律是從上到下不可逆的、歷史的。而虛擬模仿的模仿律卻是任意方向的,且可逆的,是現實模仿的完美互補,可以加速實現社會公平。
對于電視劇創作來說,虛擬模仿的積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拓寬了電視劇的題材類型,還創新了模仿方法,貢獻了許多新形式。各類神話題材、玄幻、科幻、穿越題材作品層出不窮,便是明證。如果以一種更寬容的態度歷史地看待電視劇《花千骨》《盜墓筆記》《蜀山戰紀》等,也能從中發現頗多可圈可點的技巧與形式。
在不遠的將來,人類社會生活全面進入大數據時代,中國電視劇無論從生產范式還是審美本體方面,都應該發生新的“劇變”。
注釋:
①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此處的“文本形態”與童慶炳先生著作中的“文體”意義相同,不僅僅指狹義的文學體裁,而是具有更豐富含義,意指“一定的話語秩序”,它能折射出藝術家的“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
② 張國濤:《電視劇本體美學研究——連續性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63頁。
③ 熊文泉:《“紅色經典”藝術生產的內在機理分析——以作品〈林海雪原〉為例》,《當代電影》,2004年第6期。
④ 陳波、張雷:《基于大數據的影視劇制播模式創新》,《電視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李春龍:《大數據時代的顛覆與重建——居于數據分析的電視劇商業價值評估模型》,《電視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張國濤、胡智鋒:《2013年電視劇:收視困境與創新乏力》,《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4年第2期。
⑦ 歐陽友權:《網絡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4頁。
⑧⑨ [德]瓦爾特·本雅明:《技術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胡不適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6頁。
⑩ 超文本:是一種不以單線排列,而是可以按照不同順序來閱讀的文本。見歐陽有權:《網絡文學本體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11)[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12)(14)(16)[法]加布里埃爾·塔爾德:《模仿律》,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2、267頁。
(13)仰海峰:《走向后馬克思主義:從生產之鏡到符號之鏡——早期鮑德里亞思想的文本學解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1頁。
(15)[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山東大學審美文化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
【責任編輯:劉 俊】
*本文系江西省哲社“十二五”(2015年)規劃項目“大數據時代中國電視劇編劇藝術的美學原理與產業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5YS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