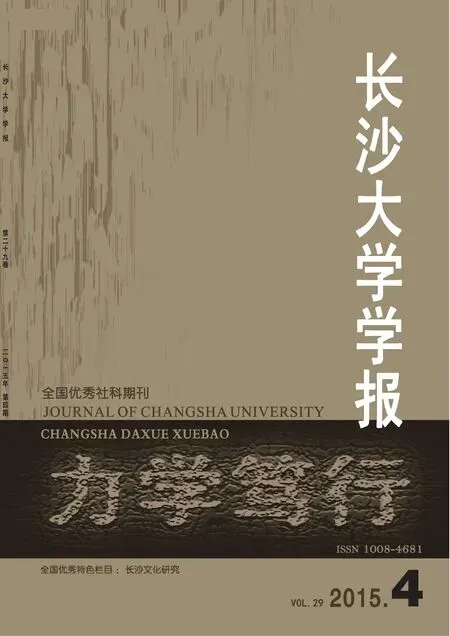操控論視角下《安妮日記》的改寫與翻譯
2015-02-20 15:42:13李蕊
長沙大學學報
2015年4期
李 蕊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 福州 350202)
?
操控論視角下《安妮日記》的改寫與翻譯
李蕊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 福州 350202)
摘要:操控論使翻譯研究超越了翻譯標準和文本對比討論的局限,轉向了對語言因素之外的文化和政治等宏觀因素的關注。以操控論的視角對《安妮日記》進行觀照,可以發現該作的改寫與中譯行為深受社會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這三個方面的影響與制約。
關鍵詞:操控論;改寫;翻譯策略;人物形象

《安妮日記》(TheDiaryofaYoungGirl),是德籍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對自己在1942至1944年間為躲避納粹迫害而藏身密室時的生活和情感的記載。作為一名成長中的13歲少女,與母親不斷發生沖突的困惑以及對性的好奇是她日記內容的重點。同時,日記還記錄了25個月中他們小心藏匿且充滿恐怖的密室生活,真實反映了德軍占領下的人民的苦難生活。戰爭結束之后,奧托·弗蘭克——安妮的父親,決定實現女兒的夙愿,出版這本日記。
但是在出版以及翻譯過程中,該書的不同版本都進行了改寫和刪減。譯者改寫和刪減的原因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因素。何種翻譯模式會被譯者所采納?又怎樣將其模式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之中?本文將從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poetics)、贊助人(patronage)三個方面,即操控論的三要素進行探討,期望可以對翻譯實踐活動帶來一些啟示。
這里論述的“操控論”并不包括圖里(Toury)的描寫學派和埃文-佐哈爾(Evan Zohar)的多元系統學派等,而是指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的操控派,其代表人物有:勒費維爾(Andre Lefevere)、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赫曼斯(Theo Hermans)等。……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