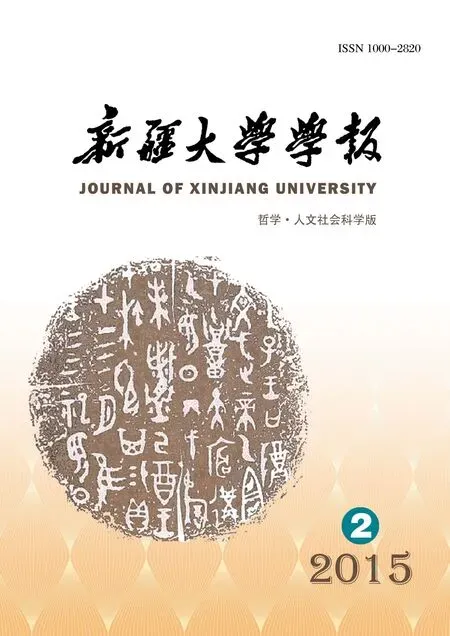敘述背后的故事
——趙毅衡文藝思想述略?
李松睿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評論》雜志社,北京100029)
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發展史上,趙毅衡教授無疑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這位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就鉆研形式主義文論的文藝理論家,幾乎是憑借著一己之力將形式主義文論介紹到中國,改寫了中國文學批評界長期以來由現實主義—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他的一系列學術著作,例如《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等,更是以其理論把握之精到、研究視野之開闊、敘述文筆之酣暢,在學術界產生了持久而廣泛的影響。在20世紀80、90年代,很多學者正是通過趙毅衡的著作才一窺形式主義文論、敘述學的門徑。以至于到了今天,無論文學研究者是否認同形式主義文論將廣闊的現實生活暫且放入括號存而不論的理論前提,形式主義文論處理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都已經成了文學研究者必須掌握的工具。有些研究者甚至還不無偏激地指出,能否在方法論上超越現實主義—反映論,掌握形式主義文論的基本方法,是判斷文學研究者是否合格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趙毅衡的文藝思想已經在中國的文學研究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跡,無論我們是否贊同他的某些學術判斷、學術觀點,其思想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需要人們進行認真的整理。本文就試圖以時間為敘述線索,勾勒趙毅衡文藝思想的發展脈絡,呈現其研究在中國學界所處的獨特地位,并總結其學術研究的基本特色。
一、以形式為中心
趙毅衡1943年出生于廣西桂林。抗戰勝利后隨父母回到上海,并在這座城市接受了小學、中學教育。正像他后來在回憶中提到的,“上海的建筑、城市格局、西方人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等,我印象深刻。實事求是地說,上海文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1]。的確,上海在解放前長期作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它那畸形繁榮的經濟催生了中國最早的現代都市文化,并推動著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的艱難轉型。于是,各式各樣的文化、思想以及價值觀在這座城市相互碰撞、交鋒、融合、新變,熔鑄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品格。而趙毅衡后來的學術風格——以用舶來理論解讀中國作品,利用本土經驗推進理論發展為特色,這無疑與其早年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
1963年,趙毅衡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京大學英文系,并很快成為班上成績最優秀的學生。然而不幸的是,趙毅衡畢業于1968年,正好趕上“文革”高潮,他作為英文專業的優秀畢業生,卻先是分配到農場勞動,后調到徐州市郊的煤礦當礦工,并且一干就是七年。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勤奮好學的趙毅衡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學業,他借著學習《毛澤東選集》的機會,在心里將其中的文章翻譯為英文,為其日后從事外國文論研究并赴美學習做了充足的準備。直到1978年國家恢復碩士研究生招生后,趙毅衡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詩人卞之琳攻讀碩士學位,這才離開了煤礦進入文學研究界。應該說,在農場和煤礦勞動的經歷,是趙毅衡生命歷程中的一段“彎路”,但在這一過程中所接觸的人和事,卻鍛煉了他的性格與心智,讓他能夠擺脫種種人云亦云的套話,對社會和人生有了獨立的看法,為他日后成長為具有鮮明學術風格的學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正像他在回憶那段煤礦生活時所說的:“1978年早春,我從黑咕隆咚的煤窯里爬出來,地面亮得睜不開眼,但也涼得叫人打戰。十年的體力勞動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幾十年來的文學方式和批評方式,所謂反映真相的現實主義,只是淺薄的自欺欺人主義。我貼近生活,貼得很近,我明白沒有原生態的生活,一切取決于意義的組織方式。”[2]
需要指出的是,這段寫于21世紀的回憶或許并不能準確地反映趙毅衡在1978年的心理感受,但它無疑揭示出:趙毅衡和彼時大多數文學研究者一樣,因為經歷了“文革”,開始對長期流行于中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文學和文學批評進行反思。只不過趙毅衡沒有像大多數同代人那樣,在對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心生厭惡之后,立刻就生吞活剝地運用諸如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系統論以及結構主義等一系列西方理論,在這些舶來理論所布下的重重迷宮中逐漸迷失了自我。而趙毅衡雖然同樣否定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但卻沒有匆匆忙忙地棄之如敝履,而是開始思考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得以流行的原因。他認為現實主義文論之所以在中國大行其道,是“中國現代以來的庸俗的經濟—社會關系決定論,與中國本有的文以載道論相結合的后果”,因此文學批評總是“把文學當作‘現實的反映”’[3]。在這種情況下,批評家們更關注所謂“內容”,而忽視了文學的形式。在趙毅衡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亟需補上形式主義文論這一課,擺脫只看內容忽視形式的慣常思維方式。因此他才選擇形式主義文論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顯然,這一選擇絕不是在倉促之際的隨意之舉,而是源自趙毅衡對于中國文學研究界存在的問題的清晰判斷。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這位才華橫溢的研究者會花費數十年的精力來耕耘這一研究領域。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趙毅衡對形式主義文論所做的研究主要是《新批評》和《當說者被說的時候》這兩本專著。今天重新翻開這些著作,人們或許會覺得它們顯得有些簡單,特別是《當說者被說的時候》,似乎不像是一本學術專著,而更像是一部教材。趙毅衡在該書中用簡明流暢的語言、生動有趣的例證,對敘述學中的基本概念,如敘述行為、敘述主體、敘述層次、敘述時間、敘述方位等,進行了系統介紹。我們甚至可以說,只要認真閱讀這部著作,人們就可以掌握對小說進行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我們當然無需指責該書偏于概念介紹,而較少學術創見,因為它本來就是作者于1985年寫博士論文時的讀書筆記。此外,如果我們考慮到在20世紀90年代,很多文學研究者認識到80年代的文學批評流于印象式批評和對作品內容、主題思想的空洞闡發,缺乏對作品形式的細致分析,開始嘗試運用敘述學理論分析作品。但由于中國學界在這一時期缺乏對敘述學理論的詳盡了解,使得“大學生研究生經常犯敘述學錯誤,往往使整篇用功寫的論文失據。甚至專家們堂皇發表的文章,甚至參考書,甚至教科書,也會出現‘想當然’式的粗疏”[4]。那么該書對敘述學基本概念、小說分析基本方法的簡明介紹,正可謂恰逢其時,使中國學界系統地接觸了敘述學理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學批評的面貌,其意義如何強調都不過分。這也就難怪該書問世后很快就行銷一空,在青年學者中間廣泛流傳,甚至出現一書難求的盛況。
與《當說者被說的時候》相比,《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該書在新世紀經過修訂后,更名為《重訪新批評》)更像是一部嚴謹的學術專著。它以新批評派對文學性質的理解、從事文學批評的方法論以及詩歌語言分析方法這三個切入點,對這一文學批評派別的發展過程、思想方法進行了深入而詳盡的介紹。由于國內學者大多是通過美國文藝理論家韋勒克、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了解新批評的,使得人們雖然對新批評派關于文學本質的認識,他們對傳紀研究、心理學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批評,以及他們解讀作品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但對這些觀點形成的背景、這一流派內部的種種分歧等卻不大了然。而趙毅衡對新批評派的研究則沒有局限于對觀點的介紹上,而是深入到這一文學批評流派的內部,努力呈現各種觀點如何在爭論中形成的過程。例如在涉及到“感受謬見”這個新批評派提出的重要命題時,趙毅衡沒有僅僅介紹該命題指的是文學作品對讀者的感染力,并非判斷其水平高下的標準,而是從1941年蘭色姆在《新批評》一書中指責瑞恰茲、艾略特、溫特斯以及燕卜蓀等新批評派中的代表人物進行“感受式批評”入手,呈現這一命題得以提出的復雜背景。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趙毅衡沒有把西方理論視為永恒不變的真理,而是努力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其思想特色進行評說。他認為“反‘感受謬見’說,作為一種權宜性的批評方法,暫時把讀者問題擱起,未嘗不可一試。但在理論上,它卻是站不住腳的”[5],并舉出維姆薩特、比爾茲萊等人在評價具體的文學作品時,不得不借助讀者感受立論的地方。正是在這里,新批評派那頗為偏激的理論預設和精彩的批評實踐之間的裂隙,被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因此《新批評》一書并不僅僅是全面介紹了新批評派的文藝思想,更總結了該派理論家在具體的批評實踐過程中的得失成敗,為中國讀者進一步尋找合適的批評方法提供了借鑒。在這個意義上,該書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學者解讀西方文學理論的經典范例。
二、“形式—文化論”詩學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形式主義文論在分析文學作品時確實充滿了洞見,但其理論預設卻極為偏激。它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個封閉自足的小宇宙,切斷其與作者、讀者以及社會生活之間的一切聯系。因此,形式主義文論雖然對作品內部所蘊涵的張力、悖論以及反諷等因素異常敏感,但卻對廣闊的現實生活視而不見,這使得形式主義文論多少顯得有些狹隘局促。關于這一點,對形式主義文論情有獨鐘的趙毅衡是有著清晰的認識的。他在談到自己的治學經歷時提到:“大約在1985年左右,我從敘述學讀到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學生產的社會—文化機制中,有一條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內容,更具有歷史性。”[6]247也就是說,趙毅衡非常清楚形式主義文論就形式談形式是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同”,但他并不認為擺脫這一困境的方法是重新回到內容,相反,他覺得探究形式得以形成的“社會—文化機制”,是突破形式主義文論自身局限性的有效路徑。正基于這一研究思路,趙毅衡在研究西方文論時以系統介紹形式主義文論知名,但在從事具體的文學研究時則沒有單純地使用形式主義文論的方法,而是有意識地將對作品的形式分析和文化分析結合起來。在筆者看來,最能體現這一研究思路的作品,當屬初版于1994年的《苦惱的敘述者》。
這部學術著作以晚清時期出現的中國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比其與傳統中國小說、五四白話小說之間的區別,分析其敘述形態之特異性的來源。20世紀80、90年代,晚清時期以其中國與西方相互雜糅、傳統與現代犬牙交錯的特質,逐漸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關注,趙毅衡、陳平原、王德威等學者都在這一領域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趙毅衡的《苦惱的敘述者》就是這一時期涌現出的代表性學術著作。有趣的是,《苦惱的敘述者》和陳平原出版于1988年的專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均使用敘述學理論處理晚清小說,將二者進行對比,或許是呈現趙毅衡研究思路之特色的最佳途徑。表面上看,趙毅衡、陳平原在處理晚清小說時,都是從敘述角度、敘述時間以及敘述結構等敘述學理論出發,分析晚清小說在形式上的特殊之處。對敘述問題,或者說形式問題的高度關注,是這兩本著作最有特色的地方。并且由于趙毅衡、陳平原處理晚清小說的方法基本相同,他們在總結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特色時也有不少暗合之處。只不過在陳平原那里,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被貫徹得更為徹底,而超越單純的形式分析則是《苦惱的敘述者》一書最有特色的地方。在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他對1902至1927年間出現的千余種著、譯小說進行抽樣分析,以敘述角度、敘述時間以及敘述結構為參照系進行量化統計,認為“中國小說1902年起開始呈現對傳統小說敘事模式的大幅度背離,辛亥革命后略有停滯倒退趨向,但也沒有完全回到傳統模式;‘五四’前后突飛猛進,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敘事模式的基礎”[7]。而造成這一轉變的原因,在陳平原看來則是“西方小說的啟迪與傳統文學的轉化”[8]這二者的合力。
如果說陳平原主要以敘述學理論為依據對晚清小說進行量化統計,其研究方法基本上沒有超出形式主義文論的窠臼,那么趙毅衡則是以敘述學分析為出發點,進而去思考中國社會思想在晚清時代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苦惱的敘述者》中,趙毅衡沒有把目光局限在晚清小說的形式特征上,而是將文學作品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整個社會的主導性文化機制的表征。這也就是趙毅衡所說的,“小說敘述文本,可以作為文化的窺視孔,可以作為文化結構的譬喻”[6]249。在這個意義上,作品的形式也就成了某種指示器,其種種變異不過反映著中國社會文化在晚清前后經歷的變化。在具體的分析中,趙毅衡雖然同樣分析敘述角度、敘述時間等敘述學問題,但他關注的重點是敘述者的形象問題。他認為在傳統中國小說中,“敘述者享有干預的充分自由,成為敘述中幾乎是壟斷性的主體性來源,牢固地控制著敘述,由此阻止詮釋分散化和意義播散”。到了晚清時代,“敘述者對其權威受到挑戰相當不安,而用過分的干預來維系敘述的控制······有時敘述者干預之多到了嘮叨的地步,不必要地自我辯護其控制方式,顯得杌隉不安”。而在五四白話小說中,敘述者地位開始下降,敘述控制得以全面解體,“使整個敘述文本開始向釋義歧解開放”[6]166?167。在趙毅衡看來,由于傳統中國在文化上從未受到嚴重挑戰,因此傳統小說中的敘述者也就牢牢地控制著作品的意義;而在晚清時代,中國文化的合法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一時期小說作品中的敘述者也就進退失據,顯得極為不安、異常苦惱;到五四時期,中國文化在外來思想的沖擊下,價值越來越趨于多元,使得小說敘述者再也無法控制文本的意義闡釋。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苦惱的敘述者》一書對晚清小說的研究是從形式分析入手的,但其真正關心的對象卻是中國文化在外來文化沖擊下所經歷的種種變化。也就是說,趙毅衡實際上是將小說的形式特征看作是文化結構在小說文本中刻下的一系列印痕,并由此去窺探文化結構自身。這就使得趙毅衡的研究相較于陳平原那部專注于形式分析的著作,獲得了更為宏闊的文化視野。在這個意義上,趙毅衡的研究實際上是聯結小說形式與文化的中介,它一端勾連著小說的形式特征,另一端則與更為廣闊的文化對接。這一獨特的研究思路,被趙毅衡命名為“形式—文化論”。在趙毅衡后來的很多研究論文中,如《無邪的偽善:俗文學的道德悖論》、《重讀〈紅旗歌謠〉:試看“全民合一文化”》以及《從金庸小說找民族共識》等,這種“形式—文化論”研究思路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例如在《無邪的偽善:俗文學的道德悖論》中,趙毅衡就對明清時期戲曲舞臺上折子戲大行其道,而全本演出相對較少的現象進行了精妙的解釋。他沒有像很多古典文學研究者那樣,將這一現象歸結為全本演出耗時過長等純技術性原因,而是力圖從文化角度來解釋作品的演出形式問題。趙毅衡認為以《白兔記》為代表的俗文學內部存在著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張力,諸如靈異、鬧劇等亞文化內容必須包裹在符合主流文化的整體框架中才能得到呈現。在趙毅衡看來,折子戲的演出恰好可以化解這一文本內部的張力,因為“在折子戲中,倫理邏輯被懸置了,被推到一個方便的距離上。這樣,在釋讀文本的意義時,全劇語境既可以被引出作為道德保護,又可以置之不顧以免干擾片段的戲劇興趣”[9]。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趙毅衡的文學研究超越了單純的作品形式分析,進而去討論使文學作品成為可能的文化背景、文化結構。
三、符號學與廣義敘述學
從趙毅衡所使用的“形式—文化論”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他將人類的社會生活看作是某種雙層結構,上面一層是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新聞以及影視等在內的各種敘述文本,而下面一層則是支配前者,并使其成為可能的元敘述(或者用更通俗的說法,那就是文化)。在人類的文化活動中,元敘述提供意義的來源,而上一層的敘事文本則將意義以各種形式敘述出來。趙毅衡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通過對上一層敘事文本的分析與解讀,去窺探下一層元敘事的“秘密”。這就是為什么他要將自己的研究方法稱為“形式—文化論”。只是因為趙毅衡在此時碰巧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因此他才會選擇將文學文本作為通向元敘事的幽謐小徑。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趙毅衡漸漸地不再滿足于將自己處理的研究對象限定在文學上,而是希望去探究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這就是使得他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脫離了原有的形式主義文論、敘述學研究,開始進行符號學和廣義敘述學研究。而由此引發出的問題是,這里的所謂形式主義文論、敘述學以及符號學之間的關系是什么?趙毅衡的研究轉向究竟有何意義?
在一次接受訪談時,趙毅衡談到了形式主義文論、敘述學以及符號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表示:
我把形式文論分為這么幾個大的部分:符號學,屬于這里最抽象的層次;敘述學是符號學運用于敘述,正如語言學是符號學運用于語言,但是語言學學科之獨立龐大歷史久遠,遠遠超過敘述學和符號學,因此很難說語言學是符號學的運用。敘述學本身也太龐大,所以單獨成為一個學科,符號學與敘述學現在就并列了。其它應當屬于形式論范疇的,包括風格學、修辭學,它們都是由符號學總其成的形式論的一部分[10]。
也就是說,趙毅衡認為符號學本來屬于最抽象的層次,敘述學不過是將抽象的符號學原理運用于敘述文本之上而已。但由于敘述學目前已經發展成為有著龐大體系和自身歷史的學科,使得人們很難將敘述學看作是符號學的分支學科。因此他雖然將符號學看作是涵蓋面最大的學科,但迫于學界慣例卻不得不將符號學和敘述學、風格學、修辭學等權宜性的并列在一起,放在形式主義文論之下。
以文學文本,特別是小說為研究對象的敘述學,只能涉及人類表意活動中的一小部分;而研究如何表達意義、解釋意義的符號學,則將人類的全部表意活動納入其研究范圍。因此,當趙毅衡將研究重心轉向符號學時,他實際上是要將人類社會的全部表意活動都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這無疑是一項規模龐大,讓人望而生畏的工作。而趙毅衡最新的兩部專著——《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和《廣義敘述學》——就是這項工作的初步成果。
在2011年的專著《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中,趙毅衡嘗試在綜合國際符號學研究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新世紀以來的文化變遷和中國符號學傳統,重新建立一套符號學體系。不過在筆者看來,趙毅衡花費巨大的心力按照符號的構成、符號的意義表達、符號的傳播、符號的解釋以及符號的修辭等項目,構建起一套表述符號學的完整體系,其意義當然如何強調都不過分。但讀過該書之后,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并不是那套完備的體系,而是趙毅衡在總結西方各派理論家對某一符號學問題的論述后,會運用中國本土的經驗與例證,指出西方理論家論述的不足,并進一步推進對該問題的探討。這才是趙毅衡的這部著作中最令人欽佩的地方。例如在《符號學》上編第九章第十節談到符號學修辭的四種主要類別——隱喻、提喻、轉喻以及反諷的演進時,趙毅衡先是引證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格雷馬斯等人關于上述四種類型相互之間是否定關系的論述,接下來,他又依次引用了維柯、諾瑟羅普·弗萊以及卡爾·曼海姆關于四種類型在歷史過程中依次演化的觀點。再次,他還進一步介紹了皮亞杰、E·P·湯普森以及海登·懷特等人如何在心理學、歷史學等領域運用符號學修辭四體演進的理論。最后,趙毅衡又用中國傳統小說以及宋代易學家邵雍的論述,證明四體演進理論對于中國本土文化來說同樣適用。行文至此,趙毅衡已經向讀者展示了自己的博學和寬闊的理論視野。但他對此還并不滿足,而是進一步對四體演進理論提出質疑,即“四體演進說沒有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反諷之后,下一步是什么?”[11]221在趙毅衡看來,中國文學史上發生的一系列文體變遷表明,當文學發展到反諷時,并不像保羅·德曼所言,意味著“文化表意無法進行下去”[11]221。恰恰相反,文化總是會在一種表意方式終結后,重新發現新的表意方式,“重新構成一個從隱喻到反諷的漫長演進”[11]221,就像古典小說讓位給白話小說、現代小說讓位給影視作品一樣。正是在這里,趙毅衡沒有像很多中國學者那樣視西方理論家的論述為普遍真理,而是敢于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并進一步推進對問題的討論。在筆者看來,這部著作最重要的學術價值或許正體現在這些地方。
如果說趙毅衡的《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主要在抽象的層面上探討了意義的傳播、釋讀等問題,那么他于2013年出版的新作《廣義敘述學》則主要探究意義如何通過人類具體的敘述活動表達出來。與傳統的敘述學相比,所謂廣義敘述學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再把研究對象限定為文學敘述,而是試圖為包括文學、歷史、傳記、新聞以及影視作品在內的人類全部敘述行為尋找規律。需要指出的是,創建這樣一種包羅萬象的廣義敘述學絕不是什么異想天開或頭腦發熱的舉動,而是近幾十年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內在要求。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乃至醫學都出現了所謂“敘述轉向”,敘述成為這些學科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界迫切希望能有一門能夠討論所有敘述體裁的共同規律的學科,而趙毅衡試圖創建的廣義敘述學正順應了這一要求。在筆者看來,或許《廣義敘述學》最大的貢獻,在于它創造了一種覆蓋所有敘述體裁的分類方法。趙毅衡在書中按照橫縱兩條軸線展開對所有敘述體裁的全域分類方案。一條軸線是按照敘述體裁的“本體地位”,分為紀實型體裁和虛構型體裁;另一條軸線則是按照所謂“時間—媒介”分類,分為過去時的記錄類敘述、過去現在時的記錄演示類敘述、現在時的演示類敘述等等[12]。于是,人類社會的所有敘述行為都可以在這一分類方案中找到相應的位置,為進一步探討敘述行為的規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遺憾的是,《廣義敘述學》一書在討論具體的敘述問題——如敘述者、敘述時間、情節以及敘述分層等時,似乎與傳統的小說敘述學并沒有本質性的差別。廣義敘述學還沒有找到真正超越傳統敘述學的路徑。在這個意義上,趙毅衡試圖總結人類社會全部表意活動之規律的努力,還只是剛剛開始。
四、結語
通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趙毅衡最關心的問題是意義究竟如何得到表達的,因此他始終在探究各種各樣的敘述背后的故事。只不過在20世紀80、90年代,他主要研究文學敘述,而到了新世紀,他開始關注人類生活的全部表意活動。在長達三十余年的研究工作中,趙毅衡的文藝思想表現出以下三個特點。首先,他從不隨意選擇研究對象,每一項研究都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研究形式主義文論,是為了扭轉中國文學研究界重內容而輕形式的弊病;在新世紀研究廣義敘述學,則是考慮到人文社會科學界急需一種涵蓋各類敘述的學科。這就使得趙毅衡的學術研究總是能解決一些真正的問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趙毅衡以研究西方文學理論知名,但他的研究卻具有鮮明的中國主體性,他總是用中國本土的經驗與例證,指出西方理論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推演出新的理論表述。因此閱讀趙毅衡的著作,我們總能在里面覺察到作者對自己研究工作的自信,這在長期奉西方理論為圭臬的中國學界中非常少見。最后,雖然趙毅衡博學多才、興趣廣泛,但他的研究卻有著一條貫穿性的主線,那就是以對文學形式的關注為核心,并進而生發出對人類整體表意活動的探究與思考。他的研究在學界產生那么深遠的影響,無疑與他能夠對某一學術問題進行長期思考有著密切聯系。直到今天,趙毅衡仍然在思考著人類表意活動的基本規律,并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和《廣義敘述學》中做出了初步探索,為國際符號學界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