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超文本敘事理念的源起?
李森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江蘇南京210013)
在網(wǎng)絡(luò)媒介時(shí)代印刷書籍并不會(huì)消失,但是“數(shù)字媒體給了我們一個(gè)上千年中難得的機(jī)會(huì):以新眼光看待印刷文學(xué),并思考我們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和理論有多大程度上是以印刷媒介為前提的。如同我們研究的電子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理論,就可以更新對印刷文學(xué)特性的評(píng)價(jià)”[1]。時(shí)至今日,技術(shù)層面上,文字的電子化運(yùn)用已經(jīng)比較成熟,除個(gè)人電腦以外,電子書閱讀器,手機(jī)等便攜電子設(shè)備也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現(xiàn)代人的生活。
相對紙媒而言,電子屏幕所顯示的內(nèi)容是即時(shí)性的、可變的,而紙媒上的內(nèi)容,尤其印刷文本,變動(dòng)起來十分麻煩。由于電子屏幕的這種可變性,使得一種非線性、互動(dòng)性和跨媒介的敘事方式變得容易而觸手可及。而這種敘事方式并非僅由技術(shù)層面來決定,雖然超文本技術(shù)的實(shí)際運(yùn)用出現(xiàn)得較晚,然而超文本的理念卻很早就產(chǎn)生了。超文本敘事的誕生與三種理念密切相關(guān):技術(shù)層面的超文本、哲學(xué)及文學(xué)理論層面的超文本,以及小說家在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的超文本理念,超文本的文學(xué)敘事便是在這三種理念的影響下出現(xiàn)的。
一、超文本技術(shù)的誕生
《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超文本,也稱作超鏈接,用于鏈接由電子連接的信息單元,目的是為了使用者更容易的運(yùn)用它們。超文本允許電子媒介上電腦程序的使用者選擇文本中的某個(gè)詞,以獲得和該詞相關(guān)的額外信息······超文本鏈接常常使用不同的字體和顏色的高亮詞匯和語段來標(biāo)示。超文本鏈接也可以把文本與聲音、圖片,動(dòng)畫鏈接起來。”[2]在筆者看來超文本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鏈接,其他特征都是附屬性的。以不同方式鏈接文字就是純文字超文本;鏈接非文字媒體(如圖像)的超文本,即超媒體(hypermedia);而被熱議的互動(dòng)性更是超文本鏈接的特性之一,如果鏈接不是互動(dòng)性的那么鏈接也就不存在了。其實(shí)傳統(tǒng)的書籍也具有互動(dòng)性,讀者必須翻動(dòng)書頁否則內(nèi)容便無法呈現(xiàn),只不過這種互動(dòng)只有一種線性模式。所以,如果鏈接是超文本的核心,那么其自由鏈接的非線性特質(zhì)就為敘事提供了新式的界面和可能。
首先,技術(shù)層面的超文本觀念最早來自德國數(shù)學(xué)家F·克萊恩(F Klein)于1704年提出的“超空間”(hyperspace)概念。克萊恩用這個(gè)詞去定義一種非歐幾何的多維幾何學(xué)特殊類型。時(shí)隔200余年,1965年電腦科學(xué)家泰德納爾遜(Ted Nelson)首次提出了“文學(xué)機(jī)器”概念[3],他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計(jì)算機(jī)創(chuàng)造和運(yùn)用文本網(wǎng)絡(luò)的可能。他認(rèn)為“文學(xué)可以是一種進(jìn)行中的互聯(lián)文本系統(tǒng)(system of interconnecting documents)”[4]。因?yàn)槌谋揪褪恰耙环N完全非線性書寫的電子形式······這意味著一種多線性和多序列的詞語網(wǎng)絡(luò),允許讀者鏈接到更多的信息資源。通過其交互性,讀者能夠在文本鏈接間跳躍,甚至建立他自己的鏈接”[5]。實(shí)際上,這些觀念的出現(xiàn)并不依賴于硬件,且都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意義上的電腦之前,但納爾遜相信可通過機(jī)器生產(chǎn)出一種新的寫作技術(shù)。甚至在納爾遜之前,身為工程師和科學(xué)家的維納沃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也設(shè)想了一種作為超文本讀寫系統(tǒng)的電子技術(shù)[6]。在實(shí)踐性的超文本軟件系統(tǒng)被發(fā)明以前,布什和納爾遜就已經(jīng)確定了超文本的關(guān)鍵性特征,“一個(gè)超文本包括主題和主題間的鏈接,這些主題可以是段落,句子,單詞,或者數(shù)字化的圖像和視頻剪輯。超文本就如同被作者用剪刀裁剪為方便語段大小的印刷書籍。不同之處是電子超文本并不是簡單的一堆無序的堆砌,因?yàn)樽髡哂秒娮渔溄佣x了文本碎片間的關(guān)系”[7]。納爾遜將“超文本”定義為“非連續(xù)記錄,即分支的、允許讀者選擇的、便于在交互屏幕上閱讀的文本······是通過鏈接而關(guān)聯(lián)起來的文本塊,那些鏈接為讀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徑”[8]。
遺憾的是布什與納爾遜都沒有能編程出投入實(shí)際使用的計(jì)算機(jī)超文本系統(tǒng),但他們的理念早已滲入到現(xiàn)代計(jì)算機(jī)運(yùn)用之中。納爾遜構(gòu)想的“上都(Xanadu)”系統(tǒng)和布什的“麥麥克斯存儲(chǔ)器”最初都是針對文件管理或者資料的存儲(chǔ)查詢,也就是說終究都是工具性的。“使用者可以用此裝置······將所有資訊,例如:書籍、照片、筆記、信件等,這些資訊可以加注釋、一頁頁或是一次跳多頁瀏覽,重要的是,使用者可以以一種‘關(guān)聯(lián)法’快速、便利地檢索這些資訊,這種相互關(guān)聯(lián)法就是依人的思維聯(lián)想跳躍法結(jié)構(gòu)的。”[9]傳統(tǒng)的文本以線性方式表達(dá)信息或組織數(shù)據(jù),其缺點(diǎn)在于無法對應(yīng)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信息系統(tǒng),與人的聯(lián)想思維有很大差異。超文本是全新的文字處理形式,創(chuàng)立之初它的意義就在于有效的組織信息,使得人們可以更加方便和自然地獲取、修改、組織、傳播和共享信息資源,使計(jì)算機(jī)更有效地迎合人類的思維方式。在這種工具性思維的主導(dǎo)下以萬維網(wǎng)(World Wide Web)為代表的互聯(lián)網(wǎng)運(yùn)用已經(jīng)將超文本現(xiàn)實(shí)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
日常的計(jì)算機(jī)運(yùn)用中,超文本鏈接帶有強(qiáng)烈的目的性,不論是查詢還是娛樂都是以讀者的主觀目的為主導(dǎo)。超文本在技術(shù)層面上的鏈接運(yùn)用迎合了人們對信息的個(gè)性化需求,但也使得個(gè)人在信息獲取時(shí)的目的性更加彰顯。某種意義上,這種觀念與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有重合之處,盡管讀者有自由選擇情節(jié)發(fā)展或跑題的可能,但最終仍然指向事件的終結(jié),使讀者感到閱讀故事的愉悅和滿足。即便“敘事數(shù)據(jù)庫”中還有剩余的信息,但如果讀者已經(jīng)滿足了自己對作品的“文體期待”就可以停止下來。如同在網(wǎng)絡(luò)上進(jìn)行資料搜索時(shí),已經(jīng)得到足夠的信息,便可以停止了。實(shí)際上,閱讀模式有很多種,追求情節(jié)發(fā)展結(jié)構(gòu)的目的性閱讀只是其中一種。有的作品會(huì)吸引讀著更加關(guān)注人物的性格和命運(yùn),并對人物產(chǎn)生情感反應(yīng)。閱讀小說與查詢資料不同,因?yàn)閿⑹碌目旄胁⒉煌耆珌碓从诠适聫拈_端到結(jié)尾的情節(jié)發(fā)展。
二、作為理念的超文本
對于早期哲學(xué)家與文學(xué)理論家們來講,雖然不知道超文本技術(shù)的存在,但卻明確提出了各自對敘述傳統(tǒng)的異議。如維特根斯坦提出:
我們的目光掃過印刷行時(shí)的方式同掃過一系列隨意的勾勾彎彎和裝飾花樣時(shí)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人們會(huì)說,目光的移動(dòng)特別輕松自如,既無停頓,也不打滑。而同時(shí),在想象中進(jìn)行著不由自主的言語。在我讀德語和其他語言用各種字體印刷或書寫的東西時(shí)情況便是這樣——但在所有這一切中對于讀本身來說根本的東西是什么呢?并沒有一個(gè)在一切讀的實(shí)例中都出現(xiàn)的特征[10]。
維特根斯坦強(qiáng)調(diào)各種閱讀并沒有一種共同的本質(zhì),各種閱讀表現(xiàn)為異質(zhì)性存在,不同語言、不同印刷、不同閱讀方式等等都可以導(dǎo)致不同的閱讀經(jīng)驗(yàn),因此閱讀并不存在什么整齊劃一的標(biāo)準(zhǔn)。對于敘事來講,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統(tǒng)一的線性標(biāo)準(zhǔn),時(shí)間、因果等不過是各種聯(lián)系中的一種。在當(dāng)代理論家中,這種觀念繼續(xù)發(fā)展,“像巴特和福柯關(guān)于作者之死的論述,德里達(dá)的文本性,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等等,這種融合了創(chuàng)新與非中心的模式很容易地發(fā)生在超文本上。”[11]此外,利奧塔的“小敘事”,德勒茲和瓜塔利的“塊莖”與“平原”,本雅明和阿多諾的“星叢(constellation)”概念等等對應(yīng)在敘事中都講述著相似的觀念。“德里達(dá)在《語法學(xué)》中指出,裂痕已經(jīng)正在小說的‘身體’上積累裂痕,因?yàn)樗鼉?nèi)在的線性正被懷疑。同樣,另一位哲學(xué)家利奧塔,這樣描述他理想中的書:‘一本好書······應(yīng)該······讀者可以從任意一頁,以任意順序閱讀。”’[12]盡管這些理論家的學(xué)術(shù)背景千差萬別,但他們概念的相通之處是對“中心”和“線性”的反叛,強(qiáng)調(diào)每個(gè)個(gè)體、片段獨(dú)立存在的價(jià)值。敘事受這些后現(xiàn)代與解構(gòu)觀念的影響也產(chǎn)生了非線性的渴望。
上述理論家哲學(xué)著作寫作形式的先鋒性可以和紙媒上印刷的擬超文本小說相媲美,如德勒茲和瓜塔利的《千平原》,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文之悅》、《S/Z》,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美學(xué)理論》等等,在寫作形式上都是當(dāng)代理論著作中的“酷兒”。他們嘗試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片段性寫作,用一種開放的、流動(dòng)的、無定向性的言語方式進(jìn)行理論言說,將其哲學(xué)理念與行文方法融為一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多諾的“文本重構(gòu)法”。他在第一稿《否定辯證法》完成后又將本來章節(jié)明晰的文本打亂為“碎屑狀”,文字不分章節(jié)且沒有段落(德文原版),再裝訂起來。文本完全拒斥被從某種同一性思路解讀,故意在文本形式上制造障礙。阿多諾說自己著作的“第一稿總是一種有組織的自我欺騙之作;在第二稿中,我自己潛入其中,對自己的作品進(jìn)行了批判”[13]。他不再以邏輯條理組織材料,而把它們打碎混合,這種“各部分、各種理論觀點(diǎn)‘具有相同的分量’的文本,也就是阿多諾制造出來的理想化理論星叢和文本蒙太奇”[14]。在對文本形式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中,讀者的主體性被調(diào)動(dòng)起來,文本也從“固體”變成“流體”。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敘事似乎要放棄線性,使每個(gè)成分都顯示出獨(dú)立價(jià)值,“開端—高潮—結(jié)尾”這樣的敘事“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被看作故事的尸體或假面,真正的敘事應(yīng)該是動(dòng)態(tài)的,直面讀者的,每個(gè)部分都應(yīng)具有平等的意義。敘事的超文本理念正是這種“星叢化”理論的背景中誕生的。
與哲學(xué)家相比,敘事學(xué)家腳步慢了半拍。如熱奈特的“超文性(hypertextualit′e)”是指:“通過簡單轉(zhuǎn)換(后文簡稱轉(zhuǎn)換)或間接轉(zhuǎn)換(后文稱為模仿)把一篇文本從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來。”[15]這明顯是從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派生而來,用以強(qiáng)調(diào)不同文本間的關(guān)系。而熱奈特的例證也說明他的“超文本性”,與電腦專家們的“超文本”概念有明顯差別:
《愛涅阿斯紀(jì)》和《尤利西斯》大概是同一藍(lán)本《奧德賽》的兩個(gè)程度不同、書名各異的超文本了······從《奧德賽》到尤利西斯的改造可以描述為一種“簡單”改造或“直接”改造,即把《奧德賽》的情節(jié)搬到20世紀(jì)的都柏林。從《奧德賽》到《愛涅阿斯紀(jì)》的改造則更復(fù)雜、更間接,盡管表面上似乎更接近一些······維吉爾······完全敘述了另一個(gè)故事,但是借鑒了前者,以便創(chuàng)作一部與荷馬在《奧德賽》中所確立的類型相同的作品······即摹仿了荷馬[16]。
同時(shí),巴赫金也常常被用來引證為超文本觀念的先驅(qū)。但正如托多羅夫所說:“巴赫金研究的······超文性······不再具有形式主義研究‘方法’的外殼,而是屬于文化史的范疇。”[17]因?yàn)椤皩υ挕迸c“狂歡”不過是對某種效果的討論,本身并不是文本的形式特征。巴赫金認(rèn)為“文本只是在與其他文本(語境)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諸文本間的這個(gè)接觸點(diǎn)上······該文本進(jìn)入對話中”[18]。而這與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可謂異曲同工。盡管這些詞匯(如:互文性、對話、狂歡······)在超文本文學(xué)的研究中常常出現(xiàn),但其所指與它們本身的意義已有明顯脫節(jié)。這些概念所針對的仍然是傳統(tǒng)文學(xué),它們大多數(shù)要求讀者以新的視角看待文本,使文本獲得一種精神價(jià)值。它們并不涉及電子媒介中的超文本,甚至也不涉及紙媒超文本,僅僅是對文學(xué)精神的闡述,而非文學(xué)形式的說明。這樣,(哲學(xué)背景較少的)文學(xué)理論家還遠(yuǎn)未達(dá)到哲學(xué)家們的境界,他們并沒有對某篇小說中的終極線性產(chǎn)生質(zhì)疑,而是強(qiáng)調(diào)文本間的相互指涉,盡管有文學(xué)史、文化史的意義,但在超文本理念上實(shí)無先見,雖論者甚多但與文本媒介空間的聯(lián)系較小。
三、文學(xué)虛構(gòu)中的超文本
小說家從作品中反映出的超文本觀念與前兩者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差別。如卡爾維諾所說:“文學(xué)生存的條件,就是提出宏偉的目標(biāo),甚至是超出一切可能的不能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只有當(dāng)詩人與作家提出別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務(wù)時(shí),文學(xué)才能繼續(xù)發(fā)揮它的作用······文學(xué)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便是能否把各種知識(shí)與規(guī)則網(wǎng)絡(luò)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樣而復(fù)雜的面貌。”[19]文學(xué)家們則把這種構(gòu)想在小說中直接以虛構(gòu)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其中最著名的要屬博爾赫斯的“迷宮”系列中所提到的各種書:
那本書叫“沙之書”,因?yàn)槟潜緯裆骋粯樱瑹o始無終······這本書的頁碼是無窮盡的。沒有首頁,也沒有末頁······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無限的書燒起來也無休無止,使整個(gè)地球?yàn)鯚熣螝鈁20]465。
人們猜測某個(gè)六角形里的某個(gè)書架上肯定有一本書是所有書籍的總和:有一個(gè)圖書館員翻閱過,說它簡直像神道[20]121。
在什么情況下一部書才能成為無限。我認(rèn)為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循環(huán)不已、周而復(fù)始。書的最后一頁要和第一頁雷同,才有可能沒完沒了地連續(xù)下去······小徑分岔的花園就是那部雜亂無章的小說······[20]130。
我認(rèn)為神只應(yīng)講一個(gè)詞,而這個(gè)詞應(yīng)兼容并包······這個(gè)詞等于一種語言和語言包含的一切,人們狂妄而又貧乏的詞,諸如整體、世界、宇宙等等都是這個(gè)詞的影子或表象[20]273。
以上四部小說中都出現(xiàn)了對神奇書籍或文本的描寫,其中的非線性與前文提及電腦技術(shù)專家的超文本如出一轍,而其內(nèi)容龐雜、求全責(zé)備則是獨(dú)特之處。“現(xiàn)代小說是一種百科全書,一種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種事體、人物和事務(wù)之間的一種關(guān)系網(wǎng)。”[21]如果想達(dá)到這樣的目的恐怕就只能靠一本虛構(gòu)的包羅萬象且形式奇特的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了,可不論是博爾赫斯還是其他文學(xué)家都無法做到。在這個(gè)意義上,“博爾赫斯的文學(xué)才能已經(jīng)枯竭了,因?yàn)閷τ谝粋€(gè)故事和結(jié)局總有一個(gè)確定性的結(jié)尾。去恢復(fù)文學(xué)的活力,應(yīng)該進(jìn)行多樣性地寫作,這包括各種可能性,而不是將它們封閉。博爾赫斯可以想象那樣一種小說,但是他無法寫出來······博爾赫斯自己從未接觸過電子空間,那里文本可以包含分叉,匯聚和平行的的網(wǎng)絡(luò)”[7]147。這種對書籍(紙媒敘事)有限性的超越也表現(xiàn)為對神秘事物的描寫,如博爾赫斯對神秘的“阿萊夫”小球的描寫:“阿萊夫的直徑大約為兩三公分,但宇宙空間都包羅其中,體積沒有按比例縮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說鏡子玻璃)都是無窮的事物,因?yàn)槲覐挠钪娴娜魏谓嵌榷记宄乜吹健盵20]306。另外,其他一些作家,如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翁伯托·艾柯的《玫瑰之名》、伊塔洛·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等作品中也都充滿了迷宮結(jié)構(gòu)①參見朱桃香《敘事理論視野中的迷宮文本研究》,廣州暨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9年。。總之,這些文本都試圖達(dá)到一種超文本效果,跨越文本中時(shí)間與空間的限定,將可能的敘事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gè)包括所有可能的故事,它們代表著一種文學(xué)家敘事理念的未來指向。
當(dāng)然也有些作者根據(jù)紙質(zhì)媒介有限的可塑性,創(chuàng)作出一些紙媒超文本小說。這些作品極具實(shí)驗(yàn)性,如法國作家馬克·薩波塔1962年出版的《第一號(hào)創(chuàng)作》就被稱為“撲克牌小說”或“讀不完的小說”。因?yàn)橛∷⒊龅男≌f沒有標(biāo)注頁碼,且都為單面印刷與撲克牌很像,閱讀之前讀者可以將未裝訂的書頁任意“洗牌”,這種排列組合可達(dá)10的263次方。根據(jù)“洗牌”后所得頁碼順序的不同,導(dǎo)致我們的閱讀有時(shí)將男主人公理解為“一個(gè)市井無賴······是一個(gè)盜竊犯和強(qiáng)奸犯;有時(shí)他又是法國抵抗運(yùn)動(dòng)的外圍成員······有時(shí)他簡直就是一個(g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英雄······因?yàn)椋虑榘l(fā)生的客觀環(huán)境的先后秩序不一樣,導(dǎo)致失誤或悲或喜的結(jié)局就會(huì)有異”[22]。此外,胡利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以及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等雖沒有《第一號(hào)創(chuàng)作》在形式上這般激進(jìn),但都具有情節(jié)上的多向選擇性。他們似乎都實(shí)踐著博爾赫斯的文學(xué)理想,產(chǎn)生一本讀不完的書,讓有限的文字無限的循環(huán)。文學(xué)在現(xiàn)代意義上有一種野心或霸權(quán),想用語言包容所有的可能性。哲學(xué)家維特根斯坦“語言是我世界的界限”和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園”的著名論述,似乎與文學(xué)家的理想如出一轍,但事實(shí)上語言包含一種廣泛性的同時(shí)又意味著一種范疇邊界。文學(xué)家所想象的無限敘事,是某種語言權(quán)力的膨脹,是與線性敘事相似的文本霸權(quán)的體現(xiàn)。
四、差異中的超文本敘事
我們可以把三種超文本目的觀與敘事直接聯(lián)系起來:納爾遜提出的根據(jù)某種目的進(jìn)行的鏈接閱讀,可以理解為對目的性情節(jié)的關(guān)注;哲學(xué)家們的后現(xiàn)代文本觀可以看作敘事以形式手段反映的在思想層面上的追求;而小說家們對超文本“百科全書式”的野心則是對具體內(nèi)容的要求。很明顯它們之間存在目的性差異,想要把三種目的都統(tǒng)一起來是極其困難的。
現(xiàn)代計(jì)算機(jī)的超文本技術(shù)運(yùn)用集中在如何讓使用者在短時(shí)間獲得最豐富、最相關(guān)的信息,以克服超文本的無限鏈接給使用者帶來的信息冗余。目前的“云技術(shù)”“云運(yùn)用”就是計(jì)算機(jī)超文本技術(shù)方面發(fā)展的最新階段。而哲學(xué)家則對超文本提出了“星叢化”的要求,各個(gè)單位都具有獨(dú)立價(jià)值和意義,而不依賴于某種總體模式。對應(yīng)到超文本敘事中,就要求超文本每個(gè)節(jié)點(diǎn)的內(nèi)容都具有獨(dú)立的意義闡釋價(jià)值,形式上近似套盒式小說,如《一千零一夜》、《十日談》等等,而這些傳統(tǒng)的套盒式敘事需要統(tǒng)攝在某個(gè)主題下完成(如大家圍坐講故事),這是后現(xiàn)代理論家難以接受的。小說家則與哲學(xué)家表現(xiàn)出完全相反的理念訴求,他們希望用某種結(jié)構(gòu)(如循環(huán))把將敘事變成一種沒有終點(diǎn)的線性延續(xù)。這種延續(xù)是環(huán)狀,而非網(wǎng)狀。因?yàn)橐话銇碚f,文學(xué)家所面對的紙質(zhì)書寫是無法像數(shù)字媒介那樣提供超文本鏈接的。敘事線性的無限延續(xù)與內(nèi)容的無限增殖,表現(xiàn)出某些現(xiàn)代小說家在面對文字?jǐn)⑹滤ノr(shí)狂妄的留戀。
由此,三種超文本理念是存在差異的,如此繁復(fù)的理念關(guān)系如何與敘事結(jié)合起來就成了問題。可以說在具體運(yùn)用中,哲學(xué)家和文學(xué)家的理念占了上風(fēng),似乎這些超文本作家在新媒體上就是要表現(xiàn)出與舊媒體的差異。一些小篇幅的超文本敘事近似于簡單的文本游戲,而篇幅較大的超文本敘事又讓人在鏈接的海洋中無所依憑。相反,超文本的非文學(xué)運(yùn)用已經(jīng)成為信息時(shí)代每個(gè)人的生活方式,在網(wǎng)絡(luò)上看新聞、查資料等,無不感到超文本鏈接的便利。在超文本媒介的背景下,文學(xué)敘事與日常語言的背離所喚起的究竟是那種“使石頭成為石頭”的藝術(shù)審美,還是對文字進(jìn)行的購物狂般的透支消費(fèi)?原來在紙媒上無法完成的想象中的敘事形式,就是超文本敘事的現(xiàn)實(shí),當(dāng)理念可以成為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候真的是一種進(jìn)步嗎。如博爾赫斯作品中那些神奇的書一樣,如果這些書就呈現(xiàn)在博爾赫斯眼前時(shí),他還會(huì)有那么大的興趣去描述它們嗎?或者如伊瑟爾所說:“可能的事情往往是令人不安的,但它同時(shí)表明任何渴望的確定性都是虛幻的替代品。由于隱含著無窮無盡的游戲變化基本是無憑無據(jù)的,所以,當(dāng)構(gòu)成游戲的差異性阻止了所有消除這種差異的努力時(shí),‘文本的快樂’就允許閱讀主體滑向其自身的無根據(jù)性······因?yàn)檫@種狀態(tài)吞沒其既不能使之遠(yuǎn)去也不能使之關(guān)聯(lián)的自身,所以它是令人愉悅的,因此,它使閱讀主體得以沉浸在‘文本主體’之中。”[23]
從文體上看,超文本是否適合用來敘事一直有爭議。按盧卡奇的說法,每個(gè)時(shí)代有每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樣式:口傳時(shí)代的史詩,手寫時(shí)代的羅曼司,以及印刷時(shí)代的小說。蘭道(Landow)就認(rèn)為信息時(shí)代的超文本似乎更加適合詩歌。
超文本更應(yīng)該是詩性的形式而不是敘事性的形式······超文本生產(chǎn)——在敘事句法的層次上——以與詩歌生產(chǎn)的話語(phrastic)層次已十分相似。換句話說,重構(gòu)敘事的方式導(dǎo)致一種與詞序、日常使用等分離的詩性的陌生化······簡單來說,超文本的鏈接把文本與類比、隱喻及其它思考的效果聯(lián)系起來,即詩歌與詩性思維的聯(lián)系[24]。
而另一位超文本大師博爾特則說:“文字文化仍然認(rèn)為小說是屬于印刷空間的······但(一些作家)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創(chuàng)造了一批有重要意義的(數(shù)字?jǐn)⑹拢┳髌贰J聦?shí)上,超文本小說已經(jīng)成為超文本觀念最有信服力的表現(xiàn)方式。”[7]121從創(chuàng)作實(shí)踐來看,超文本文學(xué)中詩歌新作、佳作頗多,但敘事作品相對較少,自1990年第一部超文本小說邁克爾·喬伊斯的《勝利花園》出版以后,文字性敘事的超文本作品在創(chuàng)作量上始終低調(diào),以至于以超文本寫作軟件鼻祖著稱的東門(Eastgate)公司的網(wǎng)站目前也只有28部較正式和嚴(yán)肅的超文本小說提供出售。當(dāng)然其它軟件如Netscape Composer、Microsoft Frontpage也可以進(jìn)行超文本創(chuàng)作,但總體上超文本敘事作品并非某些學(xué)者所估計(jì)的那樣花團(tuán)錦簇。原因在于超文本敘事理念與超文本技術(shù)理念的差異,對超文本工具的文學(xué)化使用本身就是對這種工具的“誤用”,對于結(jié)構(gòu)相對松散的詩歌來說與超文本的特性比較契合,而且詩作一般文字較少,保持了對其整體認(rèn)知的可能。而敘事則不同,它自身的線性顯得與超文本的鏈接方式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就是超文本敘事所要求的讀寫方式的革命性變化,使得故事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都成了一場“艱辛”的旅程。
或許“在得到了技術(shù)支持的敘事中進(jìn)行的各種各樣的實(shí)驗(yàn),美妙而大有前途,但卻沒有給經(jīng)久不變的敘事結(jié)構(gòu)帶來一場革命,甚至微小的變化。敘事將繼續(xù)是敘事,所以······敘事的未來就是敘事的過去”[25]。似乎敘事在這個(gè)時(shí)代根本沒有發(fā)生實(shí)質(zhì)性變化,但“藝由人作······一臺(tái)計(jì)算機(jī)的作用雖遠(yuǎn)遠(yuǎn)無法取代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行為,而后者當(dāng)從排列組合的牢籠中解放出來,抓住這個(gè)集中反駁計(jì)算機(jī)輔助文學(xué)趨勢的天賜良機(jī)。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文本藝術(shù)”[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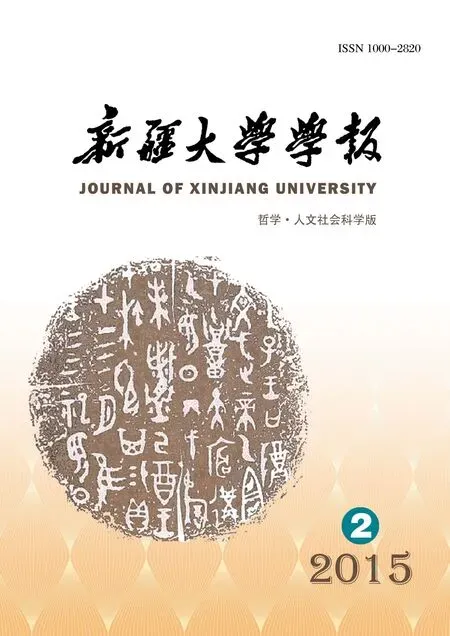 新疆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年2期
新疆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年2期
- 新疆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全國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新疆阿克蘇地區(qū)新和縣通古斯巴西古城遺址
- 通古斯巴西古城遺址前期保護(hù)研究?
- 庭審話語目的語用距離關(guān)系分析?
- 新疆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雙語師資隊(duì)伍建設(shè)現(xiàn)狀調(diào)查研究
——以喀什地區(qū)為例? - 國內(nèi)維吾爾語言研究現(xiàn)狀
——基于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立項(xiàng)的統(tǒng)計(jì)分析? - 國際環(huán)境下構(gòu)建新疆形象的新聞話語方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