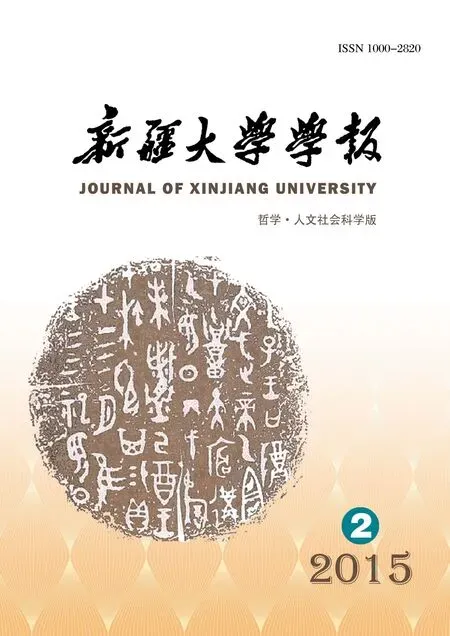從小說《新結婚時代》看新世紀都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沖突及根源?
祝嘉琳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當下中國,城鄉二元模式逐漸被打破,帶來的雙向流動日益增多,然而文化的發展與經濟政治的變遷不一定同步。鄉村文化遭遇了都市文化之后會面臨哪些沖突?都市人在生活方式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后,觀念和情感上也正歷經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轉型,在轉型中又會經歷哪些沖突?王海鸰“婚戀三部曲”之一的《新結婚時代》通過敘寫三組“錯位婚戀”,對這一問題給出了自己的思考:“兩代人,三組錯位的個性婚戀······王海鸰將普通中國人的婚姻生活現狀及在當下社會生活激蕩下的矛盾和疼痛表現得淋漓盡致”[1]2。
一、都市倫理和鄉村道德的沖突
小說的主線是靠著發奮讀書飛躍農門的農村男孩何建國和家境優越的北京女孩顧小西的婚姻生活,通過這對窮富戀,展示了都市倫理和鄉村道德的沖突。
在婚姻倫理上,農村遵循的是“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侍宗廟,下以繼后世”,即把聯姻看成是一種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利益活動,而男女雙方是否兩情相悅則為次要,放到現代社會就是農村人嫁或者娶了一個掌握著更多優勢資源的都市人,對方就理應把一切社會資源與之共享。都市人則認為婚姻是兩個人的事,完全憑著二人的感情、個性決定,與家族利益無關。城鄉完全相悖的婚姻倫理引發了二人婚姻中無數的不愉快:何建國農村的這親戚那鄰居大到找工作、看病,小到貨車被扣押都要小西和她的家人掏錢、利用人脈資源去化解。在親子倫理上,農村講究的是子對父的絕對服從,在《新》中,何建國就是一個對他爹言聽計從的大孝子,哪怕是休了小西,只要是他爹開了口,他都會“哎”地一聲應承下來,這與現代都市如小西家那種建立在平等、民主基礎上的親子倫理完全對立!在交往倫理上,農村依然保留著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社會的印記——重視人情、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而在唯實唯利的功利觀、契約意識、理性至上意識的支配下,都市人則奉行建立在利益而非情感基礎上的交換關系,人情味淡薄。在《新》中,就充分體現了在沂蒙山區這樣的封閉、淳樸的農村尚存的傳統交往倫理與以顧家為代表的現代交往倫理的激烈交鋒:建國爹托顧家給親戚或鄰居辦事無不是出于對親情、鄉情的維護,件件非辦不可;在顧家人看來,這些事不過是一個個負擔,有能力辦就辦,沒能力就不辦,甚至非常反感!
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巴爾扎克曾經說過:“‘典型’指的是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包括著所有那些在某種程度跟他相似的人們最鮮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類的樣本······不僅僅是人物,就是生活上的主要事件,也用典型表達出來,有在種種形式的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處境,有典型的階段,而這就是我可以追求的一種準確。”[2]是的,作品就是通過上述的典型人物(何和顧是典型的鳳凰男和孔雀女的組合)、典型環境(沂蒙山區是典型的封閉農村,顧家是典型的大都市現代家庭)、典型情節,具體、生動、鮮活地描繪了城鄉倫理的差異、矛盾和沖突。就像顧小西在母親的尸體旁邊對何建國哭訴的那樣:“我已經看清楚了,隔在我們倆中間的這條溝實在是太深了,深到了我們的愛情無法逾越。”[1]265城鄉倫理的這條鴻溝到底能不能彌合?二者中哪一個更為合理?在作品客觀冷靜的敘述中,似乎城鄉兩種倫理都有它的合理性,就像何建國對小西說的:“我知道我們家有時提的要求荒唐過分,但作為一個出身農村考進北京的孩子,我同時也深知這種城與鄉之間價值取向和文化認同上的巨大差異。那差異不是說說道理就能夠說得通的,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道理。什么叫做入境問禁、入鄉隨俗?什么叫做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是。就是我何建國,就算我有著此刻的認識和文化,一旦回到我的沂蒙山老家,也做不到與現實對抗。”[1]197。對于兩種倫理,小說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價值判斷或者力圖糾正哪一方——這種判斷的缺席,一方面是當前中國社會倫理巨變時刻人們倫理認同焦慮的典型癥候,另一方面,小說通過這樣冷靜甚至冷漠的筆調,幾乎是零度地呈現著都市生活的缺陷、沉重、焦慮、吊詭和變形,旨在引導人們思考倫理沖突背后中國社會的矛盾及根源。
首先,都市倫理和鄉村道德的種種沖突背后折射出的不僅僅是鄉村文化本身的根深蒂固,還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城鄉發展的嚴重不平衡造成的農村依舊貧窮。就是因為窮,何建國們的一枝獨秀必然伴隨著他人和集體的巨大付出和犧牲,所以建國爹們才會那樣理直氣壯地讓他們“償還”;就是因為窮,才會使得農民的倫理體系依然建立在平均、共有、共享才能夠活下去的觀念之上!如何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征途上有效地實現城市對農村的反哺,逐漸彌合城鄉倫理的巨大裂痕,乃當務之急!
其次,從社會文化觀念的層面來說,伴隨著現代化進程(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形式是改革開放),中國日益從一個由儒家思想主導的人情社會向由契約精神主導的法理社會轉變。因為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宗法社會,所以強調的是人情倫理,法律層面的契約形式和意識層面的契約精神在社會交往中都不占主導地位。中國人的契約意識是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推動下的產物。英國法理史學家梅因說過:“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都是一個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3]看來,契約意識的形成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但是它在使人際關系變得互利、平等、理性和正式的同時也會使現代人越來越缺乏人情味,對人情社會的種種倫理越來越不認同、不適應,就像《新》中,小西媽對建國爹仗著是她的親家在醫院橫沖直闖的行為流露出的極度反感的心態一樣。
二、都市女性現代意識的凸顯和都市男性對傳統(鄉村)女性的渴望之間的沖突
作品中小西媽—小西爸—小夏三者的情感關系便是這一沖突的典型表征。小西媽是一個事業心極強的現代女性,高強度的工作勞累猝死后,小西爸沒多久便和來自何家村的保姆小夏結合了。作品中兩個小細節很耐人尋味:小西媽猝死后,在兒女的支持下,小西爸曾經和同是中文系的秦教授相處了一段時間,但他卻不怎么上心,反倒是小夏的再次到來讓他無比安慰,小夏過年要回家一趟都會讓他倍感失落······母親還在世的時候,小西和爸爸曾經聊到過保姆的事情,小西爸借著毛姆的《寶貝》一書,表達了自己心目當中的理想保姆——對家政事務無所不通、善解人意、完全合乎你的心意你的需要······從小西爸對小夏的認可和依戀來看,小夏就是他心中理想的保姆——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個保姆型的傳統妻子,而不是像小西媽這樣的強勢忙碌的事業型現代女人。
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下,都市女性身上的現代特質如重視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忽略了家庭,在家中強勢霸道等越來越突出,女性的勤勞、樸實、溫柔、善于持家等傳統品質反而在封閉的農村保存得更完整——像小說中的建國嫂子、小夏就是很典型的傳統女性。根深蒂固的男權意識使得都市男性在擇偶時往往會很傳統,這無疑是都市女性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不得不面臨的阻力,期待男性變得開明或者女性放棄事業回歸傳統似乎都超前或滯后于時代,男權意識形態或許只有經歷時間長河的無數次洗滌才能淘盡!
三、物化的情欲和洋溢著鄉村社會溫馨的情感主義觀念的愛情的沖突
劉凱瑞—簡佳—顧曉航三者的情感關系便是這一沖突的典型表征。當劉明確告訴簡佳不可能為她離婚之后,簡佳在感情上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她拒絕了劉的包養要求而選擇了事業剛起步卻追求純美愛情并且愿意和她組建一個正常家庭的小青年顧曉航。因為在簡佳看來,自己此時對劉已經沒有愛情了,如果接受了劉的要求,和劉之間就墮落為完全物化的情欲了,即在完全物化的情欲和純潔的愛情之間,她選擇了后者。簡佳在作品中是一個十分完美的人物,她的選擇也無疑具有理想色彩——當下現實中的女性恐怕遠沒有那么瀟灑!是不是有了房子才配談愛情,選擇一份完全物化的情欲,比如做有錢人的二奶,是否比組建一個正常的家庭來得更為實際?這些問題都是當下都市女性最為困惑的!所以說,盡管小說中的簡佳及其選擇具有理想色彩,但是她經歷的一切卻間接地暗示出都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矛盾沖突的又一表征:與資本糾纏在一起的物化的情欲和洋溢著鄉土田園般詩意的純潔愛情的沖突!
愛情當然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正常的愛情說到底是男女雙方靈肉上的相契合。在現代社會里,物的極大豐富時時刻刻刺激著人的欲望,商品的拜物教已經成了失去信仰的現代人的主導意識。這使得獲得物的資本變得越來越神圣,它的力量無處不在——一切都可以用資本來購買,一切都可以用資本來衡量,就連原本神圣的愛情也要放在資本的秤上去掂量掂量!可見,物化的情欲是現代資本社會的產物!問題在于,人本身是一種情感動物,她需要獲得一種精神性的滿足,而且這種滿足越不帶有功利色彩給人的慰藉感越強,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懷念那逝去的卻單純、溫馨的鄉村情感的原因。可見,都市女性上述那么多困惑、矛盾、痛苦和糾結的根源(亦即都市文化和鄉村文化在這一層面沖突的根源)在于物質和精神本質上的對立,在于現代人對物的極度依賴和出于人本性的對純潔情感的渴望的沖突!這或許是現代人在觀念轉型中必經的!小說中,當面臨二選一時,簡佳寧愿舍棄奢華的物質享受,選擇一份帶有鄉土田園般美感的純美愛情,因為她不想欺騙自己的內心。
結語
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沖突本是一個復雜的文化課題,《新結婚時代》通過選擇當下很典型的三個角度將這一復雜課題加以感性呈現。沖突背后折射出的是轉型期的中國必經的種種沉重、吊詭與無奈:現代化給中國人帶來物質實惠的同時也造成了城鄉發展的更不平衡,給中國人帶來現代觀念的同時也進一步加速了傳統文化的衰落(如人情社會的漸失);傳統中有些雖是糟粕(如男權意識形態)卻根深蒂固,其無疑是觀念現代化的阻力,有些與物化時代水火不容卻又符合人本心的需要(如鄉土田園般美感的純美愛情),現代人失去了它靈魂自然無所依附!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沖突可能并非新題,但是新世紀二者的沖突卻有了上述新的特點,探討這一問題不僅能更通透地讀懂當下,也會給予文化現代性更多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