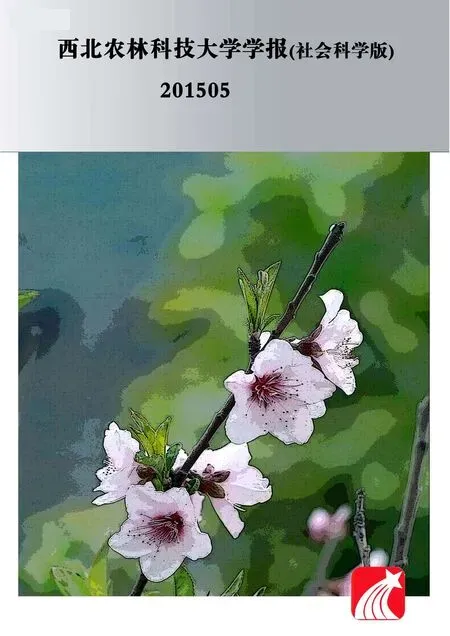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改革與立法突破
唐 欣 瑜
(海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海口 571158)
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政策改革與立法突破
唐 欣 瑜
(海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海口 571158)
盡管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有償流轉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內深受限制,但各地開展的試點實踐與地方立法對現行法律已有很大突破。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流轉已得到中央政策的確認,相關立法也有必要隨之完善,并具備了完善的可行性基礎。應從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益物權屬性、修改《土地管理法》相關規定、制定全國性專項法規三個方面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進行立法突破。
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流轉;土地立法
現階段,我國農村土地權利制度存在明顯不足的表現在土地的非流轉性、對農民利益的保障不足[1]。為進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國土資源部從1999年開始陸續安排了30處試點,基本遍及全國[2]。隨著改革的深入,各地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改革共識逐漸轉化為改革實踐,并以地方政策的形式確定實施,為繼續在全國層面上推行相關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礎。2013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流轉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得以確認,自此,現行法律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限制已被中央層面的改革政策所突破。結合十八屆四中全會中關于改革與立法的最新規定,從立法上完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是“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選擇。
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政策對現行法律的突破
(一)現行法律有關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規定
我國現有法律一直是以謹慎并有所保留的態度來對待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入市流轉。“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的規定最早見于1988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之后《土地管理法》在2004年進行修訂時直接沿用此項規定,但在第43條、第63條中進行相關限制:“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國有土地”“農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出租用于非農建設”。而后,其他的相關法律例如《城市土地管理法》也相應地規定城市規劃區內的集體土地有償出讓的前提是“必須征為國有”。2007年《物權法》出臺,并未就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作出任何突破或新的規定,反而直接在第151條中表明“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規定辦理”。
上述規定基本反映出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法律對待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態度:原則上并不允許有償流轉,甚至態度鮮明地禁止集體土地用于非農建設。盡管如此,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在現行法律中也并非完全沒有合法的可能。立法者在《土地管理法》第43條第2款、第63條第2款中還是為流轉留下了空間,集體所有的土地經依法批準后可以用于非農建設的途徑是“興辦鄉鎮企業和村民建設住宅以及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與“企業因破產、兼并等情形致使原本依法取得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在特殊情況下發生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由此便具備了法定依據,隨后《物權法》中亦有條款與這一依據遙相呼應,“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183條。。
《土地管理法》所提供的法定依據促使集體建設用地合法設立,例外的規定又為其隱形入市提供了變通路徑。面對集體建設用地在各地農村日趨形成的龐大規模,現行法律卻過于剛性地規定了其使用權流轉:一方面禁止主動流轉,另一方面承認其在特殊情況下的被動流轉。基于現行法律的搖擺不定,除了很小一部分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特殊流轉以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其他的大部分流轉處于違法私自轉讓的無序狀態,無法像國有建設用地那樣在土地市場內公開正常進行。
(二)試點地區出臺的地方性法規
為配合試點的探索與實踐工作,讓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在無法可依的大前提下得到地方的法制保護或實現有章可循,一些地方性法規、規章在不同的試點地區相繼出臺并得以實施。有關數據顯示,制定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暫行(試行)辦法的省、市級地方政府在2000-2009年間就有16個[3],2009年以后,尤其是2013年前后,沒有制定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辦法的一些省市也相繼出臺了相關地方性法規、規章。筆者對其中18個省市頒布的地方性法規、規章進行了歸納總結*具體參見關于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以下地方立法:上海市(2010)、安徽蕪湖市(2007)、浙江無錫市(2007)、江蘇蘇州市(2010)、南京市(2011)、廣東佛山市(2004)、廣州市(2011)、海南省(2013)、遼寧大連市(2003)、河北省(2008)、河南安陽市(2003)、洛陽市(2012)、湖北省(2007)、湖南省(2008)、云南昆明市(2010)、重慶市(2008)、四川成都市(2010)、貴州思南縣(2013)。,大部分地區大刀闊斧推進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流轉,不再是之前謹慎的態度。符合下列流轉條件的集體建設用地均可進行流轉:(1)經依法批準并合法取得;(2)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總體規劃; (3)沒有權屬糾紛,界限清楚;(4)已經辦理相關用地手續。各地規定依法取得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不能用于開發房地產和建設住宅,但對流轉范圍的規定卻大有不同,一些地區明確規定鄉(鎮)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宅基地不在流轉范圍,例如湖南、廣州、昆明等地一些地區允許鄉(鎮)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的流轉,例如河北、湖北等地,一些地區直接明確宅基地也可以流轉,例如我國西南部地區的四川成都市與貴州思南縣。各地相繼出臺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政策并不統一,大部分帶有地域性色彩,變動性也比較大。
(三)改革政策對現行法律的突破
《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2005年施行)第一次以政府規章的形式打破了“非經政府征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入市的傳統體制,開創了征地制度與農村非農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制度并存的時期”[4]。由此,各地相繼進行的試點也被稱為是繼“土地家庭承包”之后,中國農村開展的“第四次土地革命”[5]。2013年11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流轉” 歷史性地出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表明國家從中央層面上進行頂層制度設計,為各地的改革進一步指明方向。總體而言,改革政策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行法律實現了突破:(1)突破了國有建設用地在土地市場的一級壟斷。試點地區的改革實踐“傾斜性地改變了現行農村土地必須經政府征為國有方能用于非農用途的限制,突破國家對建設用地一級市場的壟斷”[6],原來由國家單一供應的建設用地供應體制轉變為國家與農民集體共同供應。(2)突破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主體只能是農民集體及其內部成員的限制。在現有法律框架內使用集體建設用地必須受到身份的制約,例如集體舉辦的鄉鎮企業才可以使用建設用地,宅基地只能流轉給同一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其他成員。但各地改革政策中規定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主體可以是國有、集體、私營企業、農民、城市居民等任何組織或個人,其流轉也不再限定為鄉鎮企業與集體內部成員。(3)突破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類型。2008年重慶市出臺《農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暫行辦法》,初步確定建設用地掛鉤指標可以進行交易;2011年南京市出臺的改革政策將流轉的形式擴大到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與建設用地實物對應)和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并在實踐中實現了用地指標的流轉平臺交易。由此可見,地方的改革政策突破了現有法律單一的實物交易類型,在集體建設用地的市場交易中創造性地產生了與實物交易并存的指標交易。
二、立法完善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自發流轉混亂的應然選擇
由于從流轉范圍、流轉主體、流轉秩序、流轉收益分配再到流轉監管都因確實無法可依而呈現出混亂狀態,我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要從目前的自發流轉轉化為正式流轉十分困難,當前對其進行調整也只能依靠《土地管理法》中的幾條零星規定。一方面是現實中流轉的需求在不斷增長,加上集體建設用地所涉社會關系原本就相對復雜,這僅有幾條規定也顯然已經滯后且不合時宜。另一方面,進行流轉的隱形市場屢禁不絕,當中的無序交易卻又在監管之外,長此以往,農民集體及其成員作為所有者的利益直接受損將會是不爭的事實。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推進,這一現象會更加普遍,法律如果仍不從制度上加以引導,將會使流轉更加混亂失控,農民集體及其成員原本應得的土地收益也會隨之流失。
集體土地作為稀缺資源,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了人們基于利益的驅動會使用或轉讓集體土地使用權,其流轉趨勢并不是法律阻止就可以避免的,反而會在市場的影響下逐漸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日益增多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糾紛。糾紛一旦發生便很難處理,訴諸司法程序后司法機關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面,流轉合同是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的,《憲法》《物權法》一再重申“平等保護”,尊重當事人對其私權處分的意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國法律原則上并不允許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有償流轉,甚至態度鮮明地禁止私下流轉,但各地進行的試點改革突破了對這些限制,至少在當地的政策下,流轉是合乎規定而可以進行的。根據我國合同法相關司法解釋,一份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合同是否判定為無效,人民法院應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準則,而不能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但法院在審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案件時既不能棄法律于不顧,亦不能對當地因配合改革政策而出臺的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視而不見。處于兩難境地的地方法院,往往不能像往常那樣正常、合乎邏輯地解決糾紛,甚至會要求當事人自行協商解決。這種放任自流的司法態度使得本就流轉混亂的集體建設用地糾紛不能及時解決甚至激化矛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甚至相關政策不適時改變,隨著集體土地自發流轉交易日益增多,可能會衍化為一大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
(二)是實現立法與改革政策相銜接的實然要求
在我國,集體土地的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政策的影響力甚至超出了立法。從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到黨的十八大報告,我國法律制度在政策與改革實踐的影響下已從絕對禁止集體土地流轉到《土地管理法》提供法律空間可以特殊流轉,事實上也在慢慢放寬對集體土地流轉的限制,國家、地方的改革政策與立法正逐步實現銜接。而長期以來我國集體土地的流轉均是一種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其特點是由市場行為影響立法,但卻由于缺乏立法引導,這種自發性流轉先天就“發育不良”,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也并不例外。大部分的流轉是由農民在民間自發形成,同時還要避過法律的硬性要求,往往只能在私下進行,即便是同一區域的流轉,也無法形成完整的體系。因此,主體多元化、方式多樣化、范圍不明確、秩序不統一是各地的流轉實踐呈現出來的普遍共性。由于對法律的突破沒有依據,流轉行為便不受法律保護,一旦出現糾紛,往往難以妥善解決,既損害了農民的財產利益,也影響了用地主體的發展利益。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改革進入深水區,“摸著石頭過河”,實踐先行立法附隨的改革模式弊端漸顯。
201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就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入市流轉提出 “有關部門要盡快提出具體指導意見,并推動修訂相關法律法規”;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再次明確立法和改革決策的關系*“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但是,不管學者們的改革建議如何凝結了各式各樣的智慧,尚在層層推進,也不管各地的實踐如何愈演愈烈,并已逐步深入,頂層設計中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相關立法始終呼之不出。難于選擇法定依據處理相關糾紛已是目前法院無法擺脫的困境,久而久之,不僅會對法律的權威性有所損害,實踐中進行的改革也會因為與法治處于緊張狀態而止步不前。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勢必需要實現立法與改革政策相銜接,體現在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中,應及時對各地經驗與改革成果進行總結提煉,改變以往“改革就是要突破現有法律”的認識誤區,及時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或專門立法,最終實現以法治引領相關改革,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合法流轉提供終局性的保障。
三、立法完善的可行性分析
(一)試點地區的改革成效為完善相關立法展現了創新可能
各地近些年一直在積極調研,開展試點,尋找符合農村集體土地市場化改革的新路徑。各地的集體土地試點改革經驗都是鮮活的,并在實踐過程中得到不斷驗證。以成都“還權賦能”模式的實踐為例,犧牲部分當期政府的收益,為重新把更多的集體土地收益返至農村中的農民集體及其成員提供了制度創新,這可謂是在改革遲緩、畏首畏尾的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中的一大亮點,實踐也證明農民集體及其成員得到了更多、更有保障的收益,發揮出農民集體和農民的主動性,對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早期的南海模式通過集體決定將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明確了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均得以分享土地非農化進程中土地級差收益上漲的利益。但南海模式對現行法律的大幅度突破,也導致一些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流轉試點經過實踐的考驗,不論是效果不甚理想還是取得了良好成效,都可作為嘗試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流轉的一類有益經驗,為今后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提供了正面或反面的參考。
絕大部分早期的改革是在地方和基層發動的[7],集體土地上曾經最重要改革——家庭承包責任制就是從一個地方擴展到另一個地方,并迅速遍及全國,最終被立法確認鞏固。地方試點的創新與實踐越能體現集體所有者地位和使用權人處分自由,就越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和農民集體及其成員的持續利益,二者之間的良性循環不僅刺激各地不斷涌現出各類創新,也促使創新能最終實現并被普遍接受。創新的結果并不是帶來利益,而是要被立法所鞏固,發揮其更長遠的功效。在地方實踐的影響下,國家政策和法律正逐步實現與集體土地尤其是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改革實踐的銜接,向著有利的環境轉化,這些都得益于各地試點的改革成效為完善相關立法展現了創新可能,同時為在全國層面上開展相關改革奠定了制度政策基礎。
(二)國有土地使用權成熟的流轉制度為完善相關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鑒
我國國有土地使用權流轉早在法律的確認下,經過多年的市場實踐后逐漸形成相對成熟的一套流轉制度。最早進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時,就對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進行了相關借鑒。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央的政策演化為實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同權”,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同地、同價、同權”實質上就是規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國有建設用地不能因為所有權不同遭受歧視[8],二者同等入市,在肯定政府對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管理正當性的前提下,按照同樣的市場原則定價,并在土地市場進行交易時具有同等的權利。由于基本沒有流轉中介機構例如土地評估機構、土地融資服務機構等來規范操作,流轉一方的農民集體及其成員也缺乏交易前對土地進行定級與價格評估的資質和水準,自發形成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在地價上也是“自發形成”,流轉過程中的交易雙方經協商后就可以直接確定土地價格,體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其中大部分流轉都沒有到土地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土地價格更因此缺乏有效監督與規范管理。私下議價的直接結果是集體土地市場地價普遍低于國有土地,不僅讓集體土地收益不當流失,即便是國有土地市場的運行秩序,也會受到波及。
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目前在管理上存在的很大空白,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可以提供許多有益的成熟經驗以供借鑒。由于入市交易是建立在土地規劃、審批、整理等相關機制業已相對成熟的前期基礎之上,國有建設用地已經形成一套科學合理的城鎮地價體系,該地價體系以基準地價和標定地價為核心,依據較為成熟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價格評估,可以向相關交易主體提供完善的價格信息。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成熟的流轉制度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建立從估價到融資等一系列管理范程提供必要的理論借鑒與技術支持。從短期效益來看,可以幫助集體建設用地建立相關制度以應對日益龐大的流轉需求。就長期目標而言,在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大背景下,也可以從整體上為完善我國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相關立法提供有益經驗。
“實施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制度是為了將所有權歸屬于農民集體的非農集體建設用地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由此強化國家對土地市場的宏觀調控,保護農民集體及其成員的切身利益”[9]。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觀點,但也應該看到,即便現在城鄉建設用地在統一的土地市場中實行同地同權同價,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原來由國家單一供應的土地供應體制轉變為國家和農民集體供應時,如何處理二者關系就成為了新的問題。因此,借鑒國有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成熟經驗來適當彌補當前的管理空白,已經不僅僅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在現階段進行立法完善所要考慮到的因素。從更深遠的意義上看,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本身就是對相關立法隨之完善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提出的新要求。
四、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立法完善路徑
一般認為,“流轉”不是一個傳統的法律概念,但流轉已經成為我國土地制度下的一個政策性用語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直接反映在法律中,流轉是指權利客體在不同主體之間的轉移。基于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是我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特有規定,相關立法的完善即是在保持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建立實現農村集體土地和城市國有土地法律地位平等、同地同權同價的一系列法律機制,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具體而言,立法的相關完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在《物權法》中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益物權屬性
《物權法》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參照《土地管理法》相關規定”,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性質并未因《土地管理法》的規定而有所明確。有學者甚至將現行法律的語焉不詳理解為 “《物權法》所規定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是建立在國有土地上的,按照物權法定原則,既然物權法未對其進行明文規定,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就不是物權,更說不上具有用益物權屬性”[10]。按照我國《憲法》與《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分屬于集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兩種所有權實質是相互獨立、地位平等的,并無等級差別,更不存在派生與隸屬關系。根據《物權法》第4條所寓意的物權平等原則,既然在國家所有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及其附屬設施的,可享受用益物權保護,那么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同等使用土地用于相同目的,也應同等享受用益物權待遇。由此可參照《物權法》中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有關規定,以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為目標,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相關內容進行完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物權法》中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益物權屬性是對現行法律中不平等的內容加以調整并使其符合物權法平等保護精神,也是確認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行為合法所必備的前提條件。在此前提條件之下,一旦發生流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就必須遵循物權變動的規則,以登記與交付為要件,并由國家對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進行規范管理,不再任由當事人隨意自行約定。
(二)修改《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
有學者認為,《土地管理法》的制定和修改理應遵守《物權法》關于物權的基本規定,《物權法》卻本末倒置地將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這一重要物權類型留待《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去完善[11]。依循法理,具有私法性質的《物權法》效力要優于具有公法性質的《土地管理法》,鑒于目前已經出現的沖突,進行立法完善時不能再加劇矛盾,而要以符合我國相關法律的效力設置為前提。盡管當前的《物權法》并未將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為一重要物權類型,但《物權法》也并未明確限制甚或禁止該項使用權的流轉。因此,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與現實需要先行刪除或廢止《土地管理法》中“禁止流轉”或“限制流轉”的有關條款,將“允許集體建設用地依法流轉”的內容加入規定。具體而言,在遵守《物權法》關于物權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應將“可以使用集體土地”的內容*筆者認為,《土地管理法》第43條可以具體修改為:“任何單位或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申請使用國有土地,也可以申請使用集體土地。”加入到《土地管理法》第43條中,并在第63條中寫入“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的規定,同時于該項條款中確認公益性集體建設用地即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不在流轉的范圍,以保障農村正常的公共生活以及實現農民集體為集體成員提供公共服務的功能。由于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在我國一直爭議很大,學界尚無統一共識,實踐中的試點也遲遲未能開展,較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在法律上確定流轉;而現行《土地管理法》將村民建設住宅用地與其他集體建設用地并列規定,與《物權法》分開規定宅基地使用權與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則相沖突。因此,筆者認為,在對第63條進行修改時需要充分考慮到上述問題,修改之后應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但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等公益性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與村民宅基地使用權除外。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前提下,依法取得的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通過出讓、轉讓、出租以及其他方式進入市場”。為保持法律的一致性,在修改《土地管理法》相關規定的同時,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都應當就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作出相應修改,在此不再一一闡述。
(三)制定有關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專項法規
從長遠看,立法完善的最佳選擇是在《物權法》中明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益物權屬性,或是修改《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保障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能在有法可依的環境下實現公開流轉。但從目前看,如果急欲解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秩序混亂、于法無據的狀態,可以先行制定并出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在對各地經驗與改革成果進行總結提煉的基礎上,將地方和基層改革創新形成制度性規范上升為全國層面上的制度政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雖為全國性的專項法規,但其本身是在現行法律尚未及時完善或是暫緩進行完善的階段推行的,理應對現行法律中缺乏的部分進行系統規范。因此,在該項專項法規中首要明確的就是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基本概念:“在保持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依據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的原則,由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即鄉(鎮)村各級農民集體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通過出讓、轉讓、出租、抵押、入股和聯營等方式讓渡給其他權利人行使的行為”。隨后則對流轉的原則、主體、客體范圍、形式、程序、價格、期限、交易平臺以及流轉收益的分配與管理等流轉制度進行具體規定,同時規定流轉過程中以及流轉后監督管理的主體、監督范圍、監督規則等監管制度,以及出現違法交易等相關問題時的處理辦法。
五、結 語
作為一種商品,土地產權應當“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其投入到商品經濟的洪流之中”[12]。對于我國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法律限制過,行政干預過,執法清理過,經濟也制裁過,均未阻擋住其越演越烈的步伐[13]。根據最新的黨和國家政策,爭論多年能否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問題在立法政策層面取得重大突破[14]。2014年10月23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通過,闡述了改革與立法的關系,由此,以法治引領和保障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改革,過去那種依靠政策文件推進改革的隨意做法就必須改變。盡管學界的各研究觀點就完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議,但作為物權制度的基本立法,2007年才頒布的《物權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修改,相比之下修改《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似乎更為可行,當然,如果認為當前的試點經驗尚未成熟到應立刻修改相關法律的程度,也可由相關部門制定全國性專項法規來應對當前的流轉亂象。總而言之,關于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入市流轉已達共識,目前研究的重點理應是如何從立法層面規范其入市流轉,在全國范圍內完善相關立法也已勢在必行。
[1] 王利明,周友軍.論我國農村土地權利制度的完善[J]. 中國法學, 2012 (1):45-52.
[2] 吳越,沈冬軍.農村集體土地流轉與農民土地權益保障的制度選擇[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3.
[3] 郭潔.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規劃實施的經濟法調控[J]. 法學,2010(8):76-88.
[4] 王權典.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法律問題研析——結合廣東相關立法及實踐的述評[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131-139.
[5] 張鵬,王亦白.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試點的思考[J].法學,2006(5):32-38.
[6] 唐欣瑜,梁亞榮.我國農民集體土地收益權權利演進之回顧與展望[J]. 農業經濟問題,2014(5):61-67.
[7] 崔文星.中國農地物權制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4.
[8] 華生.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M]. 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105-106.
[9] 劉道遠.集體地權流轉法律創新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28-129.
[10] 龍翼飛,徐霖.對我國宅基地使用權法律調整的立法建議[J]. 法學雜志,2009(9):28-32.
[11] 黃志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法律問題[J]. 中國土地,2013(9):54-56.
[1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6 .
[13] 蔣曉玲,李慧英.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法律問題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4-65.
[14] 韓松.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J].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70-75.
Study on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of Use Right’s Circul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n China
TANG Xin-yu
(SchoolofPoliticsandLaw,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Although China’s existing law always take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marketizational circul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the pilot practice and local legislation of some areas have been a great breakthrough to the existing laws.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can circulate in the market. It’s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improve relevant legislations about the circul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There are three proposals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s as follows: clearing the usufructuary right’s attribut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revis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land management law”and formulating special laws about the circulation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land legislation
2014-11-25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12M51189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1BFX062)
唐欣瑜(1987-),女,海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海南經濟特區法治戰略研究基地研究成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法、土地法。
F321.1
A
1009-9107(2015)05-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