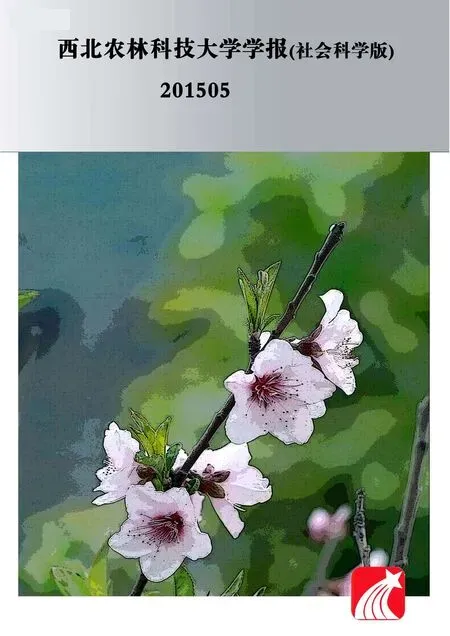資本轉換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
劉 程
(上海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資本轉換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
劉 程
(上海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關于移民融合問題的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主體缺失”的局限。基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訪談發現,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理性轉換是他們在城市融合過程中的重要行動策略。他們通過教育投資、交往投資、印象管理等方式實現了三種資本之間的相互轉換。這一轉換過程推動了新生代農民工各種資本的數量增加與結構優化,豐富了他們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內容,推動了他們的城市融合進程。不過,資本轉換的策略行動對新生代農民工(移民)融合的回報效應并非一成不變的線性關系,而是受到制度安排、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初始位置等因素的影響。
資本轉換;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
一、研究問題與思路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西方社會科學曾就“移民融合”(integration of migrants)問題展開持久的探討與爭辯。芝加哥學派的帕克(Robert E. Park)與伯吉斯(Ernest Burgess)提出:移民融合過程是移民通過與遷入地社會的接觸、互動、溝通,彼此滲透(interpenetration)和相互接納,并最終實現經濟整合、文化適應、社會融入及身份認同等目標的社會過程。這一過程包括“接觸”“競爭”“適應”和“融合”四個固定的發展階段[1]。米爾頓·戈登(Milton Gordon)進一步系統化了這種經典融合理論,又稱“同化理論”。經典融合理論在移民研究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它所主張的移民融合的單一模式和線性遞進等觀點也引發許多批評。在這些學術批評的基礎上,學術界又提出了“多元文化論”[2]“曲線融合論”[3]“區隔融合論”[4]“空間/居住融合論”[5]“婚姻融合論”[6]等理論學說。這些學說對經典融合理論的修正與拓展是“言如其實”的。在現實生活中,移民在遷入地社會的融合模式是復雜多樣的,而不只是“同化”進入“中產階級”群體或“主流社會”的單一模式[7]。移民融合的差異化模式大體可以從群體層次和個體層次兩方面來進行歸因。在群體層次,移民自身的膚色、母語、宗教等先賦性特征,以及遷入地的人口構成、對待移民的態度,當地少數族群的社會階級、種族地位、定居地點等都會影響到移民的社會融合[8]。在個體層次、教育水平、工作技能、遷移時間、遷入地語言的掌握情況及代次因素等也是影響移民融合的重要因素[9]。
在當代中國,農村流動人口(即“農民工”)當屬最大規模的移民群體。他們遠離家鄉進入城市生活,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謀職,雖然賺取了相對農業生產更高的工資收入,卻難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他們的生活經歷與發達國家的跨國移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隨著越來越多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工作,并表現出較第一代農民工更高的融入城市的意愿,有關這一群體的“城市融合”問題自然成為了學術研究的焦點。很多研究認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進程的社會因素包括制度安排、經濟分割、社會排斥、文化排斥以及空間隔離等[10]。正是這一切,使得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在個體因素方面,許多研究表明:年齡、婚姻狀態、在城市居住時間、生活經歷以及人力資本、社會網絡等因素則是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個體差異的關鍵[11]。
這一領域相關研究的主流取向是“結構范式”,即強調社會環境與外在結構對個體生活機會的限制。這些研究深刻地描述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結構性弱勢地位。但是,它們仍然存在如下幾點不足:首先,這些研究強調新生代農民工的“被動”意涵,而對他們作為行動主體的能動性關注不夠。其次,這些研究大多是著眼于農民工整體的研究,而較少關注到城市融合的個體差異性及其原因。因此,本研究擬從能動主體的視角來探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差異性的動力機制,從而試圖部分地彌補既有研究中“主體缺失”的局限性。
(二)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觀點是:理性行動是影響移民融合的個體差異的關鍵原因。國際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的社會經濟融合是一個通過重塑資本和“資本轉換”(converting of capitals)而實現移民自身價值的過程[12]。“資本”一詞最初為經濟學所使用,主要指的是設備、原材料、土地等生產要素。后來,它被擴展到非物質資源范疇,比如“人力資本”。在社會學界,“資本”概念得到更大范圍的拓展,尤其體現在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發展。更具廣泛意義上的“資本”分析框架來自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將“資本”分為三類: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他認為,每個行動者往往同時擁有多種類型的資本,但是,其占有量通常是存在差別的。三類資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又是可以相互轉換的[13]。依賴其所在的場域,各種資本之間可以按照一定的兌換率進行形式交換。正是通過不同資本之間的相互轉換,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和社會地位的再生產得以發生[14]。比如,花費金錢投入(經濟資本)可以積累具有競爭力的文化資本,而這些文化資本則可借助勞動力市場而收獲可觀的收入回報(經濟資本)。在現實生活中,“資本轉換”往往是作為一種能動策略而發生的。它通常是行動者利用某類資本形式的存量優勢來彌補其他資本形式的相對缺乏,從而以支付盡可能低的代價達到特定目的的行為方式。
在西方學術界,“資本轉換”對移民融合過程的促進作用已得到一些經驗研究的證實。移民帶著一定形式的資本來到新的環境,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移民原先擁有的資本未必能再繼續發揮作用,即:部分資本可能會出現貶值現象(例如教育資格、工作經驗),一些資本可能需要重塑(如語言交流、專業技能),還有一些資本則需要從零開始重新積累(如社會關系)。面對這種情況,移民必須投身于資本轉換和重塑的過程中。“資本轉換”過程能夠幫助移民積累更多的資本形式,可以促進移民的適應、就業和社會融合進程[15]。這對本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分析思路。
基于此,本研究的理論依據是:“資本轉換”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過程中的能動策略——通過推動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理性轉換,他們可以獲取更多的發展機會,從而更加深入地參與和融入城市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16]。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那些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從農村地區來到城市工作的流動人口。與第一代農民工群體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年齡更加年輕、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為活躍,而且大多排斥農村生活、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普遍強于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并愿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了更多努力。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法獲取資料,內容大致包括基本資料、職業狀況、職業發展與工作狀態、基本生活狀態、城市融入狀況等方面。課題組于2010、2011、2014年共開展了三批次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半結構式訪談,涉及到新生代農民工25人,平均訪談時間在50分鐘/人。訪談對象的職業領域和工作崗位的跨度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群體的異質性。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資本轉換行動:過程、策略與規則
分析顯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轉換行動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過程中的重要的能動策略。通過三種資本之間的策略轉換方式,他們的資本擁有量以動態的、轉化的形態不斷進行再生產,資本擁有的結構也不斷得到優化,這對城市融合過程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經濟資本的轉換行動
經濟資本在新生代農民工的資本轉換過程中的效率是最高的、也是最直觀的。他們通過工具性投資(送禮、送回扣等)和情感性投資(相互聯系、走訪等),移植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初級社會關系,選擇性地建構基于業緣、趣緣等紐帶的次級關系網絡,不斷擴大社會資本存量,優化社會資本結構[17]。比如,從事銷售工作的吳先生(S5)就通過業緣關系結識了很多朋友,從事服裝加工的魯先生(S16)通過業緣關系認識了很多的客戶,個案萬小姐(S7)則是通過業緣關系遇到了現任戀人(上海本地人)。在特定的情形下,一些新生代農民工還會選擇利用經濟資本直接購買通過社會資本運作而提供的服務,比如獲得優先錄用機會,或為子女教育爭取機會,如理發店店主石先生(S24)。
短期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在上述過程中的確“損失”了一定的經濟資本,但是,這種投入具有轉換的效果。它將新生代農民工經濟上的投資轉換成為情感、責任、義務等,從而事實上生產出了可供日后動用的“社會資本”。所以,這種轉換過程在本質上屬于一種能動策略。這種策略的邏輯直觀地體現在個案張先生(S6)的解釋中:“(將來)誰都會有求人的時候。”正是通過這一轉換過程,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資本的投入被轉換成為嵌入于他們關系網絡中、可隨時被動員的社會資源。
同樣的,“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換也頻現于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與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投資文化資本方面(尤其是教育與培訓)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他們從大眾媒體和親身經歷中體會到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格、職業技能)對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意義。因此,不少新生代農民工都積極開展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比如,個案王小姐(S2)堅持在工作之余自學會計,為日后更換工作打基礎。事實證明,經濟層面的教育投資是他們增加文化資本(尤其是布迪厄所謂的“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和“身體形態”的文化資本)的最佳途徑。這一方式被布迪厄稱為“社會煉金術”[18]。
兩者之間實現轉換的另一種能動策略是“文化消費”。在業余生活中,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花費不菲的價格購置電腦、智能手機、書刊雜志等文化產品,積累了更多“物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并從中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享受,如:從事工廠一線操作工作的趙先生(S4)、從事酒店服務員工作的李小姐(S9)、作為某NGO組織核心成員的袁小姐(S22)。同樣,雖然這一過程也會損耗一定的經濟資本,但它會促進文化資本的不斷積累,而由此所帶來的長期收益則是十分豐厚的。
(二)社會資本的轉換行動
作為關系投資結果的“社會資本”,也會被他們加以動用,從而獲得經濟收益、增加經濟資本。首先,社會資本所承載的信息資源可以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豐厚的收入回報。在訪談中,從事綠化工作的方先生(S12)正是通過業緣關系結識了懂技術的合伙人小李,然后共同成立了綠化公司開展業務,其經濟收入才得以大幅提高(較之以前受雇于他人時)。此外,本研究還發現,嵌入于新生代農民工關系網絡中的“人情”“社會信用”“影響”等資源也能夠產生經濟回報[19]。在求職過程中,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都曾經借助關系網絡成員的引薦和幫助來獲取招聘信息、推薦機會等,比如由親戚介紹從事汽車銷售工作的楊先生(S14)、由老鄉介紹從事五金加工的個體戶小張(S25)。這些都是他們推動社會資本實現轉換的過程,它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回報。
許多農民工也在推動社會資本轉換成為文化資本的形式。通過社會資本的建構與運作,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獲得了良好的教育環境或機會(比如從有著“鐵關系”的上司等關系網絡成員那里獲得進修、培訓的信息或優先資格),使得他們在文化資本的爭奪與積累中占據優勢地位。同時,網絡成員的相互交往,促進了他們在耳濡目染中習得“身體形態”的文化資本。比如,從事酒店服務員工作的李先生(S3),就從酒店老板那里學到如何經營管理酒店的業務知識,這為他今后實現“自己當老板”的目標奠定了基礎。這種轉換不僅僅創造了他們積累文化資本所需要的“場域”,還通過網絡中“他者”提供各種可能的幫助而加速了轉換進程。
(三)文化資本的轉換行動
西方關于移民的研究發現,移民會通過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教育資格證書等形式,謀得具有更高回報的工作職位[20]。這種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邏輯同樣體現在一些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如個案張先生(S6)通過業余時間參加大專進修班,獲得了相對其他同事更高的學歷(“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因此晉升為車間的“工段長”,崗位收入也有較大提升。而且,學習進修過程還促進了張先生“身體形態”的文化資本的積累,推動了其業務能力和車間工作效率的提高,按計件所得的收入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見,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過程雖然比較隱蔽,卻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在現代社會中,用文化資本去獲取經濟資本,不僅成為人們推崇和尊敬的方式,也越來越成為社會的主流。
一些新生代農民工還會借助自己的文化資本,通過教育培訓、印象管理、文化適應等方式,不斷精心編織關系網絡,并從網絡中動員有價值的資源。比如,個案萬小姐(S7)在文化消費(看演唱會)過程中就結識了很多本地朋友。還有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努力讓子女從小在城市接受較好的教育,使孩子有機會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進入一個嵌入資源的質量較高、數量較多的社會關系網絡,如個案張先生(S6)。這種轉換是建立在自我認同的前提上的,所以會比較穩定。不過,這一過程往往具有復雜和隱蔽的特征。
(四)資本轉換的基本規則
新生代農民工所擁有的各種資本既是特定場域中各種斗爭的焦點,又是他們斗爭過程中所使用的工具。他們所占有的資本情況制約了各種形式的收益的高低和多寡。作為策略行動的目標,他們通過資本轉換過程將手中的相對價值較低的資本轉換為價值較高的資本,以確保資本總量的不斷增加,并避免資本貶值的風險[21]。這一過程主要依循的是兩項原則,即“利益最大化”與“合法性”。在這一過程中,不同類型的資本的“不可替代性”是資本理性轉換的前提條件,而各類資本的不均等分布和不同人對于不同資本類型的需求差別則使資本轉換得以發生。
“資本轉換”過程所暗指的是:在很多時候,新生代農民工獲得一種形式的資本,是要以消耗其他形式的資本為代價的。而且,資本轉換的收益回報往往是充滿風險的。在訪談中,有的新生代農民工就遇到過一些“忘恩負義”“不講義氣”的“朋友”,所以他們不得不逐漸將其排除在關系網絡成員之外。而且,雖然經濟資本能夠部分地轉換為社會資本,但這種轉換也是不穩定的,其收益可能只是“潛在的”——一旦經濟資本喪失,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及其嵌入性資源可能會一同消失。所以,即使他們在關系網絡中擁有一些潛在的社會資源,但這些資源卻不一定能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
再者,新生代農民工各種資本之間轉換的可能性、被轉換的程度以及彼此之間的轉換率,不僅受制于資本本身以及資本擁有者的影響,而且會受到社會結構與制度安排的制約。比如,文化資本在新生代農民工獲得經濟資本的過程中至關重要,但是,其最有效的方式卻是借助于體制中的資格認定,即通過考試獲得職業資格等級證書或學歷證書。這種“制度形態”的文化資本是最具有公信力的,同時也是最具有轉換力的。相比之下,新生代農民工原先擁有的很多其他形式的文化資本,比如在農村精通的某項特別手藝(比如編織、鐵匠等),在城市里尋求資本轉換與資本積累的“兌換率”就往往很低,甚至是完全無效的。尤其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資本轉換過程是極其復雜的。
三、資本理性轉換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
借助各種資本之間的彼此轉化,比如通過“資本A→資本B→資本A”的良性循環,新生代農民工的資本存量會不斷增長。而且,這種轉換過程還會促進他們將現有資本類別轉換為更具競爭力的資本形式,優化擁有資本的內部結構,并獲得各種實質性收益。訪談發現,資本擁有的不斷積累與結構優化,有助于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形式和內容,并加速融合進程。
經濟資本的積累與優化,擴大了他們經濟生活的選擇范圍,并刺激了他們在城市的消費行為。訪談發現,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都熱衷于消費各種現代的、時尚的、新鮮的商品與服務,比如主張“到大城市里來,就要過大城市的生活”的萬小姐(S7)。在此基礎上,他們得以建立起新的“以城市為坐標”的身份認同。事實上,那些擁有優裕經濟資本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確有著更高的社會經濟融合水平,比如作為私企合作人的趙小姐(S10)、作為個體戶的小鵬(S11)、作為國企內勤主管的萬小姐(S7)、從事服裝加工的個體戶魯先生(S16)。
社會資本的積累與優化,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了更多的信息、機會、資源、影響、支持等回報,降低了他們在遷移過程中的經濟成本與心理成本,促進了他們求職、職業流動、升遷、加薪等工具性目標的實現。而且,親人、朋友等關系網絡自始至終還為他們提供著包括情感傾訴、危機應對等在內的情感性支持。再者,通過與關系網絡成員的接觸和溝通,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得以融入到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中。這一過程還為他們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并在潛移默化中消解了城市對他們的負面標簽。比如,作為私企合伙人的趙小姐(S10)和個體戶小鵬(S11)、從事汽車銷售工作的楊先生(S14),都從維護和動用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本中受益頗多。
包括資格證書、工作經驗等在內的文化資本的積累與優化,既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求職的核心砝碼,也是他們職業收入增加的關鍵所在。文化資本往往還是知識、素質與品味的象征,它對于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還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而且,積累文化資本的過程,尤其是形象意識的強化、語言的掌握與運用、法律與規則意識的增強等,也在潛移默化中賦予了他們以“現代性人格”與社會認同。這有助于推動他們與城市市民之間形成可共同接受的互動模式,弱化雙方的心理與文化排斥。比如,個案萬小姐(S7)即將結婚的男友就是上海本地人,這種被戈登等視為高水平移民融合的象征的“族際通婚”現象的出現,彰顯了大城市對這個群體越來越包容與接納的趨勢。
當然,資本轉換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的回報效應并非一成不變的線性關系,它會受到制度安排、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初始地位等因素的影響。在我國,由于戶籍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影響,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仍不得不從事一些流動性強的、低收入的工作,對其職業發展與城市融合都帶來了負面影響。而且,由于文化傳統、輿論環境等因素,城市長期以來都對農民工群體持有偏見與歧視的態度,使得他們的資本的積累與轉換行動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化過程對不同初始位置的人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比如,自雇農民工群體運作社會資本所帶來的收益,往往會大于受雇群體——因為他們的收益更多體現為商機、業務、利潤等,如作為私企合伙人的趙小姐(S10)、從事服裝加工的魯先生(S16)。
而且,資本轉換行動的回報效應也不是無限制的,而是存在一定邊界的。一方面,隨著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地區,新生代農民工之前掌握的某些資本可能會遭到貶值,乃至變得完全無用(尤其是某些文化資本)。而經驗研究表明,他們建構、積累、轉換這些資本的過程總是充滿艱辛的。另一方面,則涉及到各種資本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過程中的局限性。倘若新生代農民工單單擁有比較可觀的經濟資本,可以在城市置業安家,但是無法在當地建立穩定的社會交往與支持網絡,無法適應城市社會的生活習慣乃至文化傳統等等,都難言是真正意義上的“融合”。其隱含意思是:單單任何一種資本形式,在他們城市融合過程中的影響力都是有限的。
四、結論與討論
1.資本理性轉換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融合過程中的重要的行動策略。他們借助文化消費和人力資本投資等實現經濟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化,借助工具性投資和情感性投資實現經濟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化。他們通過職業流動等途徑實現社會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通過潛移默化的學習借鑒等方式實現社會資本向文化資本的轉化。他們還通過教育培訓、印象管理、文化適應等方式促進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轉化(雖然這個過程更加隱蔽)。
2.這些轉換過程推動了他們的資本積累與結構優化,帶來了信息、資源、機會、支持、認同等工具性與情感性回報,推動了他們的城市融合進程。因此,這種能動性的轉換過程是具有實踐意義的。這也意味著“理性行動視角”的解釋對于闡釋移民融合過程及機制是具有內在理論效度的。但是,資本轉換的理性行動對于移民融合的回報效應并非一成不變的線性關系,而是會受到制度安排、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初始位置等因素的影響。放眼未來,為了進一步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移民)的融合進程,必須逐漸破除這些結構性的限制[22]。而這注定將是一項漸進性的、復雜的、艱巨的綜合系統工程[23]。
3.資本轉換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具有促進作用,但它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本研究無法直觀地鑒別兩者的關聯強度的大小和作用機制的效應強弱。而且,資本理性轉換對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亞群體的實踐意義也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或者至少作用機制是有差別的,這在本研究中仍然沒有清晰地加以闡釋。再者,由于未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本研究無法區分研究對象在初始階段的資本擁有情況的不平等及其對資本轉換與城市融合的影響(即定量研究中的“內生性”問題)。這些均是今后研究的可能方向。
[1] Park Robert E. Race and Culture[M].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0: 150.
[2] Kallen Horace M.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Idea: An Essay in Social Philosophy[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6.
[3] Gans Herbert J. Second-generation Declines: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2, 15(2): 173-192.
[4] Zhou Mi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975-1 008.
[5] Massey Douglas S,Nancy A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Qian Zhenchao,Daniel T Lichter. Social Boundaries and Marital Assimilation: Interpreting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Intermarriag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72(1):68-94.
[7] 楊菊華. 從隔離、選擇融入到融合: 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 2009(1):17-29.
[8] Alba Richard D,Victor Nee.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826-874.
[9] Lieberson Stanley,Mary C. From Many Strands: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8.
[10] 許傳新. “落地生根”——第二代農民工城市社會適應研究[J].南方人口, 2007(4):52-59.
[11] 李樹茁,任義科,靳小怡,等. 中國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人口與經濟, 2008(2):1-18.
[12] 朱紅.轉換融合——中國技術移民在加拿大[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5.
[13]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C].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258.
[14] 方長春.地位獲得的資本理論:轉型社會分層過程的一個研究視角[J].貴州社會科學,2009(10):90-93.
[15] Drever Anita I,Onno Hoffmeister. Immigrant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Job-scarc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German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8,42(2):425-448.
[16] 盧小君,孟娜.代際差異視角下的農民工社會融入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14(1):36-46.
[17] 劉程. 資本建構、資本轉換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J].中國青年研究,2012(8):60-64.
[18] 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迪厄訪談錄[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9] 林南. 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M]. 張磊,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19.
[20] Rye Johan Fredrik.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An Analysi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Long-Term Capital Accumulation[J]. Acta Sociologica, 2006, 49(1):47-65.
[21] 布爾迪厄. 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M]. 楊亞平,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479.
[22] 朱國芬,李俊奎.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境遇和出路[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14(6):1-7.
[23] 余思新,曹亞雄.農民工市民化層次性解讀及其現實啟示[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14(1):25-35.
Converting of Capitals and Inte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to Cities
LIU Cheng
(InstituteofSocialSurve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020,China)
Current researches on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 of “agent”.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Converting of Capitals”among econom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basic rational strategy for them, in the ways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social network investment,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so on. This rational action helps increase the number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s, which accelerates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to cities, while this effect is not constantly in linear relation, but constricted by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itial position.
converting of capital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integration
2014-11-3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3CSH038)
劉程(1983-),男,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移民社會學、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
F323.6
A
1009-9107(2015)05-01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