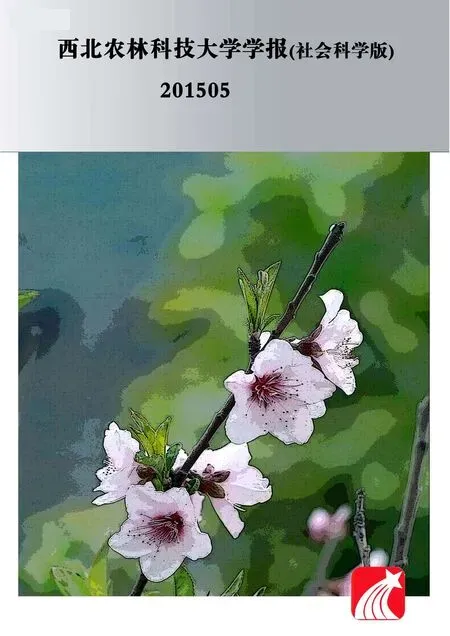建立農村環境ADR非訴訟機制探索
陳 兵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建立農村環境ADR非訴訟機制探索
陳 兵
(吉林大學 法學院,長春 130012)
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縱深推進,在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經濟推動農業工業化的同時,爆發式的鄉鎮企業增長、規模化的農業生產經營以及聚集型的農村生活場域的出現等,造成了農村環境污染的日益惡化,農村環境糾紛也隨之頻發,并顯現出與城市環境糾紛不同的特點。現行的以訴訟為主的糾紛解決機制在解決農村環境糾紛上較為乏力。為此,有必要通過構建新的非訴訟機制——環境ADR解決農村環境糾紛,以維護廣大農村地區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切實保障農村底層居民的環境權益的實現。
農村環境污染;農村環境糾紛;環境訴訟;環境ADR;非訴訟機制
一、問題提出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工業現代化和競爭國際化引發了農業現代化和現代城鎮化進程的提速,致使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類經濟發展形式和生產經營活動在廣大農村地區得以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各種環境污染也正日益侵蝕和損害著廣大農村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使其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其中頻發的農村環境糾紛嚴重影響了農村社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然而,現階段農村環境糾紛頻發的根源并不在農村自身,而是在大力發展農業工業化、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就農業現代化與傳統農業文明之間出現的激烈碰撞所產生的問題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未給予及時消解所致。簡言之,即我國高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在帶來無限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對生態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這種影響正由于所謂的環境保護的“城市中心主義”轉移至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致使農村環境污染越發嚴重,侵害了廣大農民的權益。因此,這種農村環境污染亦可稱之為轉移型農村環境污染,數量龐大的鄉鎮企業所引發的農村環境污染大致可歸入此類型。需要強調的是,筆者將要討論的農村環境糾紛除了上述類型引發的糾紛外,還包括基于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村居民日常生活所引發的環境糾紛,可分別描述為生產型污染和生活型污染[1]。
從世界范圍內各國或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歷史經驗看,在推進農業現代化,走農業產業規模化、聚合化、工業化發展道路時,不可避免地會對當地生態環境產生影響,當下要做的并不是徹底根治基于農業現代化帶來的環境問題——其不可能完全消除,而是要將農業生產發展帶來的對生態環境之危害降到最低,使之可控,即對農業生產型環境污染引發的問題可控,使致害者與受害者間的環境糾紛得以有效化解,既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亦保證農村環境的安全。與此同時,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社會二元結構形態,環境治理的重點和中心一直放在城市,尤其是那些超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大城市及其周邊,對廣大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尤其是對那些看似簡單的日常生活污染更是未能配套行之有效的環境治理設施和監督機制,致使農村環境污染,尤其是生活型環境污染基本處于無人治理的放任狀態。由此,導致了目前未能在我國農村地區形成有效的治理方案和具體措施,更談不上建立合理的具有實踐操作性的環境糾紛化解機制。
事實上,在我國農村地區的環境糾紛中,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是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居民,其實體性環境權利和程序性權利常常受到侵害[2]。正是由于這種實體性和程序性權利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更加劇了農村環境糾紛化解的復雜性和高難度,也由此進一步惡化了農村生態環境——因無法有效激發農村居民參與當地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和有效性,這種忽視或無視農民“天然在場”的特性在農村環境保護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認識和做法,不利于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和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3],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在“有損害就有救濟”的法治社會里,如何化解農村環境糾紛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關鍵,對于實現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環境安全的平衡,構建農村環境治理的法治路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二、訴訟在解決我國農村環境糾紛時明顯乏力
訴訟是目前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解決環境糾紛的主要方式,作為公力救濟取代私力救濟的選擇,訴訟可以使得各類糾紛在平等、公正、有序、安全的環境下得以解決。然而,由于我國環境糾紛解決機制是在以重視城市環境治理為中心,忽略或無視廣大農村地區的環境保護的情勢下建立起來的,其運行重心是以解決因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城市環境糾紛為主,尚未對農村環境糾紛給予應有的足夠關注,進而導致目前以訴訟為主的糾紛化解機制在應對農村環境糾紛爆炸式增長時明顯乏力。據不完全統計,在農村發生的各類糾紛中,只有不到12%的事件最終選擇了訴訟,且多是在和解或調解無效的前提下[4]。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在該中心代理的環境侵權訴訟中,原告的勝訴率僅為20%,且勝訴后的賠償也很難得到執行[5]。為此,當我們選擇以訴訟作為農村環境糾紛的主要方式并評估其價值時,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農村糾紛與環境糾紛雙重特征的影響,即將訴訟機制放置于農村社區考察時,兩者之間的現實沖突與融合可能成為了關注的焦點。
(一)訴訟方式對抗性強暫不利于農村地區糾紛及時有效的解決
西方語境下法治的最佳社會環境是“陌生人社會”,因此此類法治在西方國家更容易發揮作用,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社會效果比那些存在厭訟觀念的國家更加明顯[6]。作為一種重要的糾紛解決方式,訴訟無疑是現代社會最有效、最可靠的選擇,但是從實踐效果看,訴訟方式暫不適宜當前我國農村地區大多數糾紛的解決。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村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更多體現在經濟意義上,就社會心理和組織結構而言,大部分農村地區仍保留著極其濃厚的鄉土氣息,仍是一個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熟人社會”,這在客觀上導致了以訴訟——這種對抗性較強的方式去解決農村糾紛的困難。“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明顯不同的一點,即是當事人除了要求結果的公正外,往往還有更多其他的價值訴求。譬如,在糾紛解決后,希望恢復原有的人情關系,這就造成了廣大農村居民在很多情況下,不愿意選擇“對簿公堂”的方式來解決糾紛的心理。
(二)訴訟主體不明導致立案難
農村環境糾紛是一種新型的糾紛,類型多樣,涉及的利益主體多元,特別是由轉移型污染和生產型污染引發的環境糾紛,污染者往往與當地鄉鎮政府存在諸多利益“勾聯”,加之受害者眾多,稍有不慎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更為重要的是,目前我國民事訴訟法上尚未對大規模的環境侵權事件之原告主體資格做出明確規定*雖然,2013年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理論界和實務界認為確立了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但是,該規定并沒有確定公民個人的訴訟主體資格,就個人提起此類訴訟言,還是需要遵循普通民事訴訟原告資格的規定,即需提供直接證據證明其與所提起的訴訟爭議有直接利害關系,如此來看,加上環境損害取證責任的困難,致使很多情況下,由個人提起的環境侵權訴訟非常少,其主體資格認定十分困難。,如此,司法機關囿于現有法律規定的不明確,防止群體性事件發生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等因素的考慮,往往不愿意受理此類環境訴訟。因此,導致了長期以來,農村環境糾紛的受害方是否對某一環境侵害者而言,具有原告資格一直是農村環境司法中的難題,使得大量的農村環境糾紛被阻擋在訴訟大門之外,難以立案。盡管在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八大四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規定“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于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7]但是,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改革的關鍵期,改革步入深水區,進入攻堅階段,各類社會矛盾頻發,尤其是農村地區群體性事件多發,且事件所涉及因素紛繁復雜,其中環境糾紛是其典型代表,人民法院如何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仍是一個有待實踐檢驗的難題。
(三)訴訟運行成本畸高農村居民負擔難
普通民事訴訟一審審限可為六個月,加上二審,有時可能啟動再審程序,加在一起甚或持續好幾年,在這一過程中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難以估量,尤其是對普通的農村居民維權者而言,更是“不可承受之重”。“遲到的正義非正義”,即便最后原告勝訴,仍需經過執行程序,執行難一直是困擾我國司法公信力的關鍵難點之一*執行難問題是影響我國當前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樹立法律信仰的關鍵點,法律要被信仰,則法律應該有實效,如何實現法律的效力,其司法裁判的執行首當其沖。故,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切實解決執行難,制定強制執行法,規范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加快建立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威懾和懲戒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勝訴當事人及時實現權益。由是觀之,將此類問題寫入十八大四中全會報告,作為重點問題,著力解決,可以看出該問題在我國現階段的普遍性與困難度。。此外,農村環境糾紛由于受到涉案當事人通常較多、取證困難、侵害結果難以評估等因素的影響,如果原告選擇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很可能陷入久拖不決的困局,其產生的后果,大致如下兩方面:其一,在這一訴訟過程中,環境污染危害的潛在性和長期性會逐漸加劇農村居民的健康損害和財產損失;其二,農村環境糾紛久拖不決會增加原告由此而付出的時間、精力、人力、財力等成本。
譬如,以農村地區水污染引發的糾紛為例,若得不到及時化解,致害方不采取有效治污手段消除污染危害,受害方繼續引水灌溉,如此輕則導致農產品收成減少,重則致使土壤喪失生產能力,使大片農田變為荒地,徹底毀壞農村居民賴以生存的“命根”。與此同時,水污染還會直接危害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近年來,不少農村地區疾病多發,尤其是社群型癌癥疾病的爆發,不得不說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在這類環境糾紛中,被告企業大可派代表參與訴訟,并不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然而,相對于作為原告的普通農村居民而言,其在一年之中要忙著播種、收割、銷售等,時間、精力、人力、財力等成本根本消耗不起。“裁判是一種很奢侈的糾紛解決方式,故欲讓所有的民事糾紛都通過裁判來解決的想法是不現實的”[8],這一點在農村環境糾紛上體現的尤為真實。
綜上,現行的以訴訟作為解決農村環境糾紛的主要方式的糾紛解決機制,由于其較強的對抗性、對環境糾紛訴訟主體規定的不明確以及訴訟過程的復雜和高成本等現狀,致使其暫不適宜農村社會現實,不利于農村居民人情社交關系的維系,難以滿足農村環境糾紛爆炸式增長的需要,在解決農村環境糾紛上明顯乏力。
三、建立我國農村環境ADR機制的現實基礎
為了及時有效解決日益增多的農村環境糾紛,推進環境正義,實現生態良好、生活富裕的新農村建設目標,有必要建立一套既能補足訴訟機制缺陷,又能與農村環境糾紛特點相契合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下簡稱ADR)。ADR起源于美國,最初主要用于解決勞動爭議,現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適用的訴訟以外的糾紛解決方式。同時,美國也是最早將ADR運用到環境糾紛解決中的國家,譬如,“斯諾卡爾米河流”和“風暴國王山脈和哈得孫河”案等,即是成功運用ADR的經典案例。事實上,在西方發達國家中,ADR在環境糾紛領域業已得到廣泛應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過對社會關系進行二次調整,來實現矯正的環境正義[9]。 這對改善我國在農村環境糾紛解決領域主要依憑訴訟機制而實施效果不佳的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價值。因此,有必要在借鑒其他國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探析環境ADR在解決我國農村環境糾紛上的現實基礎,以此為據構建適合我國特殊國情的農村環境ADR機制。
(一)農村環境糾紛發生的熟人社會影響
當下我國農村社會依然是一個鄉土氣息濃厚的“熟人社會”,農村環境糾紛中的污染者,不論是當地的民營企業或者鄉鎮企業,抑或農村居民個人,都是本村或鄰村的熟人。因此,即使發生了環境糾紛,鄉里鄉親之間亦希望能夠維持原有的親情鄰里關系。在這類社群中,居民之間大部分有著血緣親情關系,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里,少有人愿意撕破臉面,打碎人情去訴諸法庭。此外,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無訟”“厭訟”“息訟”等訴訟文化和觀念對廣大農村社群及其成員影響深遠,在今天,糾紛發生后仍有很多人不愿直接發生沖突,避免傷了和氣,希望采取非對抗性的協商、調解等方式來尋求糾紛的解決。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很多農村居民仍抱持這樣一種觀念:惹上官司是件極其麻煩的事情,能私了還是私了,寧愿吃點虧,也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基于此,對抗性的訴訟不符合農村實際,難以及時有效解決農村環境糾紛,而ADR這種以注重妥協而非強化對抗性,注重事后效果而非事前考察的糾紛化解機制,在解決農村環境糾紛過程中,更能滿足爭議各方的心理訴求,推動糾紛解決。
(二)農村環境糾紛處理的多元價值考量
農村環境糾紛中的污染者對農村環境的雙重影響,使得糾紛雙方難以“對薄公堂”。農村地區常常與貧困二字捆綁,農村地區對經濟發展的主觀欲求和客觀需求較城市地區更為強烈[10]。對有些農村居民來說往往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環境污染行為的利益驅動者,又是環境污染后的實際受害者。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在污染農村環境的同時,客觀上也增加了當地農村居民的收入,迎來了他們農畜作業之外的職業生涯“第二春”。特別是對那些土地大部分被政府征收了的農村居民來說,為民營企業或者鄉鎮企業工作成為其主要的經濟來源,“自己”如何反對“自己”。這類糾紛雙方間對立而又統一的矛盾關系,更是加劇了選擇訴訟解決糾紛的難度。一項“村民對中小企業的看法”的問卷調查顯示,只有24.9%的認為,它們污染了我們的村莊,表示反對[11],并且這24.9%的農村居民也不見得主動采取行動,更多的人采取的是一種“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搭便車的心態,尤其是那些受到污染者“恩惠”并缺乏環境保護意識的農村居民。但是,如果換一種糾紛解決方式,轉化糾紛處理的心態,弱化對抗性,強調妥協性與合作性,可能更有利于矛盾的及時解決。因此,環境ADR的適用,無論是協商、調解、仲裁,還是第三方裁決,以雙方合意為基礎,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糾紛雙方的針鋒相對,在給予受害者適當經濟補償的同時,又能兼顧致害方的利益的階段化實現,從妥協、合作、共贏的多元價值層面去化解農村環境糾紛。
(三)農村環境糾紛認定的專業技術運用
高速發展的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在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日益突出的農村環境污染。無論是發生在農村地區的轉移型污染、生產型污染,亦或日常生活環境下出現的生活型污染,在環境糾紛的處理過程中都需要專業性較強的環境知識和技術作為支撐,而大多數普通農村居民都缺少環境保護與治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往往出現舉證不能的情形。譬如,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該規定表明環境污染責任證明制度施行的是“舉證責任倒置”,但是,就損害事實的存在,并沒有予以規定,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訴訟原則,原告仍需證明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存在,這就給司法實踐中農村居民舉證環境污染造成直接損害造成了困難——環境損害的認定往往需要專業知識輔助,普通農村居民很難具備。此外,我國目前大多數法官的知識結構主要是人文社會科學,具備環境、資源等自然科學知識背景的法官為數較少。因而,法官在處理環境案件上也存在知識儲備不足的缺陷,這必然對其判斷案情、采信證據產生不利影響[12]。 針對環境訴訟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前述弊端,不斷發展的環境ADR在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參與人員具有多元性,這就決定了其在環境糾紛解決中能吸收兼具環境專業和司法背景的人士參與糾紛解決,客觀上有利于促進糾紛及時有效的解決。
四、我國農村環境ADR機制的運作構想
伴隨農村環境污染狀況的日益惡化,其類型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由此引發的糾紛亦越來越難處理,通過一般環境侵權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來解決糾紛時,已明顯感到乏力,無法有效兼顧公平與效率。因此,亟需針對農村環境糾紛的特點,建立便捷、高效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在提高糾紛解決效率的同時,保障糾紛解決的終局效果。通過環境ADR機制的建立,實現農村環境治理的良效與長效,減少訴訟對農村社群所尊崇的“鄉土人情”理念的沖擊,更好達成糾紛化解的終局性,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一)農村環境ADR推進的基礎在于農村環境自治能力的建設
環境ADR的功能在于促進社會自治與社會合作,是現代社會尋求以和諧方式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13]。 基于我國農村環境糾紛的特點以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筆者認為無論是選擇仲裁、協商、調解抑或第三方裁決,農村環境ADR推進的基礎都在于對農村環境自治組織及廣大農村居民環境自治能力的建設。在我國,農村社群及其成員雖然為數眾多,但是個體性強,呈現較大的差異性和離散性,期望以其個體成員的身份參與環境糾紛解決的效果甚微。“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由強出頭”是我國傳統的處世哲學,這句話用在描述我國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上十分恰當。
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是一項帶有明顯公益性和社會性的事業,與每一位農村社群成員利益攸關,但又不是非你不可,這就導致很多農村居民在糾紛解決中遇到問題很容易退縮,難以在受害方中形成一種向心力或是凝聚力,甚或在內部出現分歧,不利于糾紛的及時有效解決。要把村民廣泛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就必須按照村民的自愿和需要并在村民中發展各種形式的社區民間組織,使之成為聯接村級組織和廣大村民的載體和紐帶。但由于農村自治組織——村委會自治職能比較弱化,難以擔負起農村環境治理的大任,因此,農村環境自治組織及其自治能力在農村環境糾紛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正如有關學者指出:“要把村民廣泛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就必須按照村民的自愿和需要并在村民中發展各種形式的社區民間組織,使之成為聯接村級組織和廣大村民的載體和紐帶。”[14]而農村環境自治組織正是這種社區民間組織的一種,通過該自治組織的建立和能力培養可以及時發現本地區的環境問題,舉行形式多樣的自治會議,充分交流、通報各類環境信息,征求廣大居民意見,代表居民參與當地環境糾紛的解決,使其切實成為當地農村居民在環境糾紛解決上的自治體。
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居民是農村環境糾紛中的重要主體,解決農村環境糾紛絕不可能讓他們靠邊站。農村環境自治能力建設,天然地包括對農村居民能力的建設與培育,要充分積極發揮其積極性與主動性,激發其維權意識。具體而言,可由當地基層組織——村委會牽頭邀請當地有威望、有能力的人成立環境自治組織,必要時可以采取選舉的方式讓農村居民選出,能夠代表其行使環境權利的、有能力的其他居民作為小組成員。該小組設置一名組長,若干組員,組長負責召集成員進行小組會議,在必要時提議召開村民會議。該環境自治組織對內負責本村村民的生活垃圾的處理問題,有權設置垃圾回收處理站等環境基礎設施;處理本村居民間日常環境糾紛的協商與調解,對外代表本村居民與環境糾紛的解決。
(二)農村環境ADR推進的難點在于各個具體方式的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這些著名的法治名言都指示我們在分析和評價農村環境ADR機制的成效時,必須關注其實施,這也是影響我國農村環境ADR機制推進的難點。依照主持ADR的主體屬性和運行方式,可將農村環境ADR分為環境仲裁、環境裁決以及環境協商與調解,這也與我國現有的ADR資源相符。
1.環境仲裁。環境仲裁是指由環境仲裁機構根據環境糾紛當事人預先約定或者事后達成的仲裁協議或者仲裁條款,做出對雙方有利的裁決,雙方服從并且履行裁決內容,從而解決彼此環境糾紛的程序[15]。 在我國,尚處在起步階段的環境仲裁,能否作為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方式尚存在爭議。從實踐上看,全國各地少有將環境糾紛提交仲裁機構仲裁的案例。只是在2007年末,江蘇省東臺市在國內首家設立環境仲裁庭后,成功解決一樁長達十余年的環境糾紛案,改變了環境保護部門多年來對環境糾紛解決的單一手段的局面[16]。實踐證明,環境仲裁有其優勢——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費用低,程序簡,且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選擇仲裁庭的組成,有效避免了當事人對裁決的不信任。在借鑒東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農村環境糾紛的特殊性,可以對環境仲裁作出如下設計,以期有效解決農村環境糾紛,推進農村環境治理效果:
第一,依法在鄉鎮一級設立常設的環境仲裁機構,聘請人民法院派出法庭、鄉鎮司法所、縣環境保護局等機構的人員以私人身份加入環境仲裁機構,邀請社會公信人士、律師以及代表農村居民環境權益的民選代表等,共同參與農村環境糾紛的仲裁工作。這樣一來既能保證環境仲裁機構的多元性,又要體現環境仲裁的專業性,區別于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
第二,遵循環境仲裁庭獨立審裁的原則,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明確環境仲裁的受案范圍和仲裁程序。
第三,肯定環境仲裁“一裁終局”的效力,裁決作出后,除無效或者依法被撤銷外,對當事各方均產生約束力,確保環境仲裁的效力價值與效率價值。
第四,承認裁決書和調解書的法律效力,確保環境糾紛在仲裁后能得到有效解決。對無故違反有效仲裁文書的當事方,責令其承擔相應責任。
2.環境行政裁決。環境行政裁決是負責環境行政監管事務的行政主體或法律授權的社會團體和組織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對環境糾紛依申請進行審查,并在充分聽取涉案當事方陳述意見的基礎上做出裁決的行政確認行為,目的是解決因環境污染而產生的糾紛,有別于其依職權主動進行的調查、處理的行政處罰行為。行政主體或法律授權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一方面,擁有高素質的具備專業知識的調查人員,另一方面,擁有勘查、監測、取樣化驗等取證設備。因此,在信息收集、判斷上具有明顯優勢,使得糾紛解決的方案更加符合實際的訴求成為可能[17]。在這一過程中行政主體或法律授權的社會團體和組織均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來解決平等的爭議雙方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糾紛,類似于日常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與處理的行為,所作出的裁決屬當事方就民事責任劃分與承擔的一種專業認定。具體而言,農村環境行政裁決有以下幾點需要明確和完善:
第一,裁決的啟動與展開。環境行政裁決在致害方和受害方因環境污染與治理發生糾紛時,任意一方當事人均可向環境行政主體或法律授權的社會團體和組織申請環境行政裁決,受理后由專業人士進行調查并公開聽證,并依法做出行政裁決確認書。這里可發現,環境行政裁決與環境仲裁有著根本區別,后者必須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方可展開。
第二,裁決的主體。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較以前的舊法,增加了23條,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環境保護法。相較舊法只用一條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農業環境的保護(舊法第二十條)而言,明顯增加了對城鄉、鄉鎮及農村地區環境綜合治理的規定。譬如,新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農業環境的保護,第二款規定了縣級、鄉級人民政府應當提高農村環境保護公共服務水平,推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此外,第四十九條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農業等有關部門和機構應對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及其防治承擔指導、監督及管理,其第二款還規定了縣級人民政府負責組織農村生活廢棄物的處置工作。第五十條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在財政預算中安排資金,支持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生活污水和其他廢棄物處理、畜禽養殖和屠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農村工礦污染治理等環境保護工作等,其力度大大加強。第十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這里的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包括縣級人民政府,因此,建議縣級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在鄉鎮設置派出機構——基層環境保護所,授權其對農村環境糾紛責任認定依法作出行政確認。與此同時,建議通過行政立法授權那些專業性強、公信力高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依法作出準行政確認,一方面可以補足基層環境保護所在專業知識、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亦旨在嘗試將更多的公共服務社會化,營造社會公共服務競爭化的局面,切實推進農村環境糾紛的多元化解決。
第三,裁決的效力。從立法旨意和法律實施看,環境行政裁決是應該具有法律效力的,至少是法律上的證明力,至于是否對當事方產生直接的法律約束力,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和實踐。因為,該行為是經一方申請而啟動,對申請方當然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對相對一方是否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還需要從兩個方面考量:其一,若相對一方接受申請并參與公開聽證,其最終確認結果對其有約束力;其二,若相對一方拒絕申請,并不愿參與公開聽證,則確認結果并不直接約束相對一方當事人,但是,其對環境責任的認定和處理意見具有法律上的證明力,可供相關行政執法部門或人民法院采信。
3.環境協商與調解。環境ADR除仲裁和行政裁決或準行政裁決外,常見的方式就是協商與調解。協商指當事方在明確環境污染責任的基礎上,本著相互體諒的原則,簽訂協議或諒解備忘錄等文件,解決環境糾紛的方式。在協商過程中,若當事人能對環境糾紛達成一個較為理想的解決方式,自然是皆大歡喜。一般很多農村環境糾紛都是從協商開始的,只有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作為受害方的廣大農村居民才會去尋求其他的方法。理論上,協商的優勢在于糾紛當事人可以全程直接參與協商過程,簡單便行、目標明確,不需要第三方介入調停、斡旋、仲裁或裁判。但是,從實踐效果看,由于農村地區環境污染類型差異大,且因農村居民(包括是農村環境自治組織)對法律知識和協商技巧的缺乏,在協商中對環境污染的認定、責任的劃分以及賠償數額一般較難及時達成一致,影響了協商的效果。
調解是指在第三方的主持下,當事方對環境糾紛進行平等、自愿的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與訴訟不同之處在于,訴訟著眼于過去,而調解更強調未來,這樣調解協議對于仍想繼續保持某種關系,如商業關系或雇傭關系的雙方而言,尤為重要。”[18]對不斷增多的農村環境糾紛而言,調解有助于維護當地和諧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熟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在我國農村,調解主要包括民間調解和當地鄉鎮政府主持的行政調解。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調解與農村的傳統調解不同,需要遵循法定的調解程序和法治的基本原則,與法治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
第一,民間調解指無公權性質的民間機構或個人以調解為手段的糾紛解決方式[19],民間調解與協商的最大區別,在于民間調解通過無公權性質的民間機構或個人介入,而協商不存在第三方介入的問題。目前我國農村環境糾紛大多是民事糾紛,本身具有可調節性,可考慮充分發揮民間調解的作用。對農村環境糾紛言,通過鄉鎮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或農村環境自治組織調解環境糾紛,它們在處理農業環境糾紛時有其自身優勢,特別是在處理由鄉鎮企業或當地居民污染行為引起的小型環境糾紛上更為方便有效。
第二,行政調解是指由行政機構主持進行的調解活動。受專業知識的限制,在我國環境糾紛解決中最主要的調解類型是行政調解。調解程序由行政環境保護機構主持,在效果上可能優于協商和民間調解。與前述行政裁決相比,鄉鎮環境保護所可依職權,主動介入農村環境糾紛的調解,在尊重糾紛當事人意愿的基礎上,促使當事人盡快達成調解協議,督促致害方積極履行調解協議內容。
由于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還是一個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熟人社會”,而非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因此,現有的以訴訟為主的糾紛解決機制難以有效應對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亟需建立適應農村社會特性的環境ADR機制來彌補訴訟機制在解決農村環境糾紛上的不足。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除了要考慮糾紛及時有效的化解外,還應關注當事人事后的關系維護和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與嚴肅的訴訟機制相比,ADR機制更能長效與良效地解決農村環境糾紛。訴訟是解決糾紛的有效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特別是在農村環境糾紛的解決上,建議通過構建以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形式上的多樣性、解決過程的非對抗性為特征的環境ADR機制,為農村環境糾紛提供多元的解決途徑,切實維護底層農村居民的環境權益[20]。
[1] 陳兵.論法治視閾下我國農業工業化污染協同防治體系[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103-110.
[2] 李運福.農村環境司法保護的困境和出路[J]. 政法論壇,2014(3):11-15.
[3] 韓喜平.農村環境治理不能讓農民靠邊站[J]. 農村工作通訊,2014(8):48.
[4] 閆魏.論ADR機制在我國農村的構建——以浙江農村為例[J].遼寧行政學院報,2010(5):31-32.
[5] 李運福.農村環境司法保護的困境和出路[J].政法論壇, 2014(3): 11.
[6] 李栗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法律機制研究[M].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9.
[7]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
[8] 小島武司.訴訟制度改革的法理與實證[M]. 陳剛,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1.
[9] 曹明德,毛濤.我國環境爭端非訴訟解決方式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42-46.
[10] 王樹義,周迪.回歸城鄉正義:新《環境保護法》加強對農村環境的保護[J].環境保護,2014(10):29-34.
[11] 王俊敏.鄉村生態社區的衰變與治理機制:理論與個案[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187.
[12] 丁渠.我國環境ADR制度的完善[J]. 法學雜志,2011(4):135-137.
[13] 劉超.問題與邏輯:環境侵權救濟機制的實證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90.
[14] 唐建平,梅祖壽,劉明君.健全組織:擴大村民在社區治理中的公共參與[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104-108.
[15] 潘鳳湘.環境仲裁三種典型模式簡論[J].知識經濟,2012(11):15-16.
[16] 李玉芳,高杰.環境仲裁法庭顯身手——江蘇省東臺市首次環境糾紛仲裁紀實[J].環境經濟,2008(2):57-59.
[17] 丁渠.我國環境ADR制度的完善[J].法學雜志,2011(4): 135-137.
[18] 克里斯蒂娜·沃波魯格.替代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ADR)[J].河北法學,1998(1): 58-59.
[19] 徐忠麟,李杏.農業環境糾紛的多元化處理機制探討[J].安徽農業科學,2011(28):17 673-17 675.
[20] 孫文中.底層視角下的農民環境維權[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128-137.
Construc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ADR
CHEN Bing
(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 large 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aggregation type field of rural life and so on caused deteriorat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frequently occur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disputes. The current procedure oriented dispute resolutions which mainly rely on the civil litigation to solve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n rural areas are not effectiv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new mechanism, ADR for environmental disputes to solve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so as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tect effectively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rural dwellers.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ura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ADR for environmental disputes;non litigation mechanism
2014-10-10
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國際學者交流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14T70274;2013M53096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項目(10YJC820003);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014B3);吉林大學首屆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資助項目
陳兵(1980—),男,吉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吉林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國際學者,首爾國立大學亞太法律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法、競爭法。
F325.2
A
1009-9107(2015)05-01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