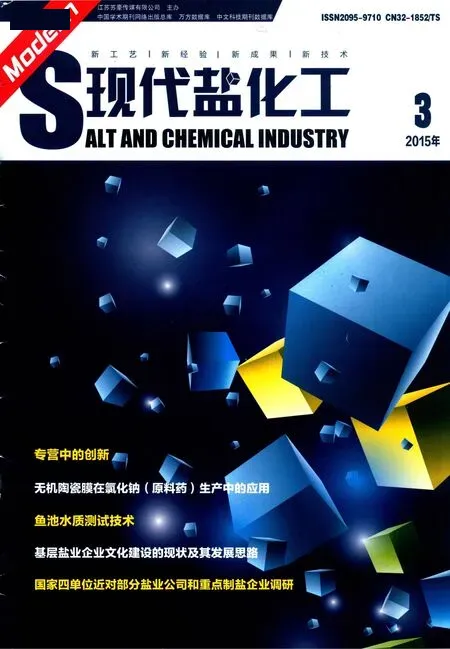我國宋代溫州鹽業(yè)發(fā)展考究
唐黎標
(杭州市食品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溫州宋代鹽業(yè)生產(chǎn)從起步到發(fā)展,鹽業(yè)流通中所融注的榷賣與鈔引形式推動著溫州宋代鹽業(yè)的發(fā)展,鹽利作為商品因子早在這一時期就推動著溫州經(jīng)濟的發(fā)展。溫州宋代鹽業(yè)的發(fā)展脈絡顯示,我國鹽業(yè)生產(chǎn)流通中的商品經(jīng)濟遠比某些西歐國家早得多。溫州宋代鹽業(yè)買賣與流通現(xiàn)象中出現(xiàn)的中國封建官府對商品經(jīng)濟的某種社會效益,并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本文試就溫州宋代鹽業(yè)的發(fā)展脈絡談點管窺之見。
1 北宋前期沿襲榷賣制輔以鈔引鹽分銷
因地處我國東南沿海,溫州鹽業(yè)鹽法漢代以前無考。相關資料顯示,溫州自唐以來就開始重視鹽業(yè)生產(chǎn)流通稅制管理。唐乾元初置永嘉監(jiān)鹽官[1],開始鹽業(yè)流通專賣管理。光緒《永嘉縣志》卷五《貢賦·鹽法》也提到:“唐宗室李谞為永嘉鹽官,而吾郡始有鹽。”后設立鹽業(yè)機構(gòu)、免稅亭戶,鬻者以法的管理制度也提上了議事日程。《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四》更是明確記載:“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yè)鹽者為亭戶,免雜徭。鹽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唐鹽鐵使劉晏實行鹽政改革以后,至唐大歷年間更是出現(xiàn)了“十監(jiān)當百余州之賦”現(xiàn)象[2],而溫州(永嘉)即在十監(jiān)之列。
宋初溫州鹽業(yè)管理延續(xù)唐朝榷賣制發(fā)展,出現(xiàn)了天富南北監(jiān)及密鸚、永嘉二鹽場,鹽業(yè)規(guī)模及產(chǎn)量也得到了提升。據(jù)乾隆《平陽縣志》卷六《貢賦·鹽政》載:“唐劉晏始有永嘉等十監(jiān)之名。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為鹽丁之額。吳越仿之,宋不改。宋置溫州天富南北監(jiān),而平之鹽政始此。”宋至道末年溫州天富南北監(jiān)及密鸚、永嘉二場鹽業(yè)產(chǎn)量達七萬四千余石,與當時鹽業(yè)生產(chǎn)歷史名場杭州場等量齊觀。《宋史》卷一八二《食貨下四·鹽中》:“(至道三年)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余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jiān)二十萬一千余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余石,溫州天富南北監(jiān)、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余石,臺州黃巖監(jiān)一萬五千余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衡、嬰州。”其中“以給本州及越、處、衡、嬰州”,就是輔以鈔引鹽分銷方式供給浙江內(nèi)地的依據(jù)。
2 北宋中期榷賣與鈔引在互為主次的變異中反復不定
宋天圣年前尤其是大中祥符四年后,河北、山東等地發(fā)生蟲災和水災,并有饑荒。此時,北宋財政的困難局面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三司使丁謂要求停止一些地方賦稅,宋統(tǒng)治者出臺了一些減免賦稅的措施,無形中也挫傷了鹽官管理積極性,但海鹽生產(chǎn)流通中的商品色彩逐漸顯現(xiàn),無形中加大了鈔引鹽甚至是私鹽的分銷流通功能。天圣年間溫州鹽業(yè)出現(xiàn)管理者疏于管理而欠稅較多的現(xiàn)象。“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封者言:溫州天富南、北兩監(jiān)自大中祥符四年后,逐界積欠鹽課甚多,所差使臣多不用心,今請依杭、秀州例,下三司及制置轉(zhuǎn)運司舉三班使臣或州縣職官監(jiān)當。從之。”[3]說的就是這種社會效應。溫州鹽官疏于管理,鹽稅欠課較多,無形中促進了鹽業(yè)產(chǎn)量的提高,也促進了溫州鹽場的進一步發(fā)展。由于商品利潤的出現(xiàn),商品流通色彩進一步加劇,也因此天圣年中溫州鹽業(y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了溫州鹽業(yè)史上的“一監(jiān)三場”局面。《宋史》卷一八二《食貨下四·鹽中》載:“天圣中,杭、秀、溫、臺、明各監(jiān)一,溫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這里的“溫監(jiān)一”即天富南北監(jiān),“領場三”疑即雙穗、密鸚、永嘉。[4]
由于位處東南沿海,史上蠻夷之地成分較濃,商品因子一旦被激活,其商品利潤及流通領域便被擴張。北宋中期,只要官府榷賣制有所削弱,與東南沿海一樣,溫州的鈔引鹽分銷甚至私鹽交易就極為活躍。宋熙寧年間,溫州與杭州一樣出現(xiàn)了鹽價苦高的現(xiàn)象。“熙寧以來,杭、秀、溫、臺、明五州共領監(jiān)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眾,轉(zhuǎn)為盜賊,課額大失。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西浙之溫、臺、明斤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5]這說明宋熙寧以來,由于官府加強了管理,在榷賣制與鈔引制主次變異中,溫州各鹽場得鹽最多,名噪一時。“熙寧五年,以盧秉權發(fā)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灶戶鬻鹽,與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灶戶益困。秉先請儲發(fā)運司錢及雜錢百萬婚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shù):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款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并海而東,為越州余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為十分。蓋其分數(shù)約得鹽多寡而為之節(jié)。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為最多。”[6]兩浙提點刑獄盧秉權的鹽業(yè)管理,彰顯出北宋中期溫州鹽業(yè)概況。乾隆《平陽縣志》卷六《貢賦·鹽政》也有佐證:“熙寧五年定諸場得鹽分數(shù),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為十分,立溫州檢校批驗所。”也正是宋中期榷賣制與鈔引制互為主次的變異使得溫州鹽場鹽業(yè)產(chǎn)量逐漸得以提高。
3 北宋后期鈔引制替代了榷賣制的主導地位
隨著鹽業(yè)的發(fā)展,宋代鹽利不僅在中央財計中占居很高的比重,而且,在地方財計中也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至少北宋后期在許多時期和相當大地域的路州,鹽錢是漕計、郡計的主要利源。北宋中后期朝廷不僅認識到鹽業(yè)在通商中的利潤率,也認識到鹽業(yè)商品流通讓利于民,是朝廷拽奪地方財計的有效手段,崇寧初出現(xiàn)的“罷官賣鹽”讓利于鹽民,正是鈔引制逐漸替代榷賣制的典型表現(xiàn)。《宋會要輯稿》(第6冊5 226頁)載:“宣和七年二月六日詔曰:‘崇寧初罷官賣鹽以利天下,立法修令,走商賈于道路,惠及百姓,行之二十余年,客人有倍稱之息,小民無抑配之害。’”實施鈔引制之后,溫州的鹽場數(shù)又有增置。史料記載,政和年間溫州又置長林鹽場,就是這一發(fā)展趨勢的體現(xiàn)。“宋,樂有天富北監(jiān)。政和間,又置長林場(元、明皆因之。南渡后,屬槽司(《隆慶志》)[7]”,這應該是鈔引鹽分銷制加強后,溫州出現(xiàn)鹽業(yè)擴大再生產(chǎn)的社會效應。此外,宋宣和年間的詔令,也體現(xiàn)了這一效應,“去歲措置新價文鈔務濟亭戶,以便商賈”,并且“鹽倉用新鈔對帶舊鹽舊鈔,兩浙已降指揮,令揭往溫、臺州請鹽”,“兩浙令揭往溫、臺州請鹽,仍每州除全用新鈔外,日支所帶新舊文鈔,共不得過一千五百貫,更不加饒。庶新鈔各無坊闕,余依見行條法”[8]宣和七年,朝廷為促進溫州鹽業(yè)商品流通,更是層層加碼。“是年三月十八日尚書省言,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旨:客算溫州鹽,每十袋增給一袋”。[9]
資料顯示,宋代鹽利在國家歲收錢數(shù)中的比重,不僅呈漸增之勢,而且還以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為最多,其最高比率44%,的確近半。[10]鹽利在朝廷和地方歲計中如此重要,中央和地方爭奪鹽利的沖突便勢不可免。北宋后期溫州鹽業(yè)從官府榷賣轉(zhuǎn)向鈔引鹽制,正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鹽利控制的加強趨勢。
4 南宋鹽業(yè)從供不應求到私販成群再到供過于求
南宋時期的海鹽收益,在財政歲收中越發(fā)突出。按高宗紹興十二年的說法,“今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這“國用”,是指朝廷當時的實際收支,不包括地方未送繳中央的“贍軍”錢財。而溫州鹽場大都在近海之濱或海島上,隨著北方戰(zhàn)事吃緊及鈔引鹽法的進一步強化,溫州恰逢天時地利順勢成為南宋鹽業(yè)生產(chǎn)最為重要的生產(chǎn)基地。
建炎年間,浙東南溫州及臺州海鹽出現(xiàn)供不應求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朝廷南遷,淮鹽道路不通,貿(mào)易困難。據(jù)史料記載:“建炎四年二月十九日尚書省言:近緣淮鹽道路不通,諸邑人自京師帶到鈔引前來兩浙請鹽,致應副不起,內(nèi)溫、臺州積壓鈔引數(shù)多有至三二年以后方當支請鹽貨。契勘廣南、福建兩路鹽貨歲出浩瀚,已許通商,訪問客人皆愿算,請令相度應。溫、臺州鹽倉不曾支鹽,令出給公據(jù),揭取鈔引,連粘付客人前來行在榷貨務,換給廣南、福建路鈔引,每一百貫馬支換廣南鹽鈔六十貫,福建鹽鈔四十貫。從之。”[11]這一供不應求局面的出現(xiàn),與高宗跨海遁跡,或駐足臺、溫一帶有關。“建炎四年正月,高宗逃至明州,又一度跨海遁跡,或駐足臺、溫一帶。鈔客們也紛然聚向浙東支鹽。一時投向溫、臺州的鹽鈔,……而印鈔換錢的事,又須臾不可停頓;于是,高宗破例開放閩廣鈔鹽進入淮浙鹽區(qū)。其辦法是,商人們在越州交錢買鈔,去廣東、福建支鹽,販至江浙荊湖來賣;或者,每袋交納3貫‘通貨錢’,辦理浙鈔的‘轉(zhuǎn)廊’手續(xù),即‘令行在榷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算請’”。[12]有時,“甚至允許用糧食換鈔[13]。”此外,從建炎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詔亦可以看出,朝廷為解決溫、臺鹽業(yè)供不應求所做出的努力,也證實了南宋初年溫州海鹽供不應求的史實。
淳熙年間,由于溫州海鹽供不應求,而事實是官鹽常貴,私鹽常賤,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我們可以從《朱子大全集》文十八《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之《朱子奏議》一文中證實:“浙東四州濱海……販私百十成群,大船搬載,巡尉不能呵,州郡不敢潔,反與通同,資以取利。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溫、臺全不成此第,民間公食私,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jiān)累月不收一袋、不放一袋者。”時值朱熹為兩浙鹽提舉,故有此奏。紹興年間,樂清尉吳明可嚴厲劾免鹽越境者,從另一個時間段證明了溫州海鹽供不應求中確實出現(xiàn)了私販成群的局面。《朱子集》八十三《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之《吳明可樂清之政》載文即是實例:“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溫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yè),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yè)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整之耶”。
海鹽生產(chǎn)一旦盲目以逐利為誘導,便逃脫不了商品流通的陷阱,南宋末年溫州海鹽出現(xiàn)大量積壓,便是商品供過于求現(xiàn)象的生動表現(xiàn)。紹興末年溫州有產(chǎn)鹽“十九萬石”的記錄。[14]當然《宋會要輯稿》(第6冊5255頁)所輯,更有溫鹽積壓的情狀陳述:“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九日浙東提鹽都潔言,溫州歲出鹽三萬五千余袋,而支發(fā)止及一萬五六千袋。緣本州水路多由海道,陸路則經(jīng)涉山嶺,自來客人少肯前來請販,致諸場積鹽數(shù)多。欲乞今后客人支請溫州鈔鹽,如指本路州、縣住賣者,每十袋加饒一袋,若指別路州、縣住賣,每十袋加饒二袋,庶幾鹽可發(fā)泄。候支發(fā)通快日,依舊榷貨務看詳。欲權依所乞,候降指揮到日,立限半年加饒。若只于本州、縣住賣及今降指揮之前,客人已算鹽鈔,更不加饒。從之。”
溫鹽積壓,除了盲目生產(chǎn)之外,亦與溫州商貿(mào)鹽道艱辛及溫州以外鹽業(yè)生產(chǎn)的逐漸正常有關,在此不作敘述。當然,之后的宋隆興初溫州“鹽展限加饒給賣”,宋乾道間溫州罷置州倉,宋淳熙初溫鹽積剩減額并灶,宋嘉定間裁減溫州鹽官,均是溫州積鹽的賣鈔鹽的謀求出路與改革需要罷了,改變不了溫州鹽業(yè)發(fā)展的總體脈絡。
[1]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五·江南道》.
[2]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溫州古代經(jīng)濟史料匯編》,330.
[3] 《宋會要輯稿》第6冊,5 191.
[4] 民國《平陽縣志》卷十四《食貨志三·鹽法》.
[5] 《宋史》卷一八二《食貨下四·鹽中》.
[6] 《宋史》卷一八二《食貨下四·鹽中》.
[7] 光緒《樂清縣志》卷五《田賦·鹽法》.
[8] 《宋會要輯稿》第6冊,5 524.
[9] 《宋會要輯稿》第6冊,5 227.
[10] 人民出版社《宋代鹽業(yè)經(jīng)濟史》,697.
[11] 《宋會要輯稿》第6冊,5 232.
[12] 《要錄》卷三一.
[13] 《宋會要·食貨》二六之七.
[14] 《宋會要輯稿》第6冊,5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