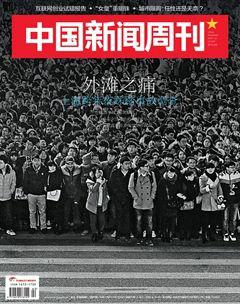如何破解“東北經濟告急”
王全寶+陳嘉林
2014年前三個季度,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GDP增速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位居最后五位,其中,黑龍江省以5.2%的增速墊底。去年東北三省經濟頹勢廣受社會輿論關注。
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東北三省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明顯下滑,經濟頹勢有增無減,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轉型,成為東北三省老工業基地共同面臨的難題。
事實上,東北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問題,早在十年前已經引起關注。2003年,國務院成立了“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負責協調東北三省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該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以下簡稱“東北辦”),具體承擔領導小組的日常工作,屬于正部級單位。
2004年5月,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的宋曉梧,調任東北辦副主任。在此任職期間,宋曉梧幾乎走遍了東北三省大大小小各個地方,對于東北經濟轉型問題,他不僅是研究者更是實踐者。
1月6日,宋曉梧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談及東北地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他指出,“東北三省經濟轉型不僅是經濟結構單一的問題,還有當地人思想上計劃經濟思維根深蒂固,很多人不相信市場的作用,包括有些官員在內。”
“投資在東北經濟增長中已經占比過高”
中國新聞周刊:國務院第28號文件中提到,要解決東北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機制性矛盾。你怎么看東北現在面臨的問題?
宋曉梧:我認為,東北地區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比較強的計劃經濟思維,而且對GDP的增長過分看重。GDP是個流量,而財富是存量,GDP增長不一定能形成財富。中國的財富積累比GDP增長要低很多,所以,雖然我們的資源、能源消耗那么多,但很多都浪費了。
我其實是一直堅決反對“保8”這種說法的。有人說,保證GDP增長在8%左右是為了保障就業,但哪個經濟學家、哪段經濟史能證明只有8%的GDP增長才能夠保證就業呢?
為了保證GDP的增長,錢都投資到拉動GDP高增長而就業低增長的行業,比如重化工業、高鐵建設、大型廣場、主題公園等,這些對經濟發展確實有一些好處,但對于解決就業作用并不是很明顯。我特別分析比較過中外在一、二、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如果假設歐美國家的就業彈性為1,那么我們就是0.1左右,所以在GDP增速降低后,就業也不會受太大影響。
振興東北不應僅要求GDP增長要高于全國。如果GDP增長了,但城鄉差距沒有縮小,基尼系數沒有縮小,產業結構也沒有調整,就不能說振興東北成功了。
東北振興應該以就業作為第一衡量指標。西方國家宏觀調控最早提出的就是保就業,比如法國,在推行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時成立了國土整治行動組,夕陽產業調整、職工安置、產業轉移和接續替代產業的引進,他們工作的第一重點就是就業和社會保障,第二才是工業項目,第三是金融融資。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東北三省都在加大投資力度。在你看來,加大投資對于東北是否是一個好的出路?
宋曉梧:目前投資在東北經濟增長中占比已經過高,東北三省前三季度GDP是37908億元,其中投資就有35000多億元。投資解決不了長期的問題。中長期問題的解決,還是要著眼于體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要創新。在出口和消費方面,東北提高不了多少,如果一定要當年見效,確實只能依靠投資。但是,投資已經比重太高了。如果非要投資也可以,但一定要投資到第三產業,一定不能再為了GDP的增長而投資。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國家提出進入經濟新常態,在這個背景下,如何看待東北的經濟發展問題?
宋曉梧: 我認為,東北地區經濟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過程中必定會經歷的痛苦,全國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只不過是在東北表現得更為突出。
中國經濟前一階段的發展是以過多消耗能源為代價的,萬元產值的能源消耗遠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更高于發達國家水平。同時還造成了環境污染,高增長伴隨著高污染。另外,勞動力成本被壓得過低。假如說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常態,就必須有效益的增長、低能源消耗、良好的環境和財富的合理分配。
“東北辦在2007年制定了整個東北振興的規劃”
中國新聞周刊:東北地區的經濟轉型嘗試從10年前就已經開始,東北辦也是那個時候成立的。當初成立東北辦,有什么考慮?

(資料圖片)宋曉梧。圖/CNSPHOTO?
宋曉梧:其實,中央在實施振興東北戰略之前,先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障試點,目的在于解決國有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是朱镕基當總理的那五年,實行了大規模的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為后來國企脫困起了很大作用,但其中有一條是減人增效,而東北的國企所占比重很高,2003年東北三省國企占比都在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這樣就導致下崗職工壓力非常大。由于當時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太健全,很多老職工發不出工資,導致東北發生了多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比如像葫蘆島楊家杖子群體性事件,沈陽的鐵西區工人上街示威等等。所以在2001年左右,為了解決東北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發不出養老金等問題,中央開始以遼寧省作為試點,逐漸向全東北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
后來,在落實基本社會保障的基礎上,國務院于2003年正式作出振興東北戰略部署,成立了東北辦,一直到2008年3月,東北辦并入發改委,成為振興東北司。
中國新聞周刊:東北辦成立后,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宋曉梧:針對東北的問題我們抓了幾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東北國有企業改革。當時東北國企比例過重,民企發展不夠,是最晚走出計劃經濟的。東北地區市場導向的改革比較慢,政府主導和國企占了很大分量。這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過程相對粗糙,有些環節沒有履行必要的程序,典型的例子就是通鋼集團的改制,職工代表大會沒有開,結果鬧出很大的事情。但總體來說,東北經濟結構的調整,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國企比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但即便如此,這個比例在全國來看還是比較高的。
第二項工作是抓對外開放。東北地區開放和東南沿海的開放特點不一樣,東南沿海的開放主要面向外國,吸引國外的資金、管理經驗和技術,而東北主要是對內開放,希望吸引國內民營企業到東北投資。當時東南沿海像溫州等地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私人資本,我們把這些地區的商會引進到了東北的幾個大城市。
當然我們也希望對國際開放,由于東北亞地區的環境特點,東北對外主要面向俄羅斯、韓國、日本,我們原打算建成“南有深圳、北有圖們江”的經濟發展格局,但由于離朝鮮太近,朝鮮核試驗惡化了當地的投資環境,這一計劃就沒能實現。
不過,當時的對外開放也確實吸引了相當一批大型外企進入,例如大連機床廠和美國、德國開展了合作,哈爾濱量具刃具廠和德國開展了合作,一汽集團和德國大眾開展合作,哈飛和巴西支線飛機的合作也都有進展。
我們曾專門組織港澳企業家到東北去尋找投資項目,但真正由港澳企業家投資的大項目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他們主營的是金融、旅游等第三產業,與東北的產業結構不是特別匹配。
我們做的第三件項工作是處置地方企業不良資產。東北在這一方面有特殊原因,其不良資產的形成主要是政府行為。當初國家號召要搞“十個大慶”,這就需要十個大慶的設備,所以東北企業都投入到設備生產中去了。后來說這是“洋躍進”,不能搞了,這批設備就積壓了下來,這是一筆歷史賬。
剛才提到的是國有企業的問題。而在民營企業方面,問題主要在于融資難。我們在2004年針對東北企業融資難問題召開過會議,有代表指出,中國金融生態最好的板塊是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快而且信譽度高,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較快、信譽度較低,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信譽度高,而東北地區則是經濟發展差、信譽度還低。后來東北辦組織了長城、華融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調查東北企業不良資產狀況,并且聯合開發銀行和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發起成立了東北中小企業再擔保公司。
再擔保公司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再擔保難的問題,但并沒有完全解決,這與銀行體系的一些管理辦法和金融市場的配置有關。
第四項工作是推動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這項工作起步相對較晚,2004年開始著手調研,2007年國務院正式出臺了文件。東北資源型城市在全國看來是開發較早的,因此枯竭也較早,像剛才我提到的下崗工人群體性事件主要就發生在這些資源枯竭型城市,例如楊家杖子的鉬礦、撫順的煤礦等。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東北地區未來的發展,當時東北辦有沒有整體的規劃?
宋曉梧:東北辦在2007年推行了整個東北振興規劃的制定。當時,對東北的戰略位置、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的主要定位和其自身區域配置等都做了明確的規定,提出建成“四個基地、一個屏障”。
四個基地是指能源及原材料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商品生產糧基地和科技創新基地;一個屏障指生態,要建成以大、小興安嶺及呼倫貝爾大草原為主體的北方生態屏障。在東北區域內部,我們按照其“三縱四橫”的地理特點,規劃了交通線路,加強鐵路、公路的基礎建設,打通區域構架。
為了制定整個東北振興規劃,我們前期做了十一個小規劃,有交通規劃、能源規劃、裝備制造業規劃、文化規劃和社保規劃等,最后統合在了一起。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針對資源枯竭型城市,主要研究了哪些方面的問題?
宋曉梧:其實,最初我們并沒有形成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概念,這部分問題都放到國企改革議題中去了,但后來在實際操作中發現,這已經不是單個企業的問題,就像撫順已經不是龍鳳礦的問題,而已經是一個城市、地區在面臨資源枯竭時所產生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包括就業、貧困、社會治安等方方面面。
棚戶區改造就是從資源枯竭型城市開始的,2004年我到撫順的棚戶區調研,當時的景象觸目驚心。當時改革開放已有時日,部分大城市已經非常發達了,但棚戶區里有十幾萬人集中連片地居住在低洼地區,房屋破舊,沒有上下水,缺少公共廁所。當時計算平均79戶居民擁有一個公共廁所。

黑龍江省雞西市的一處洗煤廠。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過程中會經歷一段痛苦的時期,東北地區會遇到這個問題,全國各地也會。
我們把棚戶區改造作為緩解資源枯竭型城市社會矛盾的突破口,但當時在國務院的立項過程非常艱難,爭論的焦點在于如何定義棚戶區這一概念,是以居住面積作為標準,還是以破爛程度作為標準?最后,我們把項目細化為中央下放煤炭企業集中連片棚戶區的改造,才最終成功立項。
當然,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還包括很多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的工程,像德國魯爾區、法國的蘭斯-貝加萊地區,已經轉型了六十多年都不敢說轉型到位,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就見成效。
“大家都愿意去做當年就見效的事”
中國新聞周刊:黑龍江省對于其經濟增速低迷的解釋是能源價格走低。這些年來,東北辦有沒有幫助東北進行規劃,以改變產業結構單一的局面?
宋曉梧:有的,2007年我在伊春召開了全國資源型城市發展旅游業的會議,有資源就有山,有山就有風景,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有文化的。焦作就是資源枯竭型城市,后來依托云臺山發展旅游業,收入比煤礦收入高出很多。我們當時強調的就是,各城市要根據自身情況發展接續替代產業,如果礦產剩余可采儲量是充足的,那就可以延長產業鏈繼續生產,但如果只有三五年的可采儲量就不要繼續開采了。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提出發展接續替代產業后,地方政府是否認可?
宋曉梧:地方政府還是認可的,國務院也出臺了相應文件,但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一些短期行為在其中起作用了。很多地方礦產的剩余可采儲量也就是三五年,但地方政府的市長、書記任期也大多不到三年,所以很多人就認為,在他任期內的這三年還能繼續開采礦產,至于四五年后的事情就根本不管了。如果去興建過去沒有的產業鏈,等產出效益時這個官員可能就不在任了,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做當年就見效的事,這就是干部任期制和經濟發展長期存在的矛盾,這不僅只存在于東北,而是全國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