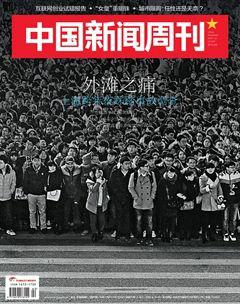中美教育哪家強
趙勇
美國俄勒岡大學教育學院全球與在線教育研究所所長,著有《誰怕大猛龍:為什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好(又最差)的教育體制》 一書
中美教育之間的相互關注度一直在上升,但全球教育中首先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問題,所以非常難回答“哪種教育模式更好、哪種更差”。
比較教育的優劣,首先要看教育的目的,此外還要看衡量標準。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掌握人類已有的知識(尤其是幾個特定學科的知識)、培養整齊劃一的人才,那么,中國等東亞國家的教育應該比美國教育的效率高得多。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在多項國際性考試(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PISA考試)中的排名往往都是中等偏下,而東亞國家學生則名列前茅。這促使美國政府開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來趕超亞洲國家。
近幾十年來,美國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大趨勢就是模仿東方,聯邦政府不斷參與到教育的過程中——增加考試、推行統一課程標準、不斷加強聯邦政府對教育的干預權。2001年,布什政府發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開始用聯邦政府經費來控制教育。規定各州的中小學必須統考,分類看成績,三年不達標要整改,從而推動各州實行統一考試和統一標準。奧巴馬最大的教育改革措施就是推廣“通用核心課程標準”和統考,迄今已有43個州參與。同時,鼓勵教師績效與學生分數掛鉤。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教育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考試成績上一直表現不佳,但是這并不妨礙它是全球創新性領先的經濟體,其在創新產業方面一直有強勁的發展。而包括日韓在內的亞洲國家雖然教育比較發達,但是引領的行業較少。迄今美國還是公認的極具創新力的國家,因而不少人認為,美國的教育體制長于培養創新人才。
從歷史上看,全世界的傳統教育走的都是同一個范式,即培養大批有專業技能的標準的雇員,而不是培養有創新能力的人。西方工業化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消滅個性、塑造共性的過程。
實際上,美國教育也沒有刻意培養創造力,學校沒有設置創新能力培養課程。可以說,美國創新人才的涌現是美國教育作為傳統教育“失敗”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是“事故”,而不是人為的設計。創造力是與生俱來就有的,教育和文化可能增強、也可能削弱創造力。注重整齊劃一的教育鼓勵順從、聽話的學生,獎勵對已有知識的掌握,懲罰甚至排除叛逆或者不順從的學生,這樣的教育越成功,創造性人才就越少。
美國教育的“事故”來自其教育的地方化。美國聯邦憲法規定教育為各州自己的事務。美國的教育起源于民間,最早就是由各地鄉鎮辦的,由當地自己收稅、管理,后來成為學區。學區的概念在美國非常重要,在很多地方是完全獨立自主的部門。學區的目的就是服務于當地社區。美國曾經有十幾萬個學區,相當于十幾萬個獨立的教育系統,經過上世紀大規模合并后現在還有14000多個。
學區多、地方自治,在這種情況下多樣性自然就產生了,導致沒有辦法有效貫徹統一標準:各地、各校甚至各個教室的教學內容;對學生的態度和要求;追求的教育目標都可能不一樣,不聽話的學生“漏網”的機會大大增加,無意中讓創造性人才有了生存空間,同時,與集中的教育體制相比,也很難用某幾個標準的學科成績來評價整個學生群體。
此外,美國文化不是以單一標準來論成敗,而是鼓勵學生追求自己的專長和自己定義的成功。例如,美國對于肄業生的容忍度較高,眾所周知,比爾·蓋茨、喬布斯和扎克伯格等都是輟學創業的。因此雖然美國學生在國際測評中成績往往低于亞洲孩子,但是在信心方面他們卻遠遠超過亞洲人,而創造力是需要信心的。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文明的消亡不是來自謀殺,而是自殺。美國幾十年來教改的方向則近乎自殺。近年來,美國青少年的創造力已經開始下滑。好在學界和政界已經對標準化、考試化、集權化的教改方向開始反思。有幾個州已經或正在決定退出“核心課標”,民間對其支持度也大大下降。
從傳統范式上說,中國教育是成功的。然而,教育的功能不在于彌補弱項,而在于發揮強項。文化和教育是相互促進的,美國的移民文化促進了其教育的多元化,同時也帶來了差異大的弊端。而中國深受統一模式的束縛,應該更加強調個體化培養,發揮每個學生的潛力。
21世紀是創新驅動的世紀,全球教育都必須轉型,從就業導向教育轉向創業導向教育。目前,中國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面向未來的。現代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國際視野、創造力和創業精神的人,中國教育的走向不應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同樣的人,而應把每一個人都培養成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