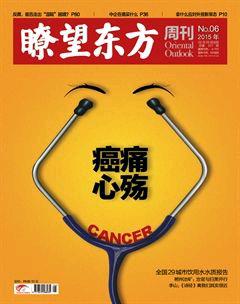癌痛何時休
呂爽

2012年3月5日,上海普陀區石泉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位老人正躺在病床上。 該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舒緩療護項目試點單位之一
“20年以后我們可以讓中國的癌癥病人不痛苦。”多年前,著名的腫瘤外科醫生李同度教授對當時還是學生的姚陽說。
“可是20年后,中國的癌癥病人確實還在痛。”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腫瘤內科主任醫師、教授姚陽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疼痛的病人往往很絕望”
“你知道為什么一些癌癥患者會去跳樓嗎?是因為太疼了。疼痛的病人往往很絕望,疼痛會使患者抑郁、恐懼、易怒,不配合治療。” 姚陽說。
20世紀8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曾提出:到2000年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讓腫瘤病人不痛”的奮斗目標。但遺憾的是,在晚期癌痛治療領域,癌癥病人目前依然未能遠離疼痛。
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長征醫院曾對上海七個區約8000名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進行了調查研究,該項調查發現,對患者來說,疼痛的殺傷力最大。許多患者反映,疼痛就像惡化信號,吞噬著生的希望,內心的焦慮和抑郁如影隨形。
“癌痛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癌癥疾病給患者帶來的疼痛,另一方面是治療給患者帶來的疼痛。”姚陽說。
1986年,姚陽正式成為一名腫瘤科醫生,從醫30年的經歷也讓他看到了中國醫生對于癌痛認識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我國還沒有中長性的止痛藥物,癌癥病人有的會打杜冷丁。一針杜冷丁,只能緩解兩個小時的疼痛。”姚陽說。杜冷丁副作用很大又不能長時間緩解疼痛,當時控制極其嚴格,“每個醫生手上只有一點點”。
杜冷丁的使用可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癥狀,導致煩躁、焦慮及癲癇發作,而杜冷丁的鎮痛作用僅為嗎啡的1/10~1/8。
那時候的癌癥病人個個痛,天天痛。
“那個階段,醫生主要關注癌癥病人的手術、放化療,關注腫瘤疾病的治療,而對癌癥給患者帶來的癥狀不太關心。貧血、乏力、疼痛、惡心,癌癥患者都這樣,也沒什么藥物。”姚陽說。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了一輩子外科醫生,已經七十多歲的李同度教授開始在全國奔走,把世界衛生組織早在1986年就已經發布了的《癌癥三階梯止痛治療原則》介紹到了國內。
1993年5月14日,當時的中國衛生部發布《癌癥三級止痛階梯療法指導原則》,包括以下五個基本原則:首選無創(口服、透皮等)給藥,按階梯用藥,按時用藥,個體化給藥,注意具體細節。
“對于癌痛,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是逐漸認識和了解的。”姚陽說。控釋、緩釋型的嗎啡制劑進入國內后,給癌痛患者帶來些許幫助。
擔心“成癮”
1999年和2007年,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曾開展了上海癌癥疼痛現狀調查和上海醫師對癌癥疼痛的認識調查。
1999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有86.2%的醫師認為病人怕成癮未按時用藥,而患者怕擔心成癮而盡量不使用止痛藥者為52.2%,兩者之間的明顯差距是——醫師更怕“成癮”。調查中還發現,1999年仍有13.5%的患者使用杜冷丁來緩解疼痛。
2007年的調查結果顯示,42.4%的患者認為服用止痛藥會成癮,25.5%的患者認為不會成癮,32.1%患者答“不知道”。與1999年的調查結果相比,認為不會成癮的患者比率上升了12.3個百分點。腫瘤科和非腫瘤科醫師對重度癌痛治療曾經使用過杜冷丁的比率,比1999年下降了11.7個百分點。
根據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數據,在2010年,對癌癥疼痛規范治療率進行評估結果總體規范率為82.4%。不規范和無法評價的病史比例下降明顯。
在世界衛生組織三階梯癌痛鎮痛治療原則方面,我國的不懈努力已初見成效,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社會認識不足、醫療水平有限,癌痛治療的城鄉之間、地域之間依舊很不平衡。姚陽說,盡管止痛效果有限,且存在多種副作用,但“我接觸到一個在上海偏遠社區的病人,至今還在用杜冷丁來止痛。”
嗎啡止痛的利與弊
“作為醫生我們不僅要關注癌癥帶給病人的疼痛,更要關注治療給患者帶來的疼痛。當醫生沒辦法去除疼痛病灶的時候,止痛藥就成為了癌癥病人剩下的短暫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去除疼痛的手段。”姚陽說。
中國人提到嗎啡,大多想到的是鴉片和上癮。“患者家屬確實有誤區,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嗎啡給癌痛病人所帶來的獲益大于它的副作用,這不應該成為接受癌痛治療的障礙。”上海市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俊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大量臨床實踐證實,癌癥患者因長期使用嗎啡止痛而成癮者,極為罕見。”
盡管我國的藥典中已補充了癌癥患者使用嗎啡不受極量限制的條款,但在實際執行中,嗎啡的管控相當嚴格,需要醫生“開單”,并經過層層程序才能夠使用。
在上海徐匯區的康健社區服務中心,嗎啡類止痛藥物手續要簡單些,來到這里的病人已經進入癌癥晚期。對該服務中心舒緩療護科負責人唐躍中來說,幫助病人減輕痛苦是他和其他醫護人員最主要的工作。“用藥前我們會跟家屬溝通,告訴家屬副作用是什么,我們會怎樣處理。現在一半多的家屬能夠接受。”唐躍中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家屬覺得病人不用嗎啡止痛的時候是清醒的。”唐躍中說,“還有的家屬會擔心嗎啡上癮,我就跟他們溝通說,病人并沒有多少時間,起碼病人不再痛苦。”
“便秘、惡心、嘔吐以及精神狀態的改變等,都屬于嗎啡的副作用。”張俊解釋。
誰消耗了全球93%的嗎啡藥品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允許將嗎啡作為一種必要的止痛藥物,但在全世界范圍內阿片類止痛藥物的使用仍存在巨大的不均衡。高收入國家消耗了全球93%的嗎啡,而65%的癌癥死亡患者是來自于中低收入國家。
其中,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四國使用的阿片類藥物占全球的68%, 而所有中低收入國家使用的阿片類藥物加起來只占全球的7%。國際抗癌聯盟通過其全球癌痛防控項目正在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來加強對國際藥品管理,降低不平衡性和防止藥物濫用。
目前,臨床上常用于癌痛治療的短效阿片類藥物為嗎啡即釋片,長效阿片類藥物為嗎啡緩釋片、羥考酮緩釋片、芬太尼透皮貼劑等。
根據媒體報道,目前我國每年的嗎啡用量約為253千克,人均消耗量為0.203毫克,在123個向聯合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報送嗎啡醫療消耗量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07位。
社區醫院被寄予厚望
疼痛是人的一種主觀感受,每個人對疼痛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不同的癌痛有不同的治療方法,因此癌痛的治療又是個性化治療。“比如腦轉移的癌痛,最重要的是脫水,用嗎啡藥品就不行。除此以外,癌癥患者一般都是年紀大的人,常伴有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這也給疼痛的治療帶來一定難度。”姚陽說。
“不同的癌癥病人在疼痛的過程中,帶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最高的境界是去除疼痛的原因而不僅僅是使用止痛藥。所以止痛藥使用的指標只是國家關注癌癥疼痛治療的一個側面,不能代表全部。”姚陽說。
長期大量的臨床實踐證明,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癌癥三階梯止痛方案給藥,可以使90%以上癌性疼痛得到緩解,能明顯改善癌痛病人的生活質量。
在我國,大多數癌癥晚期病人并不住在醫院,而是在社區。以上海瑞金醫院腫瘤科為例,只有10%的癌癥晚期病人在醫院接受治療。所以,社區醫院和社區醫生在癌癥晚期病人的疼痛照護和治療上被寄予厚望。
“三甲醫院的腫瘤專家培訓社區醫生,給社區醫生提供支持和幫助,這對于癌癥患者太重要了。”姚陽說。
從2014年開始,姚陽開始與社區醫院合作,“我在腫瘤科‘打打殺殺三十年,但是我能幫助的癌癥病人十分有限,這不是建幾個癌痛規范化治療示范病房、示范基地能夠解決的,我希望能夠讓基層衛生系統也能實現癌痛規范化診治,社區醫院醫生完全做得到。”
為什么還在痛
“祝愿爸爸平靜安寧走完人生的最后一路。”在徐匯區康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一棵祈愿樹上,掛著這樣一張祈愿卡。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坦然地面對親人的離世。
胃癌晚期去世前,林老太也受了癌痛帶來的折磨。“她告訴我們,她真的受不了了,想快點‘走。”林老太的外孫女王曉梅(化名)告訴本刊記者。
“醫生告訴我們,這個時候可以選擇使用嗎啡止痛,但會有一系列副作用。醫生讓家屬自己作選擇。”王曉梅說。林老太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最后選擇使用嗎啡藥品,接受癌痛治療。“那時候離我外婆去世大約還有一個月左右。”
嗎啡藥品確實給林老太帶來了一些困擾。“她開始說胡話,時而清醒時而迷糊。”王曉梅說。家人都很擔心,“那個時候,我們也很猶豫,因為不知道選擇使用嗎啡藥品是否真的是對她好。”
王曉梅說,當時恨不得問醫生如果是他們的家屬他們會怎么作決定。“從醫生的角度來說,只會給家屬提供選擇方案,讓我們自己作決定。”
家族里最大的一次爭執,發生在林老太去世前的一周。“阿姨想要把外婆接回家,不再接受疼痛治療。”那時林阿婆出現了嚴重的嘔吐等癥狀,“媽媽和舅舅一直堅持讓外婆接受癌痛治療,直至去世。”王曉梅回憶,外婆“走”的時候,完全吐干凈了,應該并不痛苦。
到目前為止,患有晚期肺癌的王先生并沒有接受癌痛三階梯治療。“爸爸還有身后事要交代,我哥哥在外地還沒有趕過來,希望爸爸能夠保持清醒,如果用了嗎啡藥品的話,據說會一直昏睡。”王先生的女兒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再等等,之后可能會選擇用嗎啡藥品。”
“我們對于癌痛治療的宣傳和教育還不夠,患者和患者家屬還不了解癌痛是可以避免的,并且副作用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上海市疾控中心腫瘤防治科主任鄭瑩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據本刊記者了解,雖然我國的藥典中已補充了癌癥患者使用嗎啡不受極量限制的條款,并且癌痛類藥物已經納入了醫保報銷范圍之內,可絕大多數的癌癥晚期患者依然在忍受癌痛的折磨。

2011年7月30日,江西南昌,寧養院送來的免費止痛藥幫助吳英減輕了癌癥帶來的痛苦
“我們對于臨終關懷、生死哲學的思考還比較少,到底誰能對生命作決定。”鄭瑩說。由于癌癥晚期患者大多已經無法自己作決定,無法自己選擇什么樣的治療方案,作決定的大都是家屬,而家屬很多時候較難設身處地地體會到癌痛帶來的折磨,往往不會選擇癌痛治療。
“癌痛治療并不是一個科研難題,技術也已經很成熟,但專業人員應該更重視一些。”鄭瑩說,“癌癥防控、治療的專業人員應該多做些這個角度的研究,因為這對癌癥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舒緩治療
2012年6月,上海市徐匯區康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放舒緩療護病房。剛剛開放的時候,入住的病人以及家屬并沒搞清楚舒緩療護病房與腫瘤科室的區別。“曾經有患者家屬問我們,什么時候開始化療。”唐躍中回憶。
“我們并不是腫瘤科醫生,提供的并不是癌癥的治療。”唐躍中解釋說,“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減緩癌痛,讓病人最后一段路不要那么痛苦。”
舒緩療護的概念在我國較難被接受。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不少人認為放棄對臨終病人的搶救而只是選擇止痛,是“不孝”的做法。不少人也沒有考慮對癌癥晚期病人難以回天的多次搶救,可能帶來更多的過度醫療傷害,也是一種疼痛。
“有的病人家屬,來之前就做好了心理準備,我們就跟家屬溝通起來沒有障礙。”舒緩病房的護士長告訴本刊記者,“現在的家屬對于嗎啡類止痛藥也越來越接受了。”
這里的舒緩療護病房共有17張床位。“因為剛剛‘走了一位病人,所以現在住了16位病人。”唐躍中說。
2014年,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要求進一步將舒緩療護床位增加1000張,其中400張居家舒緩療護床位。
根據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上海每年因癌癥死亡約3萬人。每個癌癥晚期病人最后3個月都需要照護,舒緩床位顯得還不夠。這意味著,更多的癌癥晚期患者可能很難得到有效以及規范的癌痛治療。
“一直有病人在排隊等床位。床位空出來的時候,我們會打電話通知。”唐躍中說。但是在聯絡簿上,很多當時正在等療護床位的病人備注欄里寫著不需要了,“其實是病人‘走了,沒有等到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