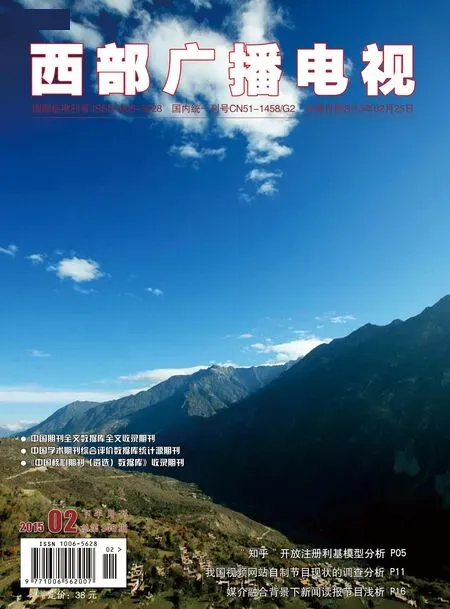日本恐怖電影中的性別社會認知焦慮
摘 要:由兩性的社會認知異化所催生的焦慮常出現于日本恐怖電影之中。具體分析此類影片則可概括出日本恐怖電影對表現兩性的社會認知焦慮的熱情。其中包含了男性的認知焦慮與女性的認知焦慮兩個方向,并使不同影片產生出完全不同的觀影心理效應。
日本恐怖電影中的性認知焦慮可以從男性視角和女性視角兩個方向解讀。兩性對于由同一社會所催生出的不同的性別認知觀念構成了日本恐怖電影的原始精神食材,并對一些具有符號地位的恐怖電影產生了深刻影響。
1 處刑人女友與男性的焦慮
從上世紀60年代發起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至今,關于性別命題的社會研究已是流派紛呈。此類成果的普及使男人得以理性認識到女性在千百年間居于第二性的生存狀態——一種對于女性傳統“受害地位”的同情或愧疚感成為中產階級男性群體的共識。但戲劇性的是,社會分配方式以及家庭分工恰恰使這個敏感而脆弱的“社會主力”群體成為在異性面前最不具備控制力的階層(對比其他男性階層而言)。這種控制力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產階級男性將對女性的不安認知與不可避免的、日益繁重的“社會責任(對大多數中產階級男性而言家庭責任成為其社會責任的構成主體)”化合并具象為現代社會男性所特有的性認知焦慮。這就像三池崇史的《切膚之愛》:中年喪妻、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青山在將獨子撫養成人之際躊躇地做出再婚決定。他不顧友人警告,堅定追求著神秘美女麻美——借由一次面試發現的令他一見鐘情的目標。但隨著交往的推進,有關麻美的可疑身世令青山日益感到不安,似乎眾多跡象都在證實這個女子曾經受到種種來自男性的侵害——其中自然也應包括那次帶有點無傷大雅的欺騙意味的面試。在這個身處對女性持有最大程度尊重的階層的男人心中,令人憐惜的受害女子“極合邏輯”地蛻變成“復仇天使”,并在那段令世人膛目結舌的“似夢似真”的幻境中對他進行了無比凄慘的處刑……如果說觀眾對她(麻美)襲擊青山的行為(在青山的噩夢中)產生一種矛盾感受,那大概是因為人們將他的家庭看作是“功能失常的”,男性權威“已受到破壞”。然而在自己的焦慮中將男性權威喪失殆盡的青山夢醒后還是要面對迎娶麻美的“正常生活”。
2 女性的焦慮
話題同樣由女性主義運動引起,迄今為止的愈發理性而具有觀念性的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似乎將兩性在社會位置上的平衡論題似乎被置于了常態化境地。在此若借用雅克·拉康(Jaques Lacan)精神分析學關于“三種菲勒斯”的原理,筆者更愿意將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理解為:從對“實際的菲勒斯”的敵視到對“想象的菲勒斯”的輕視再到對“象征的菲勒斯”的奪取過程。然而即使女性選擇將自身菲勒斯化卻也仍然不能逃脫資本時代對人類社會的異化。當女性主義與“社會閹割”(根據拉康的觀點,男人只有在閹割后才能具有象征的菲勒斯。那就意味著在現代社會喪失性活力的男人將從它物中尋求菲勒斯的象征性替代物,這也正是前章之表述。)令男人和女人同時具備象征的菲勒斯時,令她恐慌的就不再是男性而是充滿敵意的整個世界。石井隆的《不溶性侵犯》戲劇化地揭示出了這一現實:千希露曾經是“男權”的受害者,而當已經像男子般自立的她再度受到曾經的施害者的侵犯時,無助的她親手處決了這些“軟弱的雄性”——她因此失去了通過自身努力而獲得的社會地位甚至是繼續生存下去的社會空間——社會無情地沒收了女子用血汗為自己奪得的“菲勒斯”。這足以令現代社會的任何一位女性感到焦慮。相同的命題到了昆汀·塔倫蒂諾的《殺死比爾》中則以另一視角加以了詮釋:私自逃離組織的“無名”女殺手“B”(由烏瑪·瑟曼扮演的這位冷艷女郎有名字,但導演似乎更愿意將這位符號化的菲勒斯式女子之名當作一個“無關”的噱頭)向試圖殺害她(和她未出世的女兒)的殺手集團展開血腥的復仇。然而被復仇者(以女性為絕大多數)大都也已過上了脫離組織的“新生活”,于是菲勒斯式的女人們為了各自的生存理由而相互殺害。在這里一切都似已注定,人人都有了受害者的意味,一切異化的根源似乎又回到了女人們辛酸的成長史——充滿敵意的社會。(千希露)這樣的殺人既沒有讓她從過去的痛苦以及她目前作為女人的狀態中得到解放,相反,卻導致了她退出這個世界,而走向最終的自我毀滅。而脫離“致命毒蛇(D.I.V.A.S)”的女殺手們無論試圖成為相夫教子的平凡主婦或是日本黑幫頭目或是將殺手職業進行到底,都仍要為在奪得菲勒斯時所犯下的罪孽買單。這樣的心理表現使得《殺死比爾》這部美國影片所具有的濃郁日式特色變得自然而貼切。
結合以上內容,可以從日本最具符號價值的兩部恐怖電影中歸納出一種對于兩性的社會認知異化及其所催生的心理焦慮。這樣的理念成為了日本恐怖影片的基礎性表現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