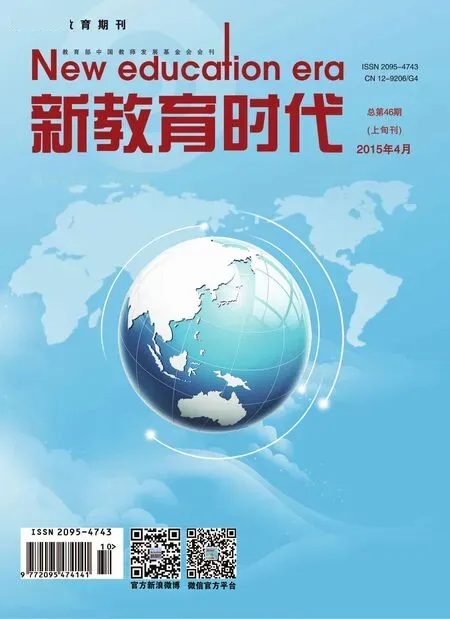從翻譯文化觀角度探討傳統譯論的意義
盛莉敏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從翻譯文化觀角度探討傳統譯論的意義
盛莉敏
(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在文化多元化語境下,面對異的考驗翻譯應遵循的原則,以尊重、開放的心態面對異質文化,進行平等、雙向的文化交流,從文化的角度來認識翻譯方法問題。但是,近三十年來國內翻譯研究中有重技輕道,重語言輕文化,重微觀輕宏觀的傾向。因此,確立翻譯文化觀很有必要,近些年,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這樣,多元文化語境下翻譯研究發展便應堅持如下原則,堅持翻譯研究的歷史發展觀、文化觀、動態觀,堅持文化研究的系統性和科學性,探索并構建中國學派的譯學理論,并且翻譯研究要走出象牙塔。
傳統譯論 魯迅 近代翻譯
下面淺析實現中國傳統譯論在中國翻譯理論的構建中的意義。
中國翻譯從象胥的任命到整個外事機構的設置,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中出現了三次翻譯高潮,像一只無形的手推動者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
我國的傳統翻譯理論自成體系。翻譯始于佛經翻譯,從漢末道安的“案本而傳”,六朝的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再到玄奘的“意譯直譯,圓滿調和”。近代又有嚴復“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魯迅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出發提出的“寧信而不順”的翻譯思想,還有林語堂“翻譯是一門藝術”的翻譯美學,傅雷的“神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理論。
傳統譯論可謂是源遠流長,碩果累累。而且中國古代及近代的“一些重要譯論,大都淵源有自,植根于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取諸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羅新璋,15)。這說明實現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化在中國現代翻譯理論的構建中的可行性。
然而,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很多問題,下面就從漢譯英中諺語和文化負載詞為例,說明翻譯的不可譯性。
漢語中的許多諺語,尤其為雙關語,如浙江江心寺正門的著名疊字聯,出自宋朝王十朋之手,內容為:“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念“yun,zhao chao,zhao zhao chao,zhao chao zhao san;chao,chang zhang,chang chang zhang,chang zhang chang xiao”)斷句不同,讀法不同,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見一斑。
傳統譯論的發展也自有其脈絡,羅國璋先生把傳統譯論的歷程高度概括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傳統譯論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現代一路走來,自有其傳承。到了現代,我們不應拋棄這一傳承。要知道,譯論應深深植根于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而脫離了本國土壤,一味崇尚西方翻譯理論,采用現成的西方譯論,翻譯研究便恰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但這并不是說要拋棄對西方譯論的研究,目前西方翻譯理論研究更為深入,廣泛,覆蓋符號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各個方面,我們以謙虛包容的態度,去吸取西方譯論的長處。
一代代的翻譯家們推動了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我們作為新一代的譯者,也應肩負起責任,兼收并蓄,在虛心吸收西方前沿譯論精華的基礎上,善于總結自身經驗,發展出深深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的翻譯理論,在世界譯林中獨樹一幟。
本文主要以魯迅先生的譯論為切入點,簡析傳統譯論對中國語言文化的意義。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翻譯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必不可分的。第一個重視翻譯并大力加以倡導直譯的人是魯迅。魯迅先生希望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
出于這個目的,魯迅先生作為五四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提出直譯思想,主張“寧信而不順”。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寫道,“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二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與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
魯迅的直譯思想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極高的譯學價值,它飽含了魯迅為創獲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的良苦用心,也大大開拓了中國譯學研究的視野。明清時期力主翻譯的“歸化”,這實則是一種長期“閉關鎖國”思想禁錮下的產物,當時人們做著天朝上國迷夢,盲目自大,以為“歐洲諸國皆為蠻夷小國,不足為慮。”認為歐洲文化及語言沒有什么可取之處,所以翻譯多采取歸化的手段,將外國語言馴服在漢語的威力之下。而魯迅先生站在了意譯的對面,提出直譯的主張,魯迅先生希望通過直譯,達到“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的目的。從當時的文化大背景下,魯迅這一主張蕩滌了當時社會的不良思潮,在當時,魯迅的直譯思想實際上是以一種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包容和接受外國文化,使中國文化能夠更加謙虛地吸收外國的養分與養料,才可以使漢語這棵大樹更加根深葉茂,充滿生命力。它是魯迅提出的一種理性的文化主張,是他為中國的新文化建設而發出的吶喊。
魯迅先生“寧信而不順”這一翻譯思想,從翻譯批評角度來看,犧牲了達而去求雅,并非是完全對的,甚至被梁實秋先生批評為“硬譯”。但如果從文化視角來看,在當時急需文化輸入的大背景下,“直譯”思想卻是極為合適的,不失為一個良策。
近代翻譯對漢語的詞匯、語法、句式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翻譯對漢語句法的影響,一是被動句使用頻率、范圍擴大;二是句式復雜化、多樣化,三是句子變得靈活多樣。(王克非,458)
總體來說,近代翻譯史以直譯為主,翻譯方法多為異化,采取歐化的方式,大力推進了白話文運動的浪潮,對中國的語言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國外出現“漢語熱”的熱潮,文化之間的傳遞是譯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我們應該根植于傳統譯論,充分認識到翻譯對于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
[1]許鈞.翻譯概論[M].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9.
[2]羅國璋.翻譯論集[M].商務印書館.1984.
[3]王克非.近代翻譯對漢語的影響[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2(6):458-463.
盛莉敏,女,漢族,生于1992年8月,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