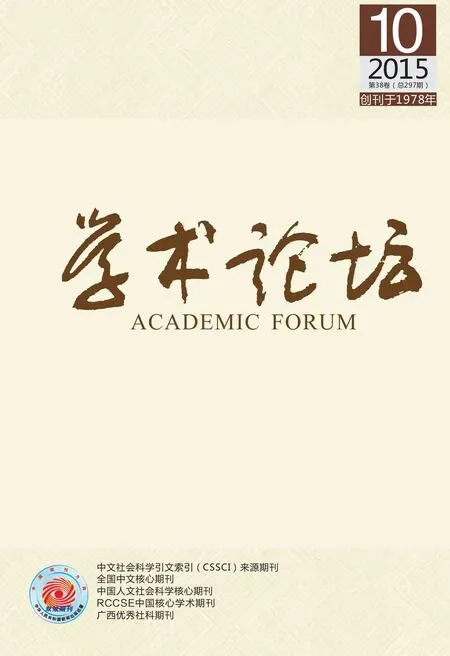沉默的情境社會學闡釋
王晴鋒
沉默的情境社會學闡釋
王晴鋒
情境社會學從互動組織和互動秩序的視角分析沉默,將它看作是結構性的而非心理性的現象。沉默被視為一種情境關系,是互動過程的產物。根據情境系統的互動規則與運作共識,面對面互動中的個體必須保持適當卷入,同時也必須采取適當的行動確保他人的適度卷入,以防止出現情境疏離與崩潰,這是一種交互支持的儀式性共同卷入。互動情境具有相對封閉、多人參與以及共同在場的特征。沉默是與情境和在場他人的疏離,是在場的缺席,它會導致尷尬的身份處境。在情境社會學的視角下,沉默并非個體內在屬性的反映,而是情境建構的產物。從互動規則的結構性分析框架而言,沉默更多的是一種情境失當行為。
戈夫曼;沉默;情境社會學;社會互動
沉默是人類活動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沉默不是一種孤立的、個體性的失語狀態,而是社會互動的重要構成。沉默并非是毋需解釋的無言空白,美國社會學家哈維·薩克斯(Harvey Sacks)曾說,“沉默是一種可解釋的溝通行動模式”[1](P212)。沉默存在多種不同的闡釋,行為者本身也會由于各種原因而沉默。在面對面的談話中,出現沉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交談者之間“話不投機半句多”;可能是由于談話者性格內向、不善言辭;可能是對談話主題感到索然寡味或對談話參與者不熟悉;可能是因重要他人在場而不敢說話或怕自己表達不好反而給人造成不良印象;可能是由于話題信息不對稱,無從說起;沉默也可能是出于一種無聲的抗議、拒絕與不合作等。本文的意圖并不是探討各種沉默現象的原因,無論這種原因是生理的、心理的抑或社會的,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政治的、經濟的抑或文化的。因此,這里沒有關于沉默的各種隱喻中充斥著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兒童、女性、同性戀者和大屠殺幸存者等),也不談論結構性壓制和社會漠視。本文探討的沉默本身即構成自成一體的分析系統和對象,這是一種互動性的、他人在場時的沉默,并試圖表明沉默可以在情境社會學的框架下進行分析。
一、沉默的類型、功能與本文的視角
不同層次的環境都會產生沉默現象,如在人類思維過程和文化發展進程中,日常生活意圖性的人際溝通中,政治和公民生活中以及病理性的環境中[2]。20世紀以來,不同的學科從各自的視角出發對不同的沉默現象進行了研究,諸如管理學研究組織沉默,它是指組織員工了解組織運行中潛在的問題,但出于某種目的而沒有表達個人觀點的行為[3],此類研究主要探討組織沉默的測量、原因與影響等[4];傳播學研究公眾沉默,即人們由于害怕孤立而導致“沉默的螺旋”[5];歷史學研究歷史沉默,即歷史編撰學與考古實踐等選擇性地忽略,有意識地遺忘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系[6];精神分析學運用弗洛伊德的壓抑觀念分析沉默,即個體潛意識地埋藏創傷性的痛苦記憶。此外,文化學研究文化沉默[7];集體記憶的研究者探討沉默與遺忘,比如維爾德·韋尼特茲基-瑟羅斯(VeredVinitzky-Seroussi)和查娜·提格(ChanaTeeger)區分了外顯的沉默與隱蔽的沉默,前者指言說與敘述的文字性缺失,后者則指記憶性談話與表征的掩蓋與遮蔽,但它并不是談話、儀式與實踐的徹底缺失。這兩種沉默類型都可以成為強化記憶或遺忘的機制[8](P1104)。
社會語言學對沉默的關注始于20世紀70年代,它最初被視為一種缺失狀態,也即言語、意義與意圖的缺失;沉默被視為一種否定、消極和失能,不被視為互動的構成。20世紀90年代之后,這種狀況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學者們開始視沉默為一種語言符號,認為它是在指稱功能中表達信息的。有些學者甚至將沉默置于語言的核心,認為“言說從沉默中產生,又歸復沉默”[9](P1911)。與語言學一樣,社會學中的會話分析學派也研究微觀言語層次的沉默。1974年,美國社會學家薩克斯、謝格洛夫和杰弗遜發表了《談話中話輪轉換組織的最簡單系統》(“The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一文,此后,話輪、話輪轉換規則和毗鄰對等概念成為會話分析的重要工具,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將這套概念運用于談話沉默,比如探討話輪內沉默、話輪間沉默以及話輪沉默等[10]。
同時,也有學者探討了沉默的類型、功能與意義。例如,托馬斯·布呂諾(Thomas Bruneau)區分了三種類型的沉默:心理的、互動的和社會文化的。他認為心理性沉默的持續時間相對比較短暫,表現為談話過程中的停頓,或者故意減慢語速以讓受話者理解剛才說的話;互動性沉默的持續時間比心理性沉默長,它與人際關系有關,其中話輪轉換起著重要作用;社會文化性沉默則是前兩種沉默形式的基礎,社會與文化習性決定著心理性沉默和互動性沉默[11](P36)。丹尼斯·科仲(Dennis Kurzon)也探討了社會互動中的沉默類型學,他根據沉默者與受話者之間的關系、參與互動的人數、是否存在具體的文本、保持沉默的意圖以及權威與社會規范等區分了四種沉默類型:談話沉默、主題沉默、文本沉默與情境沉默。其中最常見的是談話沉默,相應的研究也最多;主題沉默是指言說者(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規避某個特定的話題或主體,如男性話題中女性的缺席;文本沉默指沉默者在既定的環境下默讀或默誦某個特定的文本,如默禱;而情境沉默中的個體并不默讀或默誦任何文本,如在各類紀念儀式上的沉默[12]。關于沉默的功能方面,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指出了言語溝通中的六大功能,即指稱功能、情感功能、意動功能(conative function)、交際功能(phatic function)、詩意功能(poetic function)和元語言功能,在這種分析模式的基礎上,米加·埃法拉特(Michal Ephratt)探討了沉默在這六個方面相應具有的功能[9]。此外,弗農·詹森(Vernon Jensen)也探討了沉默的五種功能:聯結功能,將人們或若干關系結合起來(如紀念儀式場合);感染功能;揭示功能,表明對某個話題不知情;判斷功能,表達異同、喜惡之情以及默許與無聲的抗議等;激活功能,如言說之前的醞釀[13]。
本文主要采用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關于微觀人際互動的分析框架來探討沉默現象。安妮·羅爾斯(Anne Rawls)曾指出,戈夫曼試圖通過系統性地闡述“關于情境的社會學”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表演和社會秩序的構成[14](P231),這種視角的特點是強調社會互動的情境性。本文將戈夫曼的這種分析模式稱為“情境社會學”,并主要運用戈夫曼的擬劇論和微觀互動論作為理論框架來分析沉默。在情境社會學看來,沉默是一種情境關系,是互動過程的產物。這種互動是通過眼神、身勢以及碎片式話語完成的。沉默更多的是結構性的,而非心理性的。在這種視角下,沉默并非個體內在屬性的反映,而是一種情境建構的產物。
二、情境系統中的互動規則
在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中,互動參與者每時每刻都在進行信息交換。在戈夫曼看來,行動者的信息不僅是“發出”的(give),也是“流露”的(give off)。印象管理的高手和深諳舞臺表演技巧的老手能夠對這兩種信息進行操控以塑造和維持他們希望產生的自我。但是,戈夫曼同時認為,“任何一種情境定義都具有明顯的道德特征”[15](P10),個體有義務保持一種自然的參與卷入,當他無法維持互動位置或執行特定的互動角色時,其他共同參與者會提供援救以恢復互動秩序。也就是說,個體不僅自身必須保持適當的卷入,而且也必須適時采取措施確保他人的適度卷入。因此,這是一種交互支持的共同卷入。現實是不穩定的,容易遭到各種干擾與破壞。為保證互動平穩流暢地進行,需要有一套機制防止出現情境定義的崩潰。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戈夫曼將互動看作是一種儀式,是對“共同體道德價值的表達性復原與重申”[15](P29-30)。這種道德性包含了兩個維度,它既體現在表演者之間(或劇班內部),也體現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一方面,個體采用防衛性措施保護自身的情境定義,劇班成員承擔著道德義務或品性,具體表現為擬劇忠誠、擬劇紀律和擬劇審慎;另一方面,互動參與者通過保護性措施保全他人的情境定義,這涉及各種后臺管理、謹防冒失者不合時宜的闖入、配合他人的舉止等,以確保互動流暢,防止出現尷尬。因此,互動中會產生“臨時妥協”和“運作一致”(working consensus)的情境倫理[15](P8)。在戈夫曼那里,經過充分社會化的個體是“儀式性雅致的客體”[16](P31),他愿意遵守社會互動的基本規范。與迪爾凱姆的社會系統一樣,戈夫曼的個體也具有神圣性,并且浸淫在一個充滿道德意涵的世界中。戈夫曼如此引用迪爾凱姆的觀點:“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既不可褻瀆它,也不可侵入其領域,然而,與此同時,最大的善卻是與他人的交流。”[15](P56)
以上大致勾勒了戈夫曼關于日常生活中互動規則的輪廓。無論是出于社會規范的要求還是人際互動導致的結果,社會性沉默的促使因素通常是外部性的。在社會情境中,無疑也存在完全由個體的內在性所引發的沉默,例如不希望被打攪、獨自沉思冥想等,這種類型的沉默基本上不是互動的產物。人們通常將沉默看作是“正常狀態”的疏離,是一種“溝通斷裂”[17]或能指的缺失,是參與者單方面宣告的互動熄滅狀態。在情境論的視角下,社會互動中的沉默是個體與情境和他人保持距離,自我脫離于當下,成為在場的缺席者,從而造成一種尷尬的身份處境。在這種情形中,沉默者處于一種特殊的臨界狀態:要么加入面對面互動,要么起身離開。沉默者讓在場的他人感到局促不安、心神不寧,因為他由參與者的角色轉變成一位互動的監視者、旁觀者和偷聽者。這種交流是不對等的、單向度的,它破壞了共同的關注焦點,突如其來的沉默暴露出參與者之間缺乏共同的旨趣。沉默者是清醒的、理性的和有意識的,并且有能力對正在進行的情境進行持續的感知性監控,而智障者、夢游者或沉睡者的舉止一般不會構成沉默行為。沉默者隱藏了意圖,將話語以及思維的文本深藏不露,他甚至還有可能操控表意行為的信息“流露”。
我們這里探討的互動情境具有這樣的特征,即相對封閉、多人參與以及共同在場,并且每位參與者都承受著參與互動的情境壓力。會議、聚餐、面對面聊天和讀書會之類的場合,可以被視為這種情境系統的典型表現形式。在這些情境中,沉默是一種行為失當,不管它是因溝通受阻而出現的游離狀態還是抗議與不滿的表征,而這種行為失當是互動雙方造成的。在相對封閉的互動情境中,個體沒有權利不說話;相反,根據情境系統中的互動規則,他有共同維持、參與卷入的義務。他必須是“開放性的人”,既允許他人進入,也意欲進入他人。此外,在談話互動中,一旦出現缺乏“安全供給”的狀況,也容易引發參與者之間的沉默。這里需要略加說明的是,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行動系統,關于沉默的分析排除了純粹個體性的因素。我們所作的是形式化的情境性分析,而這種分析邏輯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三、沉默與情境失當
任何個體在不同的場合都能產生一定程度的介入,即使是啞巴、耳聾以及其他殘障人士也可以通過身勢語進行溝通,他們并不一定是情境中的沉默者。因此,任何形式的沉默都不是單純的生理原因能夠完全解釋的,而精神病理學也無法解釋在一般的社交場合隨處可見的沉默。正因如此,筆者認為沉默是一種情境性的社會行為。情境社會學主要從互動組織和互動秩序的視角分析沉默,它包含以下一些關鍵性的要素或分析工具,即聚集(gathering)、沉默者所處社會位置的易接近性或可進入性、相互參與、卷入義務與情境疏離等。互動參與者有維持互動的職責,共同防止出現情境撤離與疏遠,因此,個體需要約束自己,同時開放自己,使能夠彼此卷入互動,這也是互動的可進入性原則。遵照這種互動規范,即使是兩個意見不合的人在無法規避的社交場合也會勉強地相互寒暄致意。
但是,互動情境中自發的團結狀態是脆弱的,它面臨著各種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產生疏離與崩潰。就約束性卷入而言,情境失當行為可以被稱作“錯誤卷入”(misinvolvement)[16](P117)。戈夫曼分析了疏離性錯誤卷入的四種形式:(1)外部專注。個體忽略規定的關注焦點而將其主要關注放在與當下無關的事物上。(2)自我意識。個體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互動參與者本身,這種自我意識并非由于個體對談話主題有濃厚的興趣,而是沉湎于自我關注,它是互動系統的內部專注。自我意識可以是表達欣喜或保護自我的方式。(3)互動意識。談話參與者不適當地關注互動進程和情境結構,而不是自然地投入于會話的正式主題。當談話過程中用盡了諸如閑聊之類的“安全供給”時,互動意識就可能導致令人痛苦的沉默[16](P120)。(4)他者意識。互動過程中個體將另一位參與者作為關注對象而導致分神和注意力不集中,如當談話互動中出現矯揉造作、故弄玄虛或偽善的互動參與者時。個體一旦感知到他人的做作、虛偽、傲慢無禮和粗鄙放肆等特征,就會認為他們破壞了互動的基本規則,對這種不公平游戲所懷有的警惕與敵意導致他將注意力放在這些人及其不端行徑上。當信息傳達過程中說話者的“通訊設備”本身表達了額外的信息時,聽話者會由于競爭性的刺激源而導致分心,變得過于關注說話者本身而不是其說話的內容。此外,過度卷入(將個人感受凌駕于道德準則之上)也是他者意識的重要來源。上述這四種互動的疏離形式構成了對互動秩序中卷入義務的違犯,在實際情形中這些形式通常會糅雜在一起同時發生。與互動產生的疏離是個體無法根據社會規定的準則恰當地對卷入進行配置并控制其程度,結果導致他對互動及其參與者表達出不恰當的態度。需要指出的是,疏離的屬性具有群體差異性,對個體是否“恰當地卷入”的感知與評判與其所屬的文化準則密切相關。
沉默是對相互卷入規則的公然違犯。在某些場合,個體的沉默會比公開表達異見更讓在場者感到情境壓迫,這種疏離破壞了情境的交互性和整體性,因為沉默者通常是被認可的參與者(至少在卷入之初他是被如此定義的),不是毋需關照或可以忽略不計的旁聽者,其他參與者無法視沉默者為“非人”(non-person)。而沉默是自我主動摒棄了參與者的身份,但又由于他的在場而無法徹底擺脫這種身份。沉默者無法履行相互卷入的義務,又由于共同在場的他人未能揣摩其意圖而導致無法施行適當的補救措施,從而最終可能導致情境崩潰。與偷聽等行為一樣,沉默是對交互卷入的重要威脅。
沉默者自身也會產生異樣的情緒表現,覺得格格不入、如坐針氈,無法表現得輕松自在(除非他是精神病人),它會導致一系列負面的情感:緊張不安、臉紅、焦躁、尷尬、窘迫甚至敵意,并以惡性循環的方式導致一個自我封閉的交流圈。他人讓其回答沉默的原因時,他可能閃爍其詞——作為一種心理體驗,很難說出沉默的具體原委,而真正的原委又源自于在場的他人及其情境,沉默者為了顧全顏面而不愿說出真實的感受,這反過來又加深了他人既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刻板印象。在特定的情境互動中,每一位參與者都被視為合格的成員,潛在的沉默者自身也如此認為。隨著互動的深入,他會越來越感覺疏離,而談話者則越來越投機。這是一種個體心理性的沉默螺旋,越沉默就越難以啟齒介入當下的話題,這個過程中會發生價值累加效應。盡管情勢的發展并非一開始就是這樣,也就是說,沉默者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料想會出現沉默,他不是有意來現場向他人展示“沉默的”,他是來參與的,也即有參與的意愿。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導致卷入的發展將他遠遠地甩出了情境及其互動狀態,從而使他無法參與。此時,沉默者的卷入度急劇下降。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自我開除,它潛在的危險在于:沉默者隨時可能蘇醒過來,恢復參與的資格與能力。對沉默主體而言,他自身則成了旁觀者,但是對其他在場者而言,他仍是參與者——一位不合格的、不適當的參與者。這便是沉默者身份的尷尬之處。在通常情況下,自由式談話的參與者、話題和談話進程等都是無法事先預料和控制的。因此,沉默的重要社會學特征在于它是一種情境性行為,沉默是在情境中逐漸累積生成的,或者說,沉默是展演性的。這便是沉默的動力學特征。
四、情境互動論視角下的沉默
我們在上文已經談到,沉默產生的個體心理效應會不斷地累加,因為一個人在被疏遠的同時,情境中的其他人并沒有停止互動,他們即時性生成的關系也在迅速地發生變化,“運作共識”迅速成為參與者之間的基本原則。這種共識與原則會形成一個共同體和一種細微的互動氛圍,從而產生無形的隔閡,并且很可能在某個疏離個體的反照之下更加增強他們之間的團結和默契。也就是說,沉默會促成他人之間的團結和共謀。無論這種沉默是有意還是無意,它都是一種情境失當行為,它違犯了被社會普遍認可的情境禮儀與互動規則。
每一個情境都存在退出機制,沉默者可以選擇自我離開,但這種獨自離開會對情境造成公然的破壞,因此,它必須謹慎處理。退出者會尋找各種圓通的、合乎情理的、他人樂意接受的理由來退場。在場的參與者也可能樂于接受他離開的請求,因為他是互動的干擾者和破壞者。當然,也可能出現情境補救的行為,即在場的他人主動提供協助,如選擇沉默者擅長或喜歡的話題,使他暫時成為談話的核心等,從而象征性地重新肯定其地位。這種情況下通常呈現出對答的形式,但一般難以為繼,因為不可能整場談話都以“補救”某個人的形式進行,談話通常是“自然而然的”。
正是由于存在責成個體遵從情境性共同卷入的規則,我們才能解釋在聚焦式互動中對失當卷入的反應。在可進入式互動中,個體有義務使自己的行為與“情境氣質”(ethos of situation)保持協調,并且有義務在情境中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卷入。因此,我們即使是在無心參與的場合也要巧妙、得體地表現出正在專注傾聽的表象。在成功的社交場合,參與者們顯得志同道合、興致盎然,逐漸形成一種趣味相投的情境氣質。而沉默則是對這種情境倫理的抵制,拒絕投入互動共同體。正是基于這樣的互動共識,長時間不參與的個體會導致自己和他人的焦慮,乃至互動秩序的崩潰。沉默不僅使自我感到窘迫,也讓他人感到局促不安。因為自我成為無法窺視的黑洞,他人會覺得自己被冒犯。其他參與者無法判斷沉默者的立場與心理,以為是當下的談話或行為冒犯了他,因此使得整場談話變得如履薄冰,使得話題驟然變得狹窄,談話氣氛變得凝固。
這里對情境互動論視角下的沉默分析作三點澄清:首先,對于在場的他人而言,個體都是彼此可進入的和可獲得的。我們這里討論的是在特定情境中有資格、有能力參與卷入的個體卻出現沒有參與卷入的情況,沉默者成為在場的缺席者。這是一種微觀的互動分析,它探討的不是宏觀意義上的集體性、合謀性沉默,也就是說這里要談論的不是“房間里的大象”[18],不是遺忘、忽視和否認。我們的主要意圖不是探討沉默的成因和動機,也不提供打破這種沉默的可能方式,而是從微觀互動的角度分析作為一種情境失當的沉默現象。其次,戈夫曼在分析微觀互動系統時沒有過多地涉及權力因素,盡管他并沒有忽略它的存在,這是因為權力的介入在本質上干擾或破壞了正常的互動秩序,各種“例外”的介入和混雜使得原本復雜的社會現實變得更加糾纏不清、撲朔迷離。在沉默問題的分析上亦是如此。所有權威等級下的沉默形式也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如上級訓話時下級默默地接受(尤其是家長對孩子)。這種雙方地位不對等條件下的沉默是對權威的服從,不需要插話,更不能反對和抵抗。沉默顯得理所當然,也心安理得,甚至被認為是虛懷若谷、遵從接受與守規矩,沉默便成了“金”。這也是為什么戈夫曼更愿意借鑒動物行為學的思想來探討人類互動行為的原因之一。最后,互動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應該介于熟人與陌生人之間,也即是“半生不熟的人”。互動參與者之間并非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如果是像夫妻或兄弟姐妹那樣親密無間的熟人,那么他們之間在面對面的談話過程中可任由時間流淌,在大多數情況下沉默并不會導致情境的崩潰。如同權力關系一樣,熟人關系(情感)亦會改變原初的互動結構。
五、結語
生理學從生理功能障礙和缺失的角度解釋沉默,心理學尤其是精神病理學從情緒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研究沉默,語言學以話輪轉換探討沉默,而社會學則從情境互動的角度來分析沉默。當然,我們對沉默的分析只是提供了一個視角。我們知道,沉默并不僅僅是言說的對立面而已,沉默之處可能恰是語言或描述系統的限度之所在。沉默甚至可以是言語的救贖,在很多社交性的場合,個體會有意識地希望保持沉默,以尋求一份清凈的安樂,恢復一種安全感和自由感[19]。在某些場合,適當的沉默還能夠為人格增添一種審美上的雅致與魅力,也即所謂的“沉默是金”。此外,沉默也可以是一種社會排斥、反社會行為以及非暴力的反抗形式。從情境社會學的視角看來,沉默更多的是一種情境失當和破壞互動秩序的行為,是互動情境的威脅,沉默并不是金。這種分析主要是基于三個原因:首先,面對面參與者所處的是必須作出即時性反應的“壓迫性情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情境社會學是從客觀的、純粹的情境互動規則來探討沉默,而不涉及個人情感以及他人的諒解或關懷。簡而言之,它是一種結構性分析。作為情境失當的沉默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沉默,它也可以被視為韋伯意義上的理想型。最后,本文的分析路徑類似于迪爾凱姆對社會失范的研究,對作為情境失當的沉默之分析是為了更好地揭示微觀人際互動的卷入規則與秩序。
詩人對沉默充滿了各種迷戀和贊賞,因為他們更需要退回內心世界來反觀自我。與之不同,社會學家的生活世界是喧囂嘈雜的,他們論述的個體需要不斷地參與各種面對面的卷入和互動,并遵循各種社會規范。沉默者并不是沒有社會角色,而是拋棄了社會賦予的既定角色,但他仍然滯留在情境里面。正是基于社會交往與互動卷入的規則,使得社交場合中的沉默變得難以容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關于沉默的情境分析不是一種歷史性分析,因而無法帶入情境之外的個體歷史、文化結構和社會進程。這也是帕森斯式的結構功能主義取向的特征。戈夫曼畢生追求闡釋的概化和形式化,他的方法是將社會組織的切片放到微觀分析框架的顯微鏡下進行仔細的觀察,從而達到理解整個互動行為系統的目的。本文希望關于沉默的情境社會學分析為理解社會組織提供這樣的一種維度。
[1]Lynch,Michael.Silence in Context: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Theory[J].Human Studies,1999,(22).
[2]Johannesen,Richard.The Functions of Silence:A Plea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J].Western Speech,1974,(38).
[3]何銓,馬劍虹.沉默的聲音:組織中的沉默行為[J].心理科學進展,2006,(3).
[4]徐榮,曹安照.組織沉默研究述評及啟示[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9,(6).
[5]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M].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6]Schmidt,Peter and Jonathan Walz.Silences and Mentions in History Making[J].Historical Archaeology,2007,41(4).
[7]Berlin,Isaiah.The Silence in Russian Culture[J].Foreign Affairs,1957,36(1).
[8]Vinitzky-Seroussi,Vered.,and Chana Teeger.Unpacking the Unspoken:Silence in Collective Memory and Forgetting[J].Social Forces,2010,88(3).
[9]Ephratt,Michal.The Functions of Silen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8,(40).
[10]左巖.英語會話中沉默的研究[J].國外語言學,1996,(2).
[11]Bruneau,Thomas.Communicative Silences:Forms and Function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3,(23).
[12]Kurzon,Dennis.Toward a Typology of Silence[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7,(39).
[13]Jensen,Vernon.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Silence[J].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1973,30(3).
[14]Rawls,Anne Warfield.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G].In Goffman's Legacy,ed.Javier Trevi?o.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15]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馮鋼,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6]Goffman,Erving.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M].New York:Pantheon,1967.
[17]Silvers,Ronald.On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J].Human Studies,1983,6(1).
[18]伊維塔·澤魯巴維爾.房間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M].胡纏,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
[19]Ganguly,S.N.Culture,Communication and Silence[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68,29(2).
[責任編輯:戴慶瑄]
王晴鋒,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講師,社會學博士,北京100081
C91
A
1004-4434(2015)10-00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