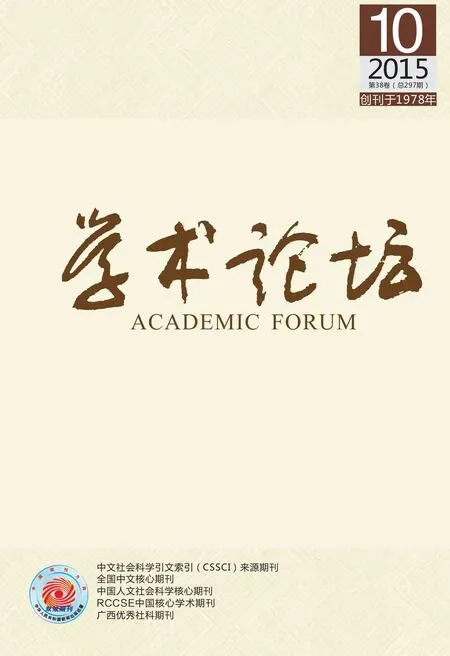論預算法定原則及其實現路徑
李培磊,解志勇
論預算法定原則及其實現路徑
李培磊,解志勇
預算法定原則的實現有不同的形態。我國實現預算法定的前提條件是政府的財政決策和立法權得到控制;基本模式是發揮人大的規范權力,實現全過程法律控制;此外,還要在關鍵環節建立人大的直接權力作為保障措施。
預算法定;財政權力;全過程法律控制
新《預算法》在立法目的上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加入了“規范”和“約束”等關鍵詞,實現了從“管理法”向“控權法”的轉變。還在總則部分增加規定“各級政府、各部門、各單位的支出必須以經批準的預算為依據,未列入預算的不得支出”。這被認為是邁向預算法定的重要標志[1]。
預算法定原則是財政法定原則的一部分。但正如財政法定原則一樣,它也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2]。學界一般是從內容上將財政法定原則闡釋為財政權力法定、義務法定、責任法定、程序法定四者。這一闡釋并無錯誤,但卻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引,因為預算法定原則的實現有不同的形態。
一、預算法定原則的不同形態及歸納
美國、德國都是將預算法定原則貫徹得比較好的國家,但在這兩個國家,預算法定原則的表現卻有所不同。
(一)美國:強調議會的直接權力
在美國,預算法定最突出的特點是凸顯了議會在控制政府財政收支方面的直接權力。
首先,美國國會有權自己制定預算。美國憲法將征稅權和根據撥款法案進行開支的權力賦予了國會,而對于總統和行政機構在預算方面的權力只字未提。盡管1921年頒布的《預算與會計法案》為總統預算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但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下,總統預算只是對國會的建議,國會仍掌握著預算方面的主導權力。諾頓(Philip Norton)曾依據議會在預算方面的權力不同,將議會劃分為:(1)制定預算的議會,即有能力修改或者拒絕行政機關提出的預算建議,并且有能力自己制定預算替代之;(2)影響預算的議會,即有能力修改或者拒絕行政機關提出的預算建議,但是缺少能力自己制定預算并替代之;(3)批準預算的議會,即對預算的影響很小或沒有,缺少能力修改或拒絕行政機關提出的預算建議,也沒有能力自己制定預算并替代之,一般來說,他們僅限于贊成預算[3]。美國的國會即屬于第一種。
其次,最終生效的預算案是一個法律的集合。美國國會在預算過程中需通過兩次預算決議案。第一個預算決議案只是在議會內部確定一個財政框架。依據這個框架,兩院各類委員會制定法案。第二個預算決議案包含了財政收支框架和征稅法案、授權法案、撥款法案等具體法案,并且需經總統簽署后才能生效。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正是這些法案。以撥款法案為例,美國憲法第九款規定“除根據法律規定的撥款外,不得從國庫提取款項”。
最后,財政支出需經國會的同意,沒有例外。美國憲法規定支出必須依據撥款法案是極具剛性的,沒有例外。當預算案不能如期通過時,政府如果要獲得財政資金,必須獲得臨時撥款法案[4](P155)。臨時撥款法案和普通撥款法案一樣,也是需要國會兩院一致同意才能通過,經過總統簽字才能生效[5]。因此,當預算不通過,臨時撥款法案也未能及時制定時,美國政府沒有便宜行事的權力,可能發生停擺。
(二)德國:強調議會的規范權力
在德國,議會在確定預算案方面的權力要弱于美國國會。因此,德國議會在預算案之外,更注重通過其他法律規范實現對政府權力的有效控制。
首先,德國聯邦基本法賦予了行政機關在財政收支方面的直接權力。根據德國《聯邦基本法》,“如某個財政年度結束時,尚未以法形式確定下一年度預算計劃的,聯邦政府在新預算計劃生效前,有權就下列事項給予一切必要的支出……”。又如,“超計劃的和計劃外的支出需征得聯邦財政部長的同意。只有在出現不可預見和非故意超支的情況下,方能予以同意。具體由聯邦法律予以規定”。這兩項都表明了德國行政機關在財政收支方面的直接權力,并不需要得到議會批準,只需要遵守議會制定的法律。
其次,德國議會有能力修改或者拒絕行政機關提出的預算草案,但是缺少能力自己制定預算并替代之。因此,屬于諾頓所言的“影響預算的議會”。其重要差別在于議會修改預算草案的權力是有限的,一般不能作出增加支出數額的修正。根據德國《聯邦基本法》第113條,“導致聯邦政府提出的預算計劃支出增加的法律或者導致收入減少的法律需征得聯邦政府的同意。聯邦政府可要求聯邦議院暫緩決議通過此項法律”。在沿襲了德國預算制度的日本,學者指出,(議會進行)增額修正雖是可能的。但在修正時,仍須注意預算提案權在于內閣這一主旨[6](P121)。
最后,因為權力配置上的差別,德國議會在控制政府的預算權方面采取了更復雜的方式——精細的立法。例如,針對上述聯邦財政部擁有的同意超計劃支出的權力,《聯邦預算法》第37條作出了更具體的要求。除了這種具體的法律規則,德國的《聯邦基本法》《聯邦預算法》以及《聯邦和州預算基本原則法》規定了大量關于預算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包括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一般原則又可以分為實體原則和程序原則:前者包括必要性原則、經濟與節儉原則、總體覆蓋原則、預算平衡原則、總體經濟平衡原則、禁止搭載原則等,后者包括事先原則、年度原則、公開原則等。特殊原則數量更多,僅針對預算編制階段的就有:統一與完整原則、當期原則、預算清晰原則、毛額估算原則、個別估算原則等[7](P42)。
(三)對預算法定原則的歸納
通過對美國以及德國預算制度的比較,可以獲得對預算法定更為完整的認識。預算法定包含三個關鍵的語素,“預算”“法”以及“定”。
“預算”的本質是政府的財政收支計劃,但要實現預算法定,不能只要求這一計劃法定,與之相關的財政收支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控制。
“法”不僅指預算案。預算案由議會通過立法程序確定,固然是預算法定的重要保障,但其他法律的作用也不能忽視。并且,法不僅包括法律規則,還包括法律原則。
最后,“定”固然主要是指規定,但必須注意到,“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僅僅是文字上的規定是沒有意義的,法定的要求需要由一定的機制保障其實施。
基于以上分析,可將預算法定原則的要求歸納為三個部分:(1)與政府財政收支計劃相關的重要事項都由法律規定,其中的大部分還要直接體現在預算案中,由議會通過立法程序審定;(2)沒有體現在預算案中,也沒有法律作出具體規定的事項,至少也需要由法律作出原則性的要求;(3)不論是具體的規定,還是原則性的要求,都要有一些控制機制以保證法定的要求得以實現。
上述三個部分可以簡述為一句話:政府的財政收支權力完整地處于議會或議會制定的法律的控制之下。
二、中國實現預算法定的出發點
既然預算法定不是單一模式,在中國落實預算法定原則,就必須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在各類實際情況中,作為規制對象的政府財政權力配置狀態是最基礎的。我國的《預算法》于2014年8月31日進行了修訂,可以預計的是,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與預算相關的政府財政權力配置不會再發生大的改變,這為討論預算法定原則的實現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出發點。
(一)政府不再擁有進行預算外收支的權力
新《預算法》最重大的改變在于確立了全口徑預算制度,取消了預算外資金。
在我國,預算外資金長期以來都以法定的名義存在于國家財政活動之中。原《預算法》第76條規定“預算外資金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新《預算法》第4條明確規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
(二)政府的預算決定權和調整權受到削減
在原《預算法》之下,政府擁有兩項在特定情況下的預算決定權:其一是在預算批準之前對臨時預算的決定權;其二是在不影響收支平衡的情況下,對超收部分進行支出的決定權。
之所以將這兩者稱為決定權,是因為不需要經過人大的審批程序:對臨時預算的決定,政府只需要事后進行說明;對于超收預算的決定,需要事前通報和事后說明①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中央預算審查監督的決定》第四條。。新《預算法》維持了第一種權力,但增加了實體的和程序性的要求②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七條。。同時取消了第二種權力,不以收支平衡為條件,只要是增加或者減少預算總支出的,都需要經過人大批準③。
在原《預算法》之下,政府還擁有在預算科目之間進行調劑的權力(這在法定的預算調整范圍之外,屬于廣義的預算調整),一般不需要獲得人大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以下簡稱《人大監督法》)對此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農業、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等預算支出需要調減的,各級政府需要經過人大的批準。新《預算法》將這一限制普遍化,規定“調減預算安排的重點支出數額的”需要經過人大批準程序。
(三)政府依然行使大量的財政決策立法權
實踐中,不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財政收支方面的立法權十分普遍,大有壓過人大立法權的勢頭。并且,一些政策行為也顯著地侵擾了立法權。
首先,中央政府方面。目前,我國的18個稅種中,只有3個稅種是由全國人大決定的,其他都是由條例創設。國務院獲得這些授權的依據主要是《關于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有關稅收條例草案試行的決定》和《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這兩個文件都是打包式的授權,其寬泛程度幾乎可以視為人大“轉讓”了財政立法權。
其次,地方政府方面。《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以及《國務院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明確表達了稅收立法權集中在中央的觀點。目前只有海南省、民族自治地區以及特別行政區有獨立的稅收立法權,大多數地方政府只享有制定實施細則的權力[8](P363-365)。但地方政府顯然不甘于此,它們不制定稅法,但通過其他方式行使財政收支立法權,例如:(1)拓展行政收費立法權。省級政府雖然不能開征新稅,但可以名正言順地征收各種具有稅收性質的“費”。(2)擅自出臺具有減免稅效果或類似效果的政策。地方政府減免稅的權力被嚴格限制,但利用這些財政政策,地方政府取得了類似立法權的效果。
(四)政府預算違法法律責任追究機制不暢
在當前,人大監督權的發揮依賴于政府,主動性和獨立性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導的審計監督和行政問責的效果也不理想。
首先,人大在獲取監督信息和實施問責方面對政府有很大的依賴。一項實證研究表明,最近幾年,地方人大獲取監督信息方面成績顯著,分別有52%和45%的地方人大表示能夠掌握詳細的部門預算收入和支出信息。而在問責方面,地方人大普遍做得不甚理想,有89.1%的地方人大常委會近5年來(2012年之前5年)未曾對決算審查中發現的重大問題提出質詢;否決政府審計整改報告的僅1例;而否決政府決算草案和審計工作報告則從未出現過[9]。這一情況的根源在于人大缺乏主動獲取信息和實施問責的制度化途徑。當政府報送的材料更為完整,人大就能獲得較為充分的信息,反之則不然。一個數據顯示地方政府向人大報送部門決算的樣本比重明顯小于部門預算[9],這凸顯了政府的主導地位。同樣,當政府對于人大提出的整改要求履行不力,人大也沒有更為有效的措施。
其次,政府審計監督雖能發現大量問題,但卻未能將其轉化為約束力。根據審計署的報告[10]:2013年,科技部部本級未經財政部批準,自行將3個項目預算共計2.2億元細化并下達給所屬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部本級在“工業和信息化行業管理”項目中列支與項目無關的課題經費100萬元、擴大開支范圍向所屬信息中心等支付其他項目資金1281.20萬元;所屬應急中心未經批準,自行調整項目支出預算803.87萬元。類似這樣的問題長年累月地存在于各級政府,但即便在多次被披露之后,也鮮見有相關主體受到追究。
三、中國實現預算法定的路徑
新《預算法》在沒有改變權力配置結構的前提下作了一些細微的改變,可見我國的財政權力配置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常態:政府擁有一些原生的財政收支權力,人大的主要職責在于對其進行控制。這表明我國走上了類似德國的預算法定模式——主要靠發揮人大的規范權力實現對政府權力的控制。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要實現預算法定,在基本模式之外,還有一些特殊要求需要滿足。
(一)前提條件
在政府擁有的上述權力中,最危險的是財政決策權和立法權,讓它們受到法律控制是在我國實現預算法定的前提條件。
其原因在于:財政決策權和立法權處在預算權力的上游。從某種意義上說,預算只是對法律、法規、政策乃至政府項目所等確定的財政收支進行的匯總與調和。各級政府控制著財政決策立法權,就控制了預算的源頭。缺乏控制的財政決策立法權,對于預算法定原則的傷害有類似“先斬后奏”的效果。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的“四萬億”救市計劃。這一案例突出地反映了政府重大財政決策對于預算的綁架作用。政府在2008年11月9日公布了“四萬億”救市計劃。在中國,當政府公布了這一計劃,就沒有人懷疑這一計劃是否能順利進入預算,實際情況比人們想象的更為順利。2008年12月1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委員長會議——而不是人大常委會會議——同意預撥一定比例的項目支出資金,在批準之后,按照批準的預算執行[11]。在2009年及之后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四萬億”投資也沒有作為一項整體的財政預算納入預算草案,而只是將其當年投資的部分納入預算提請人大代表審議[12]。
這一事例固然反映了人大權力的虛置,但根本上還是因為政府的決策權過于強勢。當政府作出決策時,通常也已經經過各級黨委的討論,人大所能做的就只是事后準認了。這從根本上消滅了預算對于財政支出的控制功能,嚴重損害了預算法定原則。與重大財政決策權類似的還有行政立法權,尤其是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權力以及政府對重大項目的審批權,當它們基本完全由政府掌握時,都具有同樣的效果。
(二)基本模式
結合上文對預算法定要求的歸納,我國實現預算法定的基本模式應該是:充分運用人大的規范權力,實現全過程法律控制。前半部分較容易理解,關鍵是后半部分。
全過程法律控制要求對預算的監督向上游和下游擴展。向上擴展到預算前過程,包括立法、政策制定、項目審批等,向后擴展到預算后過程,主要是法律責任的追究。這些過程與狹義的預算過程(包括編制、批準、執行、調整等)在效力上密不可分,可以稱之為廣義的預算過程。
實行全過程法律控制是可行的,不僅有域外經驗作為借鑒,還有自身實踐作為基礎。在德國,《聯邦預算法》第7條第2款規定“對所有具有財政效力的措施,均須進行經濟性調查”。諸如采購、投資、補貼以及社會與稅收財政措施,包括立法計劃等公權力措施都有財政效力。因此法律規定的經濟性調查就擴展到政府擁有的這些權力。并且,經濟性調查不僅要在措施的規劃階段進行,而且在措施終結時以及實施過程中也要進行[7](P57)。在我國,一些地方也有了類似的實踐。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些實踐中,“全過程控制”的理念比較相似,但參與控制的主體卻有所差別——北京市的模式著力于增強和改進人大的監督權[13],而湖南省的模式則以改進財政部門的監督體制為核心[14]。這反映了“法律控制”理念的差別。根據孫笑俠教授的總結,法律控制的方式主要有規則性控制、過程性控制、補救性控制、自治性控制、內部性控制、合理性控制等[15](P191-294)。其中,內部性控制難以擺脫“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的困境,但這偏偏是我國對政府的預算行為進行控制的主要手段。因此,加強法律控制主要是完善其他法律手段,尤其是規則性控制和過程性控制。這兩者分別體現了人大的規范權力在實體和程序方面的應用。
(三)保障措施
充分運用人大的規范權力只能提出法定的要求,預算法定原則還要求建立機制保證法定的要求得以實現。這指向了預算法定的保障措施:在關鍵環節建立人大的直接權力。直接權力是相對于規范權力來說的,前者是指人大直接采取行動或作出決定,后者是人大為政府權力設定規范。
需要建立人大直接權力的關鍵環節有:
第一,預算前過程中的重大財政決策和立法程序。作為預算法定的前提條件,對這兩者的控制,可以通過規范的方式,也有必要在特定事項上建立人大的直接權力。這類事項主要有:(1)數額巨大的跨年度財政支出項目。“四萬億”救市計劃即是一例。在歷史上,寶鋼、三峽建設都是經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會議審批的,但法律中對于這種審批權尚沒有明確規定[3]。(2)對財稅立法權有所侵擾的行政立法和決策。這兩類事項的共同點在于:具有跨預算年度的影響力,人大難以通過年度預算案進行控制。
第二,預算審批和調整中的決定程序。目前,人大的主要權力是整體批準或整體否決,只有少數地方(河北、湖北、山西、廣東、廣西、海南和重慶)規定了在人大審議過程中提出修正案的程序。整體否決權太過激烈,人大不會輕易行使,這就使得法律的規范性要求容易落空。
第三,預算監督中進行調查的程序。調查的核心是獲取信息,充分的信息對于預算監督意義重大。目前,人大缺少主動獲取信息的方式:《憲法》規定的特定問題調查程序不適合作為常規的監督手段,而《人大監督法》規定的執法檢查手段雖是常規手段,但由于檢查人員的專業性缺乏保障,當與控制著審計部門的政府相比較時,人大在信息方面處于明顯劣勢,這同樣會使規范性要求失效。
第四,預算后過程中進行問責的程序。目前,人大進行問責主要是通過以下程序:(1)聽取政府報告;(2)在報告基礎上提出意見,必要時可以作出決議;(3)督促政府部門進行整改或問責;(4)聽取政府關于整改情況的報告。這一程序以同體問責為核心,本質上是依靠行政部門自覺改正,這會讓其他的法律控制措施都淪為裝飾。需要注意的是,第四個環節的問題與前三個略有不同,人大并不是缺少直接問責的權力:質詢、罷免、撤職等都是法定的權力,只是它們長期處于凍結狀態。嚴格來說,在這一環節,并不是建立人大的直接權力,而是恢復。
(四)具體建議
基于上文分析,有一些具體的建議:
第一,修訂《預算法實施條例》以及地方《預算監督審查條例》,讓新《預算法》增加的規范性要求落到實處。例如第一條規定的“公開透明”、第三十六條規定的“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財政政策相銜接”等,都需要進一步細化。
第二,修改《人大監督法》,建立人大對重大財政決策的批準權。新《預算法》規定“在預算執行中,各級政府一般不制定新的增加財政收入或者支出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制定減少財政收入的政策和措施;必須作出并需要進行預算調整的,應當在預算調整方案中作出安排”。這是基于預算調整程序建立了人大的批準權,其精神與本建議一致,但僅能適用于影響年度預算的政策,不適用于面向未來,尤其是能夠產生跨年度影響的決策。后者背后往往還有黨委參與,一旦得以確定必然有“綁架”預算的效果。黨的十八界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按此要求,讓經過黨委討論的重大財政決策進一步履行人大批準程序才更符合依法執政的要求。
第三,完善《人大議事規則》,發展對預算草案的修改權和部分否決權。這兩個權能的發展并不需要修改《預算法》,因為其內涵于《預算法》所賦予的預算審批權之中。實踐中之所以難以行使,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大的議事流程中缺乏對具體問題進行充分討論、辯論的程序。因此,這一目標完全可以通過對人大議事規則的完善得以實現。
第四,修改《審計法》或《人大監督法》,建立人大對審計機關的領導權力。這主要為了保證人大獲得充分的信息用于監督。改革審計機關的領導體制是最根本的對策,但這在短期內難以實行。這一建議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得到部分滿足,例如:(1)完善人大委托審計部門進行專項調查的制度;(2)探索在人大內部建立一個輕量級但專業性強的專門委員會,負責與審計部門日常溝通;(3)探索由人大在審計機關派駐獨立監督員的制度;等等。
[1]韋森.從“稅收法定”走向“預算法定”[EB/OL].http:// finance.ifeng.com/a/20140902/13048116_0.shtml,2014-09-02.
[2]劉劍文.論財政法定原則——一種權力法治化的現代探索[J].法學家,2014,(4).
[3]盧凌波.中國全國人大預算審查監督與預算制度創新[D].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
[4]肖鵬.美國政府預算制度[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
[5]蔣勁松.論1995年關國預算大戰[J].美國研究,1996,(4).
[6]神野直彥.財政學——財政現象的實體化分析[M].彭曦,顧長江,韓秋燕,范麗香,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7]羅伯特·黑勒.德國公共預算管理[M].趙陽,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
[8]劉劍文.財稅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林慕華,馬駿.中國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預算監督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2,(6).
[10]審計署.中央部門單位2013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和其他財政收支情況審計結果[R],2014,(20).
[11]華國慶.預算法的理念與中國預算法的完善[J].法學論壇,2009,(4).
[12]陳少英.《預算法》修訂中若干預算監督問題之探討——以“四萬億”投資為切入點[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5).
[13]謝素芳.北京人大:監督覆蓋預算全過程[J].中國人大,2013,(22).
[14]財政部駐湖南專員辦課題組,周偉華.論項目支出預算全過程監管模式的構建[J].財政監督,2008,(1).
[15]孫笑俠.法律對行政的控制——現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釋[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河之洲]
李培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解志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88
D9222.21
A
1004-4434(2015)10-01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