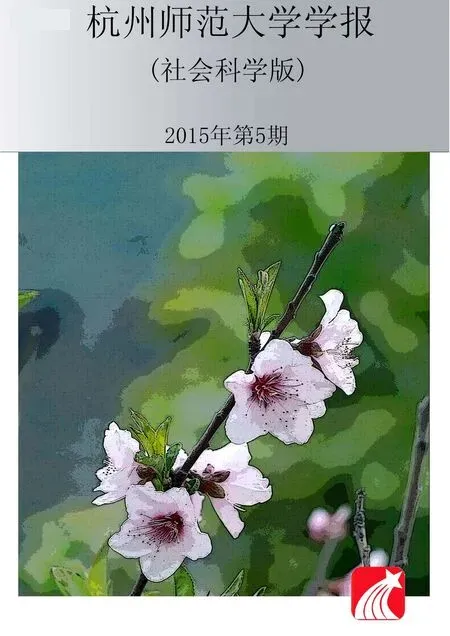周代東土紀國地望訂補
朱繼平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周代東土紀國地望訂補
朱繼平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綜合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在周代東土紀國地望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古紀國當位于今山東壽光市孫家集鎮咼宋臺商周遺址一帶,其東南紀臺鎮紀臺村的“紀臺城”漢代城址則為漢晉時期的劇縣故城。由此可以基本澄清長期以來相關學界對周代紀國與漢晉劇縣故城地望的混淆局面。
周代; 紀國; 紀亭; 劇縣故城; 紀臺城; 咼宋臺遺址

然而,對這樣一個曾經作為周室拓展東土重要代言人的古老國族,當今學術界對紀國地望的認知卻處于相對混亂的狀態。相關論說中,除據傳世文獻籠統言之在今山東壽光以南外[3](卷9齊地名“紀”條,P.351)[4](PP.292-294)[5](P.17)[6](P.460)[7](P.73),另有兩種較具體的說法主要是基于相關考古調查資料得出的。一種認為紀應位于壽光市孫家集鎮的咼宋臺遺址一帶。[8](P.18)從發表時間來看,該說提出較早,且其結論以考古試掘資料為基礎[9](P.51-55),并結合實地踏查與文獻梳理之后所得,可信度較高,然并未得到應有的關注與采信。另一種觀點認為紀國故地在今山東壽光市南紀臺鎮紀臺村“紀臺城”①此說較早見于杜在忠《壽光紀器新發現及幾個紀史問題的再認識》,收入《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98頁。,由于此論主要出自考古學界,擁有作為一手研究資料的地位,因而盡管其提出時間偏晚,但后來者居上,征引者如云②目前持此論且影響較大的考古資料及研究論著,以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年,第333頁)最具代表性。該書由國家文物局組織山東省的地方考古精英編寫,在資料性質上無疑屬于最可憑信的第一手資料,權威性與參考價值均毋庸置疑,在考古學界與歷史學界的使用率和影響之高自不待言,由此足見紀臺城說的廣泛影響。一些大型數據庫和考古學研究著作均采其說。如臺灣“中研院”史語所開發的“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中,對器號為00014的紀侯鐘出土地點的標示便是“山東省壽光市紀臺鎮紀王臺村紀侯臺”(按,“紀王臺村”當為“紀臺村”之誤),參見網址http://app.sinica.edu.tw/bronze/rubbing.php?00014。又如曲英杰《史記都城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412頁;徐龍國《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06頁,等等。,對史學界的影響亦頗
大*如唐致卿主編《齊國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3-104頁;唐敏等編《山東省古地名辭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06-107頁;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先秦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8頁;李玉潔《齊國史》,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94頁;王克奇、王鈞林主編《山東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頁;[元]于欽撰,劉敦愿等校釋《齊乘校釋》“紀城”條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99頁;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8頁,等等。。依常理判斷,若紀臺城果為周代東土紀國故地,而文獻所見紀國活動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且于春秋早期為齊所滅,那么該城址的主要使用年限至少應可上溯至春秋時期。但經過上個世紀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兩次實地調查與試掘,考古工作者已基本明確“紀臺城”的使用時代不早于戰國,以兩漢為主,資料整理者在發表簡報時卻未發現這一點與文獻記載之間存在明顯矛盾[9][10](PP.239-240),實在令人費解。
可見,關于周代紀國地望的認知還存在亟待厘清的疑問,基于這一現狀,本文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結合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對兩周前后姜姓紀國的地望及相關問題進行重新梳理和補正。粗陋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指正。
一
由于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紀侯譖齊哀公而致后者被周天子烹殺這一慘劇,紀國因此成為歷代注疏家們重點關注的古國之一,有關兩周前后東土紀國地望的文獻記載與考訂,自漢代以來便多見于各類地理志書之中,總的來說,大致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漢書·地理志》菑川國劇縣條下,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古紀國,今紀亭是”*今本《漢書·地理志》注作“故肥國,今肥亭是”,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34頁。王先謙《漢書補注》指出:“兩肥字,皆紀之誤”,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816頁。,后《續漢書·郡國志》亦載北海國劇縣“有紀亭,古紀國”。[11](郡國四,P.3473)此其一:紀亭說。至北魏,酈道元《水經·巨洋水注》則云劇縣故城即古紀國。[12](P.2211)此其二:劇縣故城說。《水經注》在中國古代沿革地理志書上所具有的經典地位,造成了此說在后世的廣泛流布*如[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12,“國于紀”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6冊,經部170,春秋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41頁;[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卷1,收入《清經解》第2冊,卷25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第238頁;[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7,“紀”國條,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97頁。。然而,《水經·淮水注》篇中,又有贛榆北紀鄣城為紀子帛之國一語[12](PP.2568-2569),此其三:紀鄣說。至南宋鄭樵撰《通志略》,又云紀初都紀鄣而后遷于劇*[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都邑》(上冊)周諸侯都:“紀都紀,遷于劇。”元注:“紀,本在東海故贛榆縣紀城是。劇在青邱臨朐縣東壽光縣西,亦名紀,音訛為劇。”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69頁。,此其四,可稱為遷徙說。
由是觀之,歷代地理志書中有關紀國地望的記載,可歸納為漢劇縣紀亭、漢晉劇縣故城、紀鄣城以及先紀鄣后劇縣等四種說法。其中,最后一說的出現可能是鄭樵意欲兼顧《淮水篇》與《郡國志》相關記載,以使《水經注》中的兩處內容不致互相抵牾,故此說實可并入第三說。按,就酈氏紀鄣說(包括先紀鄣后劇縣說)而言,清代仍有學者征引*沈欽韓引《山東通志》即從此說。參見《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一,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條,收入《清經解續編》第3冊,卷598,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第75頁。,然此說實有混淆紀國與莒之紀城的嫌疑。因此,畢生追隨其師楊守敬的熊會貞,在充分體會《水經·淮水注》篇相關內容的前后文意之后,推斷指出所謂“故紀子帛之國。《谷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兩句當為后人所加,并非《水經注》原文。[12](卷30,P.2569)此說可資憑信。加之,阮元曾言清代有山東壽光縣人得一西周晚期器紀侯鐘于“紀侯臺”下[13](3.1.2),此“紀侯臺”正隸屬于今壽光市境,可證西周晚期的紀國當確在魯北之域,又為否定紀鄣說增添了一條實物佐證。
既然與紀鄣城相關的兩種說法存在上述疑問及反證,那就僅剩下紀亭、劇縣故城二說有待進一步分析。那么究竟哪種說法更符合史實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須弄清紀亭和劇縣故城之所在。又由于紀亭屬漢劇縣所轄,因而實際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明確漢劇縣、也就是酈道元所謂劇縣故城的確切位置。
按,“劇”本戰國齊邑名,即《魯連子》所謂“朐、劇之人辯”者也。[12](卷26,P.2212)漢初置劇縣,本屬齊國,文帝時改屬菑川國[14](卷28下,P.1634),后漢屬北海國。*《續漢書·郡國四》載北海國有劇縣,見第3473頁,中華書局,1965年。晉屬東莞郡,《左傳》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杜預注“紀國在東莞劇縣”,即就此而言。可見,杜預一說與應劭、司馬彪漢劇縣有紀亭為古紀國說是一致的,表明漢晉時人皆以周代紀國故地位于漢晉劇縣轄境之內。漢劇縣,即上引《巨洋水》篇所謂“劇縣故城”,《括地志》稱“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見《史記》卷11《孝景本紀》“菑川王賢”下《正義》引,中華書局,1982年,第441頁;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下《正義》引,第2949頁。唐青州壽光縣位于今山東青州壽光市東北不遠,漢晉劇縣故地應大致在今壽光縣南約15公里處。
《水經·巨洋水注》載:“巨洋水又東北徑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12](卷26,PP.2211-2213)巨洋水亦名巨昧、巨蔑、朐彌等,今名河。[15](卷170,P.390)以今地圖正之,此水在今壽光境內大致呈西南—東北流向。既然酈氏言巨洋水流經劇縣故城西,則漢晉劇縣當位于今河東岸。今壽光市南紀臺鎮紀臺村有一名“紀臺城”的城址,恰位于河東岸。經考古調查得知,該城址平面呈圓角長方形,面積約1550×1200m2,城內地面采集物雖包括戰國時期的泥質灰陶半瓦當、簋殘片,但以大量漢代陶器碎片、瓦當和方磚等為主。[16](下冊,P.333)同時,其城墻經解剖后發現,第一期墻垣疊壓在戰國遺存之上。[10](P.240)這些考古發現都表明,紀臺城的使用年代可上溯至戰國時期,城垣的修筑年代則為漢代,可證該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當在兩漢時期。因此,從位置與年代上分析,該城址當可對應上引《巨洋水注》篇所記載的“劇縣故城”,也就是說漢晉時期的劇縣當設立于此。
從《巨洋水注》篇的文意分析,酈道元以此劇縣故城為漢晉劇縣舊城,也就是古紀國,此說粗看起來似與前揭應劭、司馬彪、杜預諸說并無二致,然深究便不難發現二者最大的差異在于:酈氏徑直以劇縣故城為古紀國,而應、司馬、杜三氏卻僅言古紀國屬漢劇縣,或者更確切的表達應為:古紀國在漢所置劇縣境內,至于劇縣所治與紀國都邑是否在一處,則未明言。不過,由應劭、司馬彪與杜預之說可以確定的是,漢劇縣下所轄之紀亭為古紀國,當可知紀國都邑實際上指的是“紀亭”。那么,這個紀亭今天又在哪里呢?
二
上節我們已分析指出,酈道元在《水經·巨洋水注》中將漢晉時期的劇縣故城誤讀為周代東土紀國都邑之所在,從而與漢晉時人的認識有了偏差。不過這種偏差在唐宋時期的地理志書中并未得到明顯延續。杜佑在《通典》古青州北海郡“壽光”條下指出:
漢舊縣也。有淄、澠二水。古紀國城在縣西南,亦有寒浞國。又漢劇縣故城在縣南。[17](卷180,P.4771)
結合上文分析可知,這里的古紀國城當指《續漢志》之“紀亭”,也就是紀國都邑。由這段引文亦可知,唐壽光縣南同時存在古紀國城和漢劇縣故城,其中前者位于縣西南,后者位于縣南,表明古紀國城當在漢劇縣故城以西。
又《太平寰宇記》壽光縣下載:“紀城,古紀侯之國,今廢城在縣南。”又云:“劇南城,故紀國,漢曾為劇縣,今城亦在縣南。”[18](卷18,P.358)據這兩條記載分析,“紀城”與“廢城”皆指古紀侯國,即漢晉時人所謂“紀亭”;而漢劇縣在北宋則被稱為“劇南城”,與紀城均位于北宋壽光縣南。不過,《太平寰宇記》所謂劇南城為故紀國一句,似乎可以理解為劇南城亦屬紀國故地。
在此基礎上,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就紀城與漢劇縣故址并存于唐宋壽光縣南總結道:
劇城,(壽光)縣東南三十里。亦曰劇南城,春秋時紀國地。漢置劇縣,初屬齊國,文帝分置菑川國,都劇。景帝三年與吳、楚叛,國除,并入北海郡。尋復為菑川國治。后漢初,張步據齊地,都劇。建武五年,耿弇討敗之,帝幸劇。尋為北海國治,以齊武王子興為北海王,都于此。三國魏廢北海國,以縣屬東莞郡。晉因之。劉宋仍屬北海郡,后魏因之,北齊省。
又緊接著此條下云:
紀城,亦在縣東南。劉昭曰:“劇縣西有紀城。”亦曰紀亭,故紀國也。城內有臺,俗曰紀臺城。《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戰國時為齊之劇邑。《魯連子》云“劇、朐之人辨”,謂此。漢因置劇縣。[19](卷35,PP.1638-1639)
由以上兩段引文可知,顧氏對漢劇縣故城和紀城別之甚明:位于壽光縣東南30里的劇城又名劇南城,為漢晉劇縣故城,春秋時屬紀國地,這與《太平寰宇記》是相同的;同樣位于壽光縣東南的紀城又名紀亭,乃紀國政治中心之所在,因城內有高臺,故俗稱為紀臺城,戰國時為齊之劇邑。同時,顧氏所引劉昭《注補》一語表明,漢所置劇縣雖由齊劇邑得名,但兩者位置并不在一處,紀城在漢劇縣以西,此說與《通典》一致。在這里,顧氏所謂劇城與紀城皆在壽光縣“東南”,與《通典》所載紀城在壽光西南之說有異,其緣由當出于明代壽光縣城較唐代壽光縣城向西有所遷移之故。*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清壽光縣因明壽光縣而來,且壽光故城在清壽光縣以東,可見明清壽光縣治當較唐宋壽光故城有所西移。參見《大清一統志》卷170青州府建制沿革“壽光縣”條及卷171青州府古跡“壽光故城”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4、396頁。
由上述文獻當可獲悉,史籍中有關漢代紀亭與劇縣相對位置的記載提示我們當在漢晉劇縣故城、也就是今“紀臺城”城址以西,去尋找古紀國都邑的蹤跡。那么,是否存在這樣的遺存呢?答案是肯定的。
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壽光市南約9公里的孫家集鎮咼宋臺、鮑家樓、釣魚臺、高松、樓子李、豐順王、二甲、岳寺李、胡營、大李家等相毗鄰的自然村落,發現了大面積的商代和西周遺址,其中尤以咼宋臺遺址遺存最為豐富。咼宋臺東距河西岸約1公里,遺址高出周圍地面8—10米,總面積約8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達3—4米,地面采集有西周時期的銅觚、爵、戈,陶簋、鬲、簠、罐、豆、盆,以及陶拍、骨器、蚌器等,西南700米還發現了大型的西周骨器作坊,是目前所見淄流域最大的一處商周遺址。[9](PP.51-55)這一發現表明,位于河西岸以咼宋臺遺址為中心的商周遺址群,不僅在年代上正可與周代紀國相對應,也合于唐宋及后世地理志書有關漢紀亭與劇縣相對方位的記載。
嚴格來說,據今咼宋臺遺址和“紀臺城”的相對位置判斷,漢晉劇縣故城實際位于古紀國正南(圖1)。盡管考古所見這種實際方位關系與文獻所載稍有偏差,但若以河為方位判斷坐標,西岸的咼宋臺遺址的確位于東岸的“紀臺城”以西,這一點對于對方位關系要求不甚精確的古人來說是再合理不過的經驗性觀察。再聯系《太平寰宇記》稱漢劇縣為“劇南城”的記載分析,“劇南城”一名顯系取其位于齊劇邑以南之意,這也從側面證明以咼宋臺遺址為古紀臺、今“紀臺城”為漢晉劇縣故址的認識是正確的。
結合以上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當可確證,今壽光縣紀臺鎮紀臺村的“紀臺城”實際上就是上引文獻所載的漢晉劇縣故址,亦名劇南城,位于河東岸。而所謂紀城或紀亭,當是位于以壽光縣南孫家集鎮咼宋臺村為中心的商周遺址群,地處河以西,現存高于周圍地面8—10米的咼宋臺遺址則當為顧祖禹所言紀城內之高臺——“紀臺”。其實這一點,早在20世紀80年代,王恩田先生在進行實地踏查時已得出明確的認識,并進一步指出,咼宋臺遺址所代表的“紀臺”應該就是酈道元《巨洋水注》篇所謂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混墓側旁的高墳,紀侯鐘也很可能出于此處。[8](P.18)這種判斷是可信的。可見,今人稱漢劇縣故城址為“紀臺城”,包括《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在內的一系列資料與研究論述,實屬以訛傳訛,不足為信。

圖1 咼宋臺商周遺址群(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壽光市文物圖》改繪)
三
上兩節綜合文獻與考古材料,使周代紀國故城與漢劇縣的相對位置關系及確切地望均得以明確。在此基礎之上,還有必要對明清時期相關記載進行一番重新審視,以澄清某些長久以來的錯誤認識。
首先,來看看《齊乘》卷四“紀城”條:
壽光南三十里,春秋之紀國。《通志》曰紀本在東海贛榆,后遷劇,亦稱紀。城內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
城旁有劇南城,漢劇縣也。《爾雅》云:“七達謂之劇驂。”北海劇縣有此路。[20](P.299)
由上文分析可知,于欽關于“紀城”的這兩段記載,可謂對錯參半。首先,引《通志》之紀都遷徙論如前文所述,并不可信。其次,以紀城旁有劇南城,為漢劇縣,由前引《太平寰宇記》文可知是正確的。以此可推測,于欽所謂位于壽光南三十里、城內有俗曰紀臺、城旁又有漢劇縣故城劇南城的“紀城”,當指的是今位于河西岸以咼宋臺遺址為核心的商周遺址群,而俗曰之“紀臺”指的正是咼宋臺遺址。也就是說,在于氏看來,紀國都邑舊址與漢劇縣故地顯然不在一處。在這一點上,下文所引《大清一統志》“紀城”條文甚得其本意,倒是現代點校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出現了誤讀。*今《齊乘校釋》一書在“紀城”條下指出:“今為‘紀國故城’遺址,位于壽光市紀臺鎮紀臺村、黃孟莊、馮家莊周圍”,并引相關考古調查資料進一步予以佐證。中華書局,2012年,第299頁。
再來看看《大清一統志》中的相關記載。該書在青州府古跡“劇縣故城”條下云:
在壽光縣東南,故齊邑。《魯連子》:朐劇之人辯。漢初置劇縣,屬齊國。文帝十六年,以悼惠王子賢為甾川王,都此。后漢為北海國治。晉初改屬東莞郡。惠帝后累經改屬。《晉書·地理志》:元康十年,分城陽之大劇,屬高密國。漢有二劇縣,故謂此為大劇也。《宋書·州郡志》:劇縣,晉屬瑯邪,宋還屬北海郡。《水經注》:巨洋水徑劇縣故城西,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九十七里。北齊省。《括地志》:故城在壽光縣南三十一里。《寰宇記》:謂之劇南城。又昌樂縣有廢劇縣,在縣西五十五里,城內有紀臺。疑此為漢甾川國所治之劇,而在壽光縣東南者,則漢北海郡屬縣也。[15](卷171,PP.396-397)
聯系前文所述,可知此段文字當有三處訛誤。其一,劇縣故城當為漢劇縣,因戰國齊之劇邑而置,但并非置于劇邑舊址。齊劇邑為古紀國舊都,亦漢劇縣之紀亭,前引顧祖禹文已言明,漢劇縣后世又稱“劇南城”,亦可為旁證。其二,據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地理志》校勘記可知,晉元康只九年,且所分城陽之“大劇”,實指“大”“劇”二縣,其中“大”有可能是指晉東莞郡之廣縣,后為避諱隋煬帝而改。[21](卷15,P.469)據此則,《大清一統志》有關“大劇”得名緣由的推測實不可信。其三,從這段文字最后兩句的表述可知,《大清一統志》并未將漢劇縣與紀國故地合二為一,而是以昌樂廢劇縣為漢菑川國治,而壽光東南劇縣故城為北海郡屬縣。
今按,“昌樂縣有廢劇縣”句應出自《太平寰宇記》,原文作:
廢劇縣,在縣西五十五里。《地理志》云:劇,故紀城也。漢置劇于紀城,后漢為縣,屬北海郡。……魯連云:“孟子,劇之辯者。”
緊接著又云:
紀臺,在縣西六十里劇城內,高九尺。《地理志》云劇縣,昔紀侯國臺,紀侯所筑。[18](卷18,P.366)
這里與“劇”相關的地名有三個:廢劇縣、紀臺、劇城。就上述文字本身所表達的意思分析,廢劇縣位于昌樂縣西55里,而紀臺“在昌樂縣西六十里劇城內”,即劇城在昌樂縣西60里,內有紀臺。由此可知,廢劇縣當在劇城以東5里,二者相去不遠。今按,今山東壽光在昌樂西北,這種相對位置古今未變,換言之,昌樂位于壽光東南,那么位于昌樂縣西的廢劇縣和劇城當位于壽光以南,其位置與《寰宇記》所載壽光縣南的紀城和劇南城是一致的。又由前文分析可知,紀國故城、齊劇邑故地當在咼宋臺商周遺址群一帶,其中咼宋臺遺址即文獻所謂“紀臺”。可見,上引《太平寰宇記》文中,位于昌樂縣西60里且內有紀臺的“劇城”,當指的是壽光縣南之紀城,也就是齊劇邑、故紀國之都,而位置稍偏東五里的“廢劇縣”則當對應漢劇縣,也就是劇南城。
據《漢書·地理志》,西漢有二劇,分別屬漢北海郡和甾川國,據班固自注可知,屬北海郡者為侯國,屬甾川國者則為縣。關于漢二劇之關系,王先謙《補注》辨之甚明:“此在北海者,專為侯國,故與甾川之劇,雖壤地相接,而名稱不混。后漢并入北海,則甾川之劇,轉為北海之郡治。《續志》北海劇下自注,與甾川國劇下應劭注同。……足為確證。”[22](卷28上,PP.723-724)既如此,作為漢之劇縣的則應屬甾川國,結合上文所述可知,甾川之劇當即《水經注》之劇縣故城,也就是唐宋時期的故劇城、劇南城、廢劇縣,今指壽光市紀臺鎮紀臺村之“紀臺城”城址。至于北海郡侯國之劇,顯然另在他處。*西漢北海郡與甾川國接壤而各在東、西,故北海郡之劇侯國理當在甾川國劇縣以東。顧祖禹以北海之劇在明昌樂縣西北(《讀史方輿紀要》卷35,山東昌樂縣“劇魁城”條,中華書局,2005年,第1641頁),王先謙從之(《漢書補注》卷28上,第724頁)。今《中國歷史地圖集》稱甾川之劇為劇縣,而稱北海之劇為劇國,并將其分置西北與東南(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21頁),顯然是十分正確的。至于北海劇國的確切所在,《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以為在今昌樂縣西十里(轉引自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第425頁)。因此,上引《大清一統志》以昌樂縣西55里的廢劇縣為漢甾川國治,是正確的,但以壽光東南劇縣故城為北海郡屬縣則表述不甚清楚,易引起混淆。
又,《大清一統志》在“紀城”條下載:

《大清一統志》在論述紀國故地時僅言其在“壽光縣南”,與前述所言劇縣故城在“壽光縣東南”相較,可知其以紀城在漢劇縣以西。該書將歷代有關紀國故地的幾種說法進行列舉之后,引青州府志指出古紀國故地——紀臺城——位于、堯二水之間。
據《水經·巨洋水注》,堯水“出劇縣南角崩山,即故義山也。……水即蕤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蕤水所出也。北徑山東,俗亦名之為青水矣。堯水又東北徑東、西壽光二城間。……堯水又東北注巨洋。……《地理志》曰:蕤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12](卷26,PP.2215-2221)則北魏時堯水是巨洋水的支流,不過到了清代堯水流路發生了重要變化。楊守敬指出:“《漢志》蕤水入海《注》言,堯水注巨洋,則在今壽光縣東入河。今堯河自臨朐縣東北流,至壽光縣東南,入丹河。”[12](卷26,P.2221)今按,丹河位于河以東,堯河入丹河,則其水道更當在河以東。如此,位于、堯二水之間的紀臺城位于河東岸,結合前文所述,此紀臺城當指位于今紀臺鎮紀臺村的漢劇縣故城。可見,《大清一統志》雖正確地區分了紀城與漢劇縣,惜在確定紀城具體位置之時,仍據舊志所言,錯誤地將紀國故地與漢劇縣混為一談。
成書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葉圭綬所撰《續山東考古錄》一書,亦對研究山東地理沿革具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對劇縣故城及其與古紀國關系等問題有如下文字:
甾川國劇縣故城在南二十五里。《水經注》:“劇縣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九十七里。’”按:此即紀國城,今故址內猶有故臺。……按:漢有兩劇縣。一屬北海,今在昌樂,而西北去紀城四五里。一即紀城,甾川國治之。名同地近,后人稱隸北海者為劇南城以示別。酈道元已混兩為一。《通典》以一為紀國,以一為漢縣。《寰宇記》本之,而誤兩城皆紀國,蓋世不知漢有兩劇縣也久矣。[23](卷16,PP.435-436)
據前文分析可知,在上引文字中,葉圭綬以漢甾川國劇縣為紀國城,所犯之誤與酈道元如出一轍。又以位于清昌樂境西北距離紀城四五里的為漢北海郡之劇,為兩宋時人所謂劇南城。可見,葉氏所犯之誤,一方面在于沒有弄清楚紀城與漢劇縣故城分屬兩地這一事實,另一方面還在于未理清北海之劇與甾川之劇的地望,而是將三者混為一談,從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亂。
四
綜上所述,通過對考古調查與傳世文獻的對比研究可知,王恩田先生有關紀國地望的認識是可信的:周代東土紀國當在今山東壽光市南孫家集鎮以咼宋臺自然村為中心的商周遺址群一帶,其中心遺址咼宋臺則應即漢晉以后志書中的“紀臺”。至于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紀國故地的“紀臺城”城址,應為漢甾川國治之所在,也就是漢晉及后世所說的劇縣故城、故劇城、劇南城、廢劇縣。二者并非《水經注》所謂合二為一的關系,實際情況應是周代紀國故地至戰國時為齊國劇邑,漢代則稱紀亭,屬劇縣所轄,換句話說,漢劇縣雖因齊劇邑而置,但并不是在原址所置。
在《水經·巨洋水注》篇誤混兩者為一地之前,漢晉時人對漢劇縣與周代紀國故地的區分是十分清楚的。同時,該書《淮水注》篇所提出的紀曾都于贛榆紀鄣一說,在后世亦無太多市場。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唐代,但到了兩宋時期情況有所變化。一方面,因宋初析壽光縣長壽鄉于營邱而置昌樂縣,《太平寰宇記》在青州壽光縣下對紀國故地、漢劇縣進行區分的同時,亦于新置昌樂縣下載縣西有廢劇縣、劇城,其行文也似乎在暗示,時人對西漢時期劇縣、劇國的認識已經出現一定模糊了。到南宋時期,又出現了鄭樵《通志略》為彌合《淮水注》篇與《續漢志》相關說法所提出的先都紀鄣后遷于劇之說,然此說對后世影響并不大,清代僅有少量征引,未造成太多混亂。到了元代,于欽所著《齊乘》一書雖引鄭樵說,然在區別紀城與漢劇縣一問題上仍是比較清楚的,這當是由于于氏作為齊人,又長期在齊地任官,因而能夠廣泛收集整理文獻,并結合實地調查,得出較正確的認知。直至明末清初,顧祖禹所撰《讀史方輿紀要》,其在紀國故城、漢劇縣、甾川之劇與北海之劇等問題上,都得出了清晰且合于事實的結論。
延至清代,集中國古代沿革地理研究之大成的《大清一統志》在紀國故地與漢劇縣之別一問題上,雖依據前代志書相關記載后尚能辨析清楚,但在紀國故地及漢二劇之確切地望等方面,卻因循《青州府志》等舊志之誤。究其致誤之由,一是受早期文獻之誤導,缺乏更加審慎的辨析,二是缺乏實際調查,不加辨析地征引《青州府志》一類的方志之書。到《續山東考古錄》一書,則或主要由于撰者學識有限而有對早期文獻的一系列誤讀,以致發生了更多的錯誤。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G].北京:中華書局,2007.
[3]錢穆.史記地名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三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0.
[6]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7]逄振鎬.山東古國與姓氏[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9]壽光縣博物館.壽光縣古遺址調查報告[C]//海岱考古:第一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
[10]王建國,李玉亭.壽光縣紀國故城遺址[C]//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1]司馬彪.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2]酈道元,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13]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M].清嘉慶九年(1804)刊本.
[14]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5]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6]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
[17]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8]樂史.太平寰宇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9]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
[20]于欽.齊乘校釋[M].劉敦愿,等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
[21]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2]王先謙.漢書補注[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
[23]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M].王汝濤,等點注.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沈松華)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Ji State in Zhou’s Eastern Area
ZHU Ji-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bout the location of Ji State in the Zhou’s eastern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locations of Ji State and Han’s Ju County, which have been confused in man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bout Zhou’s eastern states. According to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s well as the field work, Ji State should be located at Guosongtai Shang-Zhou Site which belongs to Sunjiaji Town, Shoug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o the location of Han Ju County, it is near to the south-east of Ji State and is nowadays called Jitai City, a town site built during Han dynasties.
Zhou Dynasty; Ji State; Ji Ting; old city of Ju County; Jitai City; Guosongtai Site
2015-06-07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青年項目“西周東土族群認同研究”(11CZS007)的研究成果。
朱繼平(1977-),女,湖南常德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師,主要從事先秦歷史地理研究。
歷史研究
K224;K928.6
A
1674-2338(2015)05-0043-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5.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