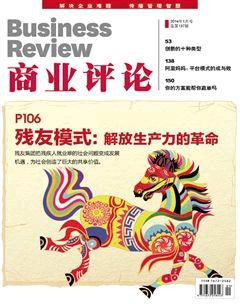彼得·圣吉:讓思想停下來
學習是一種本能。小孩在上學之前已經開始學習了,比如學走路,他們并沒有接受權威性的教學,而是在不斷地實踐中學會的。學習需要動力——內心強烈的渴望。只有想要學習的人才能取得成果。
犯錯是學習的必由之路。回想一下,當老師第一次用紅筆給你打叉時,你是什么感覺?肯定很不好受。逐漸地,孩子會開始揣測老師的標準答案。同樣,員工也會揣測老板的想法。然而,建立一家成功的企業并沒有標準答案,我們要營造一種文化接受那些因創新而犯錯的人。
根據我有限的經驗,大部分中國公司的管理者都想控制局面。公司是一個有生命的組織體系,而不是一臺需要受到控制的機器。你有沒有試過控制孩子?結果怎樣?他嘲笑你,專門和你對著干是吧!因為他是一個有生命的個體,不是機器,你不能控制他,只能影響他。
殼牌公司(Shell)的研究發現,大部分《財富》五百強公司的壽命只有三四十年,壽命超過兩百年的公司僅有18%。如今,平均每十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五百強公司消失。很多公司在當時非常成功,資金雄厚、人才濟濟、技術先進,占據了不錯的市場份額,為什么沒有活下來?答案很簡單,消失的公司都是按照機器的方式來管理的,管理者主要關注賺錢、投資回報率。他們認為公司就像一臺賺錢的機器,輸入資金、原材料、人力等資源,產出利潤。
大家有沒有想過“人力資源”意味著什么?“資源”在英語里指等待著被使用的東西。如果把人看作資源,也就意味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人必須隨時待命受企業支配。企業是一個有生命的組織體系,就像一個家庭,你不能控制它,只能影響它。層級制有時在企業里的確很有效,可以有效確保執行。但是當你要制定戰略,決定企業運營方向時,就不能把人看作資源,而是要分析人們的內在動機,關注人們的感受和熱情,那樣我們的企業才能持續發展。
現場提問
我們企業非常渴望打造一個學習型組織,具體應該怎么做?
你是怎么學會走路的?看書了沒?有沒有老師教你?沒有吧。你學會走路,是因為周圍的人都在走路,你可以看到。你要是摔倒了,爸爸媽媽會跟你說沒關系,創建了一個支持你的環境。所以,你需要伙伴,一個人是不行的。
人們經常想讓我告訴他們該怎么做,但情況沒有這么簡單。我原本是一個學習系統的工程師,了解工具和練習的重要性。我喜歡和大家分享工具,這樣才能幫助大家。《第五項修煉》介紹了很多工具、方法,希望它能激發人們采取行動。
“團隊核心學習能力”就像一個板凳,如果想要板凳穩定,就離不開三條腿:
第一,激發熱望(aspiration),包括自我超越和共同愿景。如何將你的激情和熱望植入團隊的核心學習能力?我們希望組織成員能夠擁有共同愿景,樂意分享這份激情和熱望。
第二,開展反思性交流(reflective conversation),包括發現心智模式和深度匯談。英文的“深度匯談”(dialogue)源自希臘詞“dialogos”。深度匯談指意思的順暢表達或者流動,仿佛是流淌在人們之間的意義溪流,它使所有對話者都能夠參與和分享這一意義溪流,在群體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識,并且能夠讓大家發現自己的心智模式。很多團隊的匯談層次非常淺,稍一交流就產生矛盾,大家就開始發脾氣,匯談便會終止。這對于企業來說是致命的。
第三,理解復雜事物(complexity),包括系統思考。你應該了解每個獨立個體或者事物之間的復雜性。比如,價值鏈是怎樣的過程?中間每個環節發揮什么作用?如何影響組織文化?文化又如何影響組織的生存?兩者之間的聯系是什么?客戶告訴我,它們不是學習型組織,而是正在學習變成學習型組織。這句話非常重要,你會發現,如果我們將時間的維度放大到永遠,每一個階段都在學習。
舉個例子,銷售業績不好怎么辦?有人會提議降低成本,從而提高利潤。但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是產品質量下降,這樣產品賣不出去,利潤肯定也會跟著下降。于是10%的員工不得不下崗,而留下的員工必須加班加點,祈禱自己不要失業。他們就不愿意互相合作,只關注自己的小世界來取悅老板。裁員的副作用是產能下降、士氣下降、合作氛圍變差,最終利潤下降得更多。這些副作用不是馬上出現的,會有延遲。我們希望快速解決問題,有些解決方案起初看上去確實立竿見影,但是它有副作用。如果我們沒有在一開始系統思考,結果會很糟。
如何讓我們的愿景變得有力量?您自己是如何學習的?
我在洛杉磯長大,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基本上我是在一個日本家庭里長大的,我一直對東亞哲學很感興趣。這個時代正是東西方融合的時代,我認為中國所需要的創新會對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說到儒家、佛學、日本哲學……很多傳統智慧都有一個共同的本質,關注人的發展。學習型組織的基石就是人的發展,而不是人力資源。我敬重的成功經理人都是以人為本的典范。有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工作就是把更多的人吸納進來組織更大規模的生產,產生更好的結果。這個結果可以幫助人們成長。還有一位在公共事業領域工作的女性職業經理人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很重視人的感受,比如員工的文化背景、傳統價值觀所帶來的影響。我想當東西方文化交匯時,我們需要思考如何積極利用、正確引導由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所帶來的一些影響。
中國人可能不是特別理解,為什么我會依賴諸如孔孟之道的哲學來進行企業管理。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受益匪淺的學習過程,我學會了如何以和為貴,凡事適度。每個國家的傳統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既然稱之為傳統,那就必然有它長期存在的理由。在建設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更多地想一想深層次的心智追求、開發或者發展。助人成長,你的企業就一定能夠健康成長。所以任何一種培育人的傳統,都應該對整個企業的發展有積極作用。
我知道您與南懷瑾先生私交很好,請問佛教的禪宗和企業的經營哲學有什么關系?
我很幸運,十五年前機緣巧合認識了南懷瑾先生,我很感恩。佛教更注重思想、境界的修養。而儒家是以社會大環境為背景的一種培養型文化,比如思想、心智和身體、大眾、宇宙的聯系。我個人更傾向于儒家。
有一次上課我讓七位領導者冥想:第一,先想怎樣停止;第二,真正停止下來。第一步就是讓思想停下來,你才能夠真正看清周圍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被你個人的體驗、野心、欲望所控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智模式,包括你對家庭、事業的企盼,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如果你能夠撥開云霧,就會看到自己最重視、最想要實現的東西。如果你真的能夠敏銳地感知一件事情的發展狀態,那么你在處理問題時應該沒有太大阻力。
第二步,學習停下來,確確實實地停下來。在你眼睛看到的東西背后有什么?怎樣才能控制自己的思維模式或者思維流動?我遇到10%的人說,他們是我的粉絲,特別喜歡學習型組織,但是我敢說他們其實不知道真正的學習型組織是什么,核心價值是什么。可能有極少的一部分人真正明白。我非常衷心地希望能夠創造一種氛圍,讓大家加入進來,對自身有更深層次的認識。我是物理專業的,我花了十年時間從不同方面來理解系統。我們的習慣、思維模式經常是固定的,它們不一定正確。而公司、組織都有自身的運作規律。如果不關注公司、組織的個性特點,被外界的客觀條件或者環境所干擾,蒙蔽了雙眼,這也是有問題的。
大量中基層員工對企業績效有直接的影響,他們很難有機會聆聽大師演講,在建設學習型組織中如何把他們納入進來?
很顯然,今天在座各位都是精英,我們有很好的機會學習和深度匯談,但那又怎樣?其實沒什么用,除非我們把所學帶回組織。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背后的心智模式非常好。
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才能完成組織的使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參與進來的準備,人的教育背景、社會層次不同,每個人都需要開發。管理者的責任就是要把人納入這個體系,這很重要。
最近有個激勵人心的故事發生在密蘇里的一線鋼鐵工人身上,我們對他們進行了六個月的培訓。鋼鐵工人一般都沒上過大學,所以我們分成兩個團隊:一個是針對管理層的團隊,管理層都是MBA;另一個團隊針對工會12位管理人員,其中有2人上過大學,其他人都是中學畢業。我們做了一個實驗,讓兩個團隊分別深度匯談,最后把兩組人放到一起。這是很危險的做法,因為他們之間的勞資關系很糟糕,人們在開會的時候甚至會互相扔椅子。
你們猜哪個團隊進步更快?哪個團隊更理解深度匯談的本質?是工會的人。管理層是通過數字來管理公司的,工會是通過跟人打交道來做管理的。工會人員對深度匯談的理解突破了我們的認識。他們說我們懂了,深度匯談跟我們每天的工作一樣。工人的工作是制作煉鋼的容器,盛放滾燙的鋼水,直徑有五到七米。如果容器不夠堅固,人就會死。工人說深度匯談就是要造一個容器,把人的能量放進去,如果這個容器不夠強,人們就會互相殘殺,因為我們沒法控制人的能量。這就是洞察力。我們對于深度匯談的概念完全被這群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改變了。最后我們邀請惠普、英特爾的人來鋼廠開會,鋼廠的管理層也在,但工會領導了會議。你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些人的樣子,塊頭很大的鋼鐵工人,他們講的故事非常真誠感人。工會主席非常真誠地說,他真正學會了該怎樣思考,不只是工作,還包括家庭。他過去不善于傾聽妻子的意見,現在開始學會了傾聽。
所以不要低估一線員工的力量,他們可能教育程度不如你們,但這也是一種優勢,他們可以經常敞開心扉,而且可以更快地敞開心扉。我們這些上學太多的人可能會處于劣勢,因為我們的腦子被之前的經驗占據了。
請大家思考,我們怎么把學到的東西帶回企業?要確保所有人都做好準備,你不能強迫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