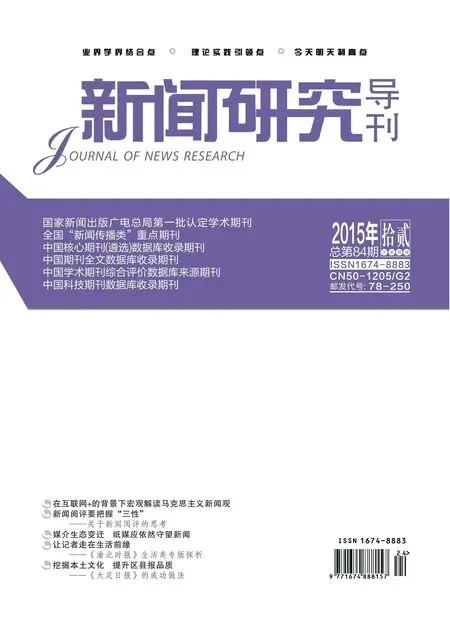認真研究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
——《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及應對》序
董天策
(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重慶 401331)
認真研究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
——《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及應對》序
董天策
(重慶大學 新聞學院,重慶 401331)
進入Web2.0時代,網絡的內容生產模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通俗地說,就是從專業人員織網變成所有用戶參與織網。換言之,隨著BBS、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技術的應用,用戶不僅瀏覽、消費網絡信息,而且分享、生產網絡信息。這樣一個開放而自由的網絡空間,給人們帶來了信息社會的種種好處,同時也為謠言的滋生和傳播創造了技術條件,以致網絡謠言近幾年來頻頻出現,日趨活躍,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并迅速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
無論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還是故意捏造的消息,抑或未經證實的傳說,謠言自古就有,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輿論現象。在現代傳媒產生以前的傳統社會,謠言的傳播途徑主要是口耳相傳,局限于人際交往與群體互動,擴散的速度相對緩慢,傳播的范圍相對有限,所產生的不良社會影響相對較小。現代傳媒產生以后,人類的信息傳播具備了突破時空限制的強大能力,但由于報社、通訊社、電臺、電視臺這些傳統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具有嚴格的審核程序與把關機制,所以現代傳媒產生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并沒有造成謠言的肆意妄為。然而,Web2.0網絡技術的應用,卻開創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發布任何信息的技術可能性。正是憑借著這樣一種技術可能性,加上網絡用戶的匿名性或脫域化,謠言仿佛一夜之間插上了翅膀,在網絡空間大肆橫行。
作為謠言的一種形態或類型,網絡謠言并未脫離謠言的基本特點,只不過其發布及主要傳播過程是通過網絡進行的。既然如此,網絡謠言的泛濫是否就是由于網絡技術的發展而造成的呢?問題遠沒如此簡單。對于當代中國來說,互聯網的發展與改革開放、社會轉型、全球化進程是相互交織的。技術上的Web2.0時代,恰好是改革開放日益深化、社會轉型日益加劇、利益分化日益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時期。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大凡社會變革時期,謠言傳播總是異常活躍。這就意味著,網絡謠言的盛行不僅與網絡技術的發展有關,而且與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有關。
2012年4月1日,中國網發布的一篇文章《網絡謠言》指出,網絡謠言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為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溫床;科學知識的欠缺,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可乘之機;社會信息管理的滯后,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機會;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公信力的下降,使公眾的不信任感增強;國內一些媒體及少數黨員干部紀律觀念淡漠,助長了政治謠言的傳播;網絡推手制造謠言,強化了謠言的擴散,挾持了網民的意見;商業利益的驅動,是謠言滋生的經濟動因;西方敵對勢力制造和利用各種謠言,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暫且不論這個分析是否全面,就其著眼于現實的社會環境而言,是相當有道理的。因此,研究網絡謠言,除了關照網絡技術,還必須重視社會現實。
早在2010年,郭小安博士就敏銳而及時地介入了網絡謠言的研究,成功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及應對策略”。從課題的設計來看,著重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切入網絡謠言研究,也是頗有見地的。歷經數載的潛心探討,郭小安博士如今奉獻出30萬字的專著《當代中國網絡謠言的社會心理研究》。書稿完成,作者囑我寫序,不便推辭,得以先睹為快。
讀完書稿,我以為這部專著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對研究對象的核心概念做了深入的闡述。譬如,對于謠言、網絡謠言,作者在做出自己的界定時,引述了古今中外的有關論斷,延展了有關概念的內涵,深化了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其二,對網絡謠言的研究具有多維視野與多維視角。譬如,第二章從不同角度論述了謠言的政治屬性,概括出“謠言是一種反權力”、“謠言是非正常權力的補償渠道”、“謠言是一種社會抗議,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謠言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謠言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監督渠道”等命題。其三,在若干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譬如,互聯網是謠言的助推器還是自我凈化器?謠言引發恐慌是否必然導致集體行動?究竟應當如何應對網絡謠言?對于這些問題,作者在論述了業已存在的各種觀點的基礎上,通過案例分析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其四,結合大量案例來展開理論闡述,體現出理論聯系實際的良好學風。
當然,書稿也還有提升空間。譬如,如何處理好研究傳統與學術創新的關系,讓自己見解特別是創新的見解體現得更加鮮明?如何讓論述的材料與表達的觀點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如何讓專著寫作擺脫論文寫作痕跡,體現出專著寫作固有的一氣呵成與自然圓潤?這些問題有待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加以深入思考和積極解決。好在作者非常年輕,是標準的“80后”,而且已經學有所成,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出版了兩本專著,委實不易。相信隨著年歲的增長與學養的豐厚,作者一定能夠奉獻更多更好的學術著作。
G206
A
1674-8883(2015)24-0025-01
董天策,重慶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