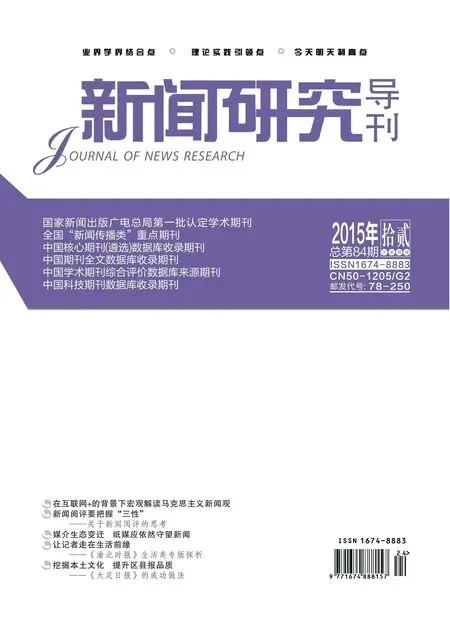淺析網絡聚合體的形成與傳播機制
許方聰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淺析網絡聚合體的形成與傳播機制
許方聰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改變了傳統的人際交往方式和群體狀態,網絡聚合體正是傳統的社會群體在網絡世界的反應。網絡聚合體在對內及對外傳播上具有異于傳統群體的傳播特征,并產生“反沉默的螺旋”效果。經過對其形成過程和傳播機制的分析,筆者認為“網絡聚合體”將成為未來輿論空間的主要力量。
網絡聚合體;缺場交往;弱紐帶;反沉默的螺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中國迅速崛起并日益顯示出巨大的變革力量。進入21世紀后,我國網民數量和互聯網普及率不斷增長。伴隨著網絡的普及和應用,人們傳統的交往、互動、傳播行為與方式被大大改變。如同克萊·舍基所言,電子媒介工具使人們打破了工業社會發展而來的組織化、機械化的僵化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一種“濕乎乎”的、富有黏性和彈力的狀態而存在,并因此形成了無數的隱形群體。這些群體的產生,是基于群體成員之間的愛、理解、共識、興趣或利益,它通過群體成員互相分享、合作和集體行動等方式迸發出力量,最終切實地改變或影響著現實生活。網絡社會正是依靠著這些“無組織”群體的自我運作與彼此互動而得以建構和維系的。
一、何謂網絡聚合體
網絡聚合體作為互聯網時代下傳統社會群體的新枝,天然地具備傳統社會群體的一些形態、結構、功能特征,同時由于聚合方式、維系手段以及目的與效果的巨大差異,又顯示出顯著的獨特性。
社會群體的形成基于一定的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則來源于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和互動。人類的交往和互動可以分為行為層面和意義層面兩類,其中又以意義層面為重心,因其是群體歸屬感與共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在互聯網時代,由于網絡傳遞信息的便捷性,現實生活中的面對面的交流與行動相比之下成本較高,人類的交往活動因而從行為層面逐漸向意義層面轉移,由此形成的網絡群體可以看作是傳統社會群體在網絡社會中的反映。
與現實社會相比,網絡社會中的人際交往具有巨大的隨意性和流動性,在網絡中游走的個人隨時可能結識任何原本毫不相干的他人,當人際交往的效率提高了,群體形成的速度也隨之加快。但另一方面,由于人際關系注意力的分散,網絡形成的群體大多具有結構松散、邊界模糊的特性,它們可能只是因為群體成員的臨時利益訴求或興趣而聚合產生,并以“接力棒”的形式得以傳遞和擴大,與傳統社會群體持續、穩定的形態相去甚遠。
基于以上特點,筆者認為網絡聚合體的定義可以歸納如下:網絡聚合體是指在互聯網或其他數字化系統環境中,以電子媒介為交往渠道,以議題、共識、興趣或利益為訴求,以意義交換為目的而自發形成的相對松散、開放的網民群體。
二、網絡聚合體的傳播機制
(一)缺場交往形式
交往是社會學和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交往產生社會關系,形成社會群體。傳統社會中的交往,多以“面對面”的形式出現,交往雙方處于同一時空場域中。網絡社會的到來,打破了交往的時空限制,“缺場交往”成為主流。
其表現之一在于,與現實世界中“人——人”的直接互動方式不同,網絡聚合體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流依賴于計算機媒介,這體現了傳受雙方在空間上的互不在場。美國社會學家C.H.庫利曾提出初級群體概念,指具有面對面交往特征的、非制度化群體,如家庭、鄰里、伙伴群體。與此相對應的是制度化的、以間接交往為特征的次級群體,如學校、社團等。網絡聚合體通常不具備完整的規章制度,網民們憑借共同的興趣或話題產生聯系,沒有明確的社會目的,可以視為網絡社會中的初級群體,但網絡聚合體中的網民成員不是直接產生聯系,而是必須以計算機為中介,人與人的交流,在現實中體現為計算機之間的聯絡,天各一方的人們通過操控計算機而與彼端的他產生聯系。
在另一方面,網絡環境下,傳受雙方在時間上也可能是彼此缺場的。互聯網海量的信息儲存功能使得人們傳送出的信息不會像口頭傳播那樣稍縱即逝,也不會像書信那樣易于損滅,人們可以跨越時間產生聯系。對于網絡聚合體而言,通過這種交往方式,其成員之間可以因信息產生聯系,而不依賴于特定條件下的社會關系。
因為這種“缺場交往”的存在,人們得以不受時空阻隔地傳遞經驗、分享信息、建立聯系,網絡聚合體也就以一種邊界模糊、結構分散的狀態存在。在特定的議題之下,不同時間、地域的網民以信息為紐帶發生“隱形交往”,而在議題不斷得以發散和延伸之后,聚合體的范圍逐漸擴大,其緊密程度也相應降低。
(二)弱紐帶結構
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拉諾維特提出弱紐帶理論。他指出,強紐帶關系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頻繁接觸的社會關系,如親友、同學等。這種關系十分穩定,但我們從中獲取的新的社會認知是有限的,與之相對應,通過弱紐帶和我們聯系在一起的是我們偶然認識的網友、生意場上的客戶、被朋友無意間提起的人等等。他們與我們的交往頻次極少,但可供獲取的認知范圍卻是廣泛的。因此,一個人的弱紐帶越多,他有可能涉足的圈子就越多。同樣,兩個互不熟悉的圈子也依賴于弱紐帶將它們相連。
互聯網特別適于發展多重的弱紐帶。有學者指出:“在網絡社會之前的社會,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弱紐帶關系,但是,唯有網絡這種媒介的出現能夠使人們的弱紐帶關系實現可以互動外化的形式。”[1]互聯網承載著海量的信息,其傳播和接收主體都是活躍于互聯網社會中的人,當我們游走于網絡世界時,也就等于穿梭于無數的弱紐帶之間。網絡聚合體并非是界限分明的排他性群體,相反,由于每個成員所接觸的圈子差異甚大,網絡聚合體之間也呈現出一種彼此交叉疊加的狀態,那些處于重合區域的成員,也就扮演了群體之間的弱紐帶角色,成為其他成員通往新群體的一扇大門。正是在這種弱紐帶的聯系中,松散的網絡聚合體彼此相連,達成平衡,同時,不斷有新的網絡聚合體在弱紐帶的廣泛牽引下破土而生。
(三)“反沉默的螺旋”效果
“沉默的螺旋”是由德國傳播學者諾依曼提出的著名傳播理論,指基于個人在“害怕被孤立”的心理壓力之下趨向于附和社會多數意見或保持沉默,從而形成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另一方則無限沉默的公共輿論現象。這種沉默現象主要受心理上的恐懼、痛苦、尷尬、從眾以及社會權力結構與文化的影響。但是,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公眾表達獲得很大程度上的解放,為“反沉默的螺旋”式的意見和言論提供了生長的土壤。
許多學者關于“反沉默的螺旋”的研究都從網民個體視角出發,分析個人意見表達時的心理和行為變化。其實,許多網絡聚合體有意無意間也正是充當著“反沉默的螺旋”的載體。首先,由于互聯網具有高度開放的特征,各種觀點得以表現、碰撞,弱勢意見群體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比較容易尋覓到與自身意見一致的其他群體成員,他們彼此相互聯系后就能夠形成網絡聚合體,從而利用弱紐帶網絡將弱勢意見不斷擴大。其次,網絡聚合體中的成員多為網絡匿名,且聚合體以一種非制度化的形式呈現,優勢意見聚合體中的成員在接觸了弱勢意見之后立場發生動搖,可以隨時擺脫現有群體加入弱勢聚合體,這種“意見叛變”是一種自由行為,沒有制度懲罰的壓力。
“反沉默的螺旋”效果可能會拯救少數人的真理,同時也可能造成非理性意見的極化,但總體而言,在維持公眾輿論平衡方面,這種效果的存在是必要且合理的。
三、“網絡聚合體”的未來——“聚合體社會”
網絡聚合體作為互聯網時代中社會交往與運動的重要角色,已經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本文刻意避免了以“群體”為其命名,而是選擇了“聚合體”的說法,有兩方面考慮:一是為了顯示出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群體的特征——“聚合”。傳統的群體均是以“群”的方式出現,整體性較強,凸顯其結構的緊密性多于個體成員的作用和地位。而聚合體則是數字化個人彼此交往組合而成的異類群體,其強調“聚合”的意義。有“聚合”,便也有“離散”,這喻示著個體成員在其中較強的能動性和主體地位。二是為了淡化個體成員的身份色彩。在現實社會中,某一群體成員出現時往往帶有群體身份標簽,群體的意見直接轉嫁到個人身上。而在網絡社會中,在個人之間形成聯系的不是身份與角色,而是意見與觀點,這是一種意義層面上的關系,而非群體制度那般僵化生硬。
隨著“網絡聚合體”搶占輿論空間,“聚合體社會”即將到來。這并不是否定正式組織和制度性群體存在的意義,而是認為“聚合體”形式更能夠適應網絡時代人們意見自由交換、個性充分釋放、人際交往范圍日益擴大以及廣泛參與社會發展進程的需求。在缺場交往的形式之下,以弱紐帶彼此相連的聚合體,實際上構成的是一種橋接型社會。在這種條件下,以一座橋連接另一座橋,以一群人溝通另一群人,隨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加濕”了,社會的運動加速了,這便是“聚合”迸發而出的強大力量。
[1]鄭志勇.網絡社會群體研究[A].中國傳播學論壇:2006中國傳播學論壇論文集(Ⅲ)[C]. 2006.
G206
A
1674-8883(2015)24-0084-02
許方聰(1991—),女,安徽宿州人,南開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