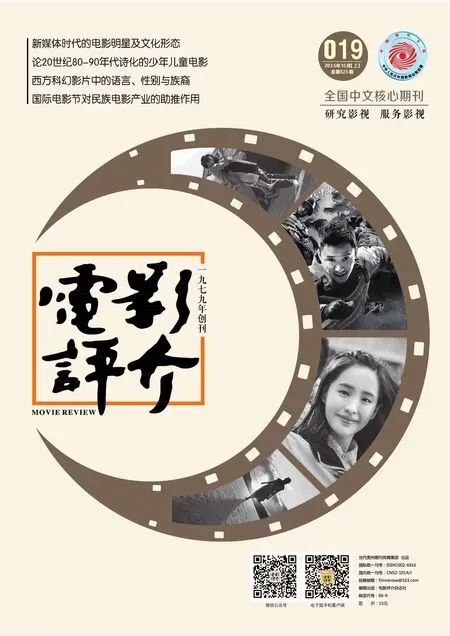“意義解構”與“大眾心理”——從無厘頭電影《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說起
趙士萌 施旭升
“意義解構”與“大眾心理”——從無厘頭電影《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說起
趙士萌施旭升
施旭升,男,安徽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導,文學博士,主要從事藝術傳播學,藝術學理論,戲劇戲曲學等方面研究。

無厘頭電影源自香港,是新浪潮電影運動影響下的突出表現,是上個世紀80年代香港電影中的特有類型。無厘頭電影的特點是對傳統電影中的固有模式進行肢解和再創,顛覆受眾傳統認知,以此表達人們的迷茫、困惑以及對于社會的一種態度,蘊含著強烈的批判色彩。作為這種無厘頭電影的典型文本樣式的《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講述了取經之前的孫悟空因欲殺唐僧而被觀音菩薩懲罰,轉世投胎成至尊寶后與蜘蛛精、白骨精相遇的傳奇故事。該片于1995年1月22日在香港首映,在第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入圍最佳編劇獎,周星馳也因該片獲得了第二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獎最佳男主角獎。本文的立意就在于通過對于《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的解讀,以追尋無厘頭電影的話語機制與意義之源。
一、意義解構的兩個方面
(一)對于時間意義的解構
時間見證了影像藝術的歷史變遷,也見證了影像藝術的無窮力量。于我們而言,不僅驚異于影像藝術帶來的感官震撼,更享受影像藝術帶給我們的溫情與冷酷。影像藝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一場模式化的創作過程,形成了影像藝術固有的風格特點,其中“敘事性”便是影像藝術中的突出特點之一。“敘事性”是影像藝術的一個“傳統”,一個關于人們認知的“傳統”,一個約定俗成的潛在契約。按照固定的影像運動模式,固定的人物性格化塑造,將具象化的影像進行敘事性連接,以達到符合固定主題的類型化影像。無厘頭電影就是在傳統影像藝術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一次“意義”解構。在傳統的影像藝術中,大多沿用傳統的人情敘事方式或者線性時間的
敘事方式,其目的是給受眾呈現一個“圖解性”“敘述性”的清晰線條,以最適合受眾的表達方式演繹影像的意象世界。這種敘事方式不僅在思維方式上易于接受,也在“滿足受眾期待”這一點上獲得了肯定。
在以《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為代表的后現代影像藝術中,首先打破的就是受眾的線性思維方式,對整個故事進行“解構化”的處理。換言之,《大話西游《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是完全意義上的突破。即對于整個敘事鏈條做了模糊化處理,影像的每一次運動即為突破,雖全在敘事之中,實則全在“世事”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預見的清晰敘事鏈。“不是虔誠地景仰經典,相反,是用種種浮夸的方式破壞經典。既定的敘事成規之中的意識形態由于不倫不類而遭受嘲笑,自行瓦解。”[1]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對于“線性時間”的重復化處理,也就是“穿越”,通過“月光寶盒”將一維的線性時間拓展成多維空間,通過對“線性時間”的多維化處理來建構故事,同樣的故事不同的維度有著不一樣的結果,而這一點正是對于固定模式下線性時間結果一元化的否定。現實維度和虛擬維度的界限模糊處理,敘事鏈條的多維化,都是對于傳統敘事的顛覆。受眾在觀看傳統影像藝術時,可以較為清晰地預知故事鏈條,也就是可以對電影的故事結構進行大致預測。而在《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中受眾的“預測”受到了挑戰與顛覆,使得整個故事處于一種懸空的位置,受眾處于一種困惑與不解的狀態中,完全被顛覆式的電影敘事所控制。
(二)對于“具象體”的意義解構
這里的“具象體”指的是人物或動物等“生命體的具象化呈現”,在傳統的電影模式中對于“具象體”的性格化塑造往往是基于敘事基礎之上的,需要有“語境”作為支撐。在無厘頭電影中,“具象體”同樣有語境。但是這個“語境”超出了文化圈的范圍,換句話說,是無厘頭電影的“具象體”不受社會等價值層面的束縛,而身處造化之中,如此“語境”下的“具象體”為無厘頭電影提供了一個闡述自我更為廣闊自由的空間。“具象體”的創造性重塑。不基于傳統意義上的敘事之中,并不意味著無厘頭電影沒有敘事,無厘頭電影的敘事性在于通過對“具象體”的創造性重塑,將“具象體”之間作“繪畫式”的勾連,以一種“全新關系”的敘事方式存在。創造性重塑的基礎在于對“傳統思維”和“傳統故事”的褫奪。這就是受眾在無厘頭電影觀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不解”和“無奈”,其實質在于自身“思維模式”的懸置。
“具象體”的“陌生化”處理。“具象體”的創造性重塑,根本在于對“具象體”的陌生化處理。“陌生化”一詞是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提出的,“陌生化效果,又譯為間離效果或間情法,在布萊希特戲劇理論中有多種內涵,它作為一種表演方法,包含著辯證地處理演員、角色、觀眾三者之間的關系及舞臺美術原則、藝術效果等內容。這是布萊希特在他的史詩戲劇實踐中提出來的一個美學概念。”[2]“陌生化”重塑是將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作陌生化處理。什克洛夫斯基理論中提出“感知自動化”,“陌生化”重塑就是要打破這種“感知自動化”的狀態,給予受眾陌生驚奇的新鮮感,在變化中吸引受眾。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曾言“才人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制錦繡花樣,無不隨時變更。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于傳奇一道,尤其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花,今夜復對此花,則不持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愧其不新矣。”[3]變則活,活則通,通過不斷的變化吸引受眾也是電視劇人物形象“陌生化”重塑的目標所在。以《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中的人物為例,受眾認知領域內的“孫悟空”應是“無所畏懼、愛憎分明、勇于斗爭”。《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則對于這樣一個受眾熟知的人物進行了重新的塑造“瘋癲狡詐無法無天”“嬉笑打鬧無厘頭搞怪”,甚至也對孫悟空進行了愛情的詮釋。這種陌生化的處理讓人物的開放性更強,給予了人物以“當代思維”與“人性”,將傳統觀念所賦予的東西一并拋除,還原成了一個真真實實的人。“具象體”陌生化處理突出表現為人物語言思維和語言傳統的重新建構。人物語言的風格與人物形象,電影主題等一系列因素息息相關。傳統影像藝術中的語言相對來說比較規整,符合我們的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無厘頭電影的語言特點是“碎片”化的組接,將受眾的傳統思維模式打亂重組,將人物語言進行重新的組接。《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中人物的臺詞呈現出了“碎片化”“去敘事”“去意義”的特點。《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中有一句經典臺詞“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情擺在我的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于此。 如果上天能夠給我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對那個女孩說:‘我愛你!’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孫悟空固然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但是對于已經被還原成真正的人來說,他可以,正是因為臺詞的“本我”復歸使得人物有了鮮活的“人性”特質。值得注意的是,臺詞設立的不同維度也讓臺詞有了一個現實存在的語境,這也是《大話西游之
月光寶盒》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臺詞與語境的契合度。正常維度下的孫悟空與“異”維之下的孫悟空是“一體兩面”,通過對不同維度“孫悟空”的不同處理,使得“孫悟空”這一多元化形象合體為一,成為了具有多重人格的“人”。多重人格中包含著“本我”與“超我”“自律”與“他律”,生生死死來來往往,總歸逃不過“自己”,“自己”便是“空”“道”“玄”,正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
二、內在于大眾心理的“酒神精神”
大眾心理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下表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80年代的香港經濟繁榮,思想開放,人們思維方式多元化,受眾娛樂化需求強烈。香港電影界也出現了許多新的類型,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受西方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無厘頭電影。大眾心理的變化對于香港無厘頭電影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其中蘊含著強烈的娛樂化和商業化訴求,也正是香港無厘頭電影的出現昭示著一個全民狂歡時代的到來。
《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這部顛覆經典的無厘頭電影,讓我們看到了“癲狂”看到了“搞笑”,看似娛樂化的背后,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意義指向,即來自內在于大眾心理的“酒神精神”。需要明晰的是“酒神精神”并非等同于“癲狂”“搞笑”,它是一種“忘我”之態,一種最純粹和最原初的自我表達。“酒神狀態的迷狂,它對人生日常界限和規則的毀壞,其間,包含著一種恍惚的成分,個人過去所經歷的一切都淹沒在其中了。”[5],“癲狂”與“搞笑”是一種淺層次的外在表達,用一種“癲狂搞笑的孫悟空形象”來顛覆受眾對于經典形象的認知,打破日常生活行為的界限。《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正是通過“意義解構”這種方式來完成自我認知的,其中不乏有百思不得其解的話語,有令人困惑的故事,將現實與夢境結合,解構“敘事性”,建構“本質自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種迷狂也傳達出了大眾對于本真生命追尋的強烈訴求,一種大眾狂歡時代下的新的認識自我的方式。
三、“意義解構”與“大眾心理”的正相關關系
“意義解構”與“大眾心理”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體現在通過“意義解構”重新詮釋和解讀純粹藝術,究其本質是對于終極“美”的探尋,即“意義解構”是追求“美”的一種方式和途徑。從這一層面來說對于“去偽存真”后純粹的自我認知,同樣也是影像藝術所追求的本質,是所有藝術共同追尋的目標。對于無厘頭電影來說“去意義”化的目的在于對于“人性”本質的探求和呈現,是對于“純粹藝術”的一種追尋方式。無厘頭電影的“迷惑不解”也是對于現實人生的一種困惑,多維度下人性“一體多面”的一種困惑。《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將這種現世困惑代入影像,傳達出了一種無處不在的時“空”觀,“空”而有之。這里的“空”便是“純粹藝術”的核心所在。究其本質,“意義解構”其實是展現“大眾心理”的一種方式和途徑。在古典電影中有故事性非常強的好萊塢式類型化影像,其敘述性的影像風格也滿足和展現著“大眾心理”,不同的是,以“意義解構”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后現代影像更能趨向于“大眾心理”的精神實質,也就是說“意義解構”是更趨近于表現“大眾心理”精神實質的一種方式。
“純粹藝術”有著更加開放的特性,它以更加開放的態度和思維去“創造藝術”,現今,“影像藝術的圍城”是對于“藝術性電影”和“商業性電影”抑或“藝術商業電影”最好的詮釋。正是這座圍城構成了現今電影市場的矛盾體,在不斷發展的對立統一前行。
總而言之,影像藝術是人類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一種剖析人性的方式。雖然很多影像藝術將視角投向了更為既得的商業利益,但對于“純粹藝術”的追尋仍舊沒有停止。影像藝術在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的方向因其多元化的發展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是對于“純粹藝術”的探求仍舊是影像藝術發展的基本路向。
參考文獻:
[1]南帆.夜晚的語言:當代先鋒小說精品[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1.
[2]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M].丁揚忠,李健鳴,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191.
[3]李漁.閑情偶寄[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23.
[4](魏)王弼.老子道德經注[M].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117.
[5]尼采.悲劇的誕生[M].周國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8:28.
【作者簡介】趙士萌,女,山東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藝術研究院碩士生,主要從事藝術學理論、藝術傳播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