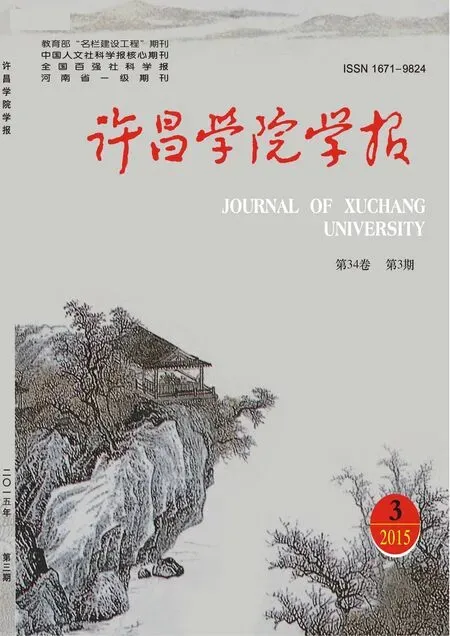讖緯與鐘嶸詩論
王 承 斌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
讖緯與鐘嶸詩論
王 承 斌
(許昌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讖緯在東漢盛行一時,魏晉南北朝時仍有相當的勢力。緯書中包含的奇特的想象、豐富的辭藻等,對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如此,讖緯還對后世文學理論影響甚大,鐘嶸的詩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讖緯影響:在詩的起源方面,他的“物感說”不同于傳統的諷諫教化論,而是在緯書“物感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對詩歌地位、作用的認識上,鐘嶸弱化了傳統詩論強調的教化作用,將詩與自然萬物聯系,從詩在天地萬物中所處的地位上論其作用,帶有一定程度的天人感應色彩;在詩歌抒發情感方面,鐘嶸表現出與傳統詩論更大的不同,很重視與“志”、教化無關的怨情,這是對緯書“詩含五際六情”、強調詩歌抒發情感的進一步發展。
讖緯;鐘嶸;詩學思想
東漢之際,讖緯盛行,漢末此風稍息,但流風余韻綿延不絕。南朝齊梁時,緯書仍有相當勢力,《隋書·經籍志》記載:“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后,又重其制。”[1]941可見緯書在當時還甚有影響,但因對統治者不利,才一再被禁。
緯書包含有奇特的想象、豐富的辭藻,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對文學創作有較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許多文人自覺取其精華,如曹植、曹丕、嵇康、阮籍、左思、沈約、謝靈運等人作品中都有緯書的影子,李善注《文選》時已指出過這一點。西晉文論家摯虞曾說過:“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2]1906肯定了讖諱對文章的作用。后來劉勰在《文心雕龍》“文之樞紐”部分專列《正緯》一章,討論緯書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對緯書也十分重視。鐘嶸詩論思想與讖緯的關系不甚明顯,前人研究鐘氏詩學思想時,多注意儒家傳統詩論和玄學之影響,論其與讖緯關系者甚少。但若深入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鐘嶸詩論與讖緯之間有較密切的關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詩之產生——物感說
物感說是六朝重要的文學觀念之一。它認為文學是“心”感于外物的結果,自然外物的變遷,引起主體的心靈波動,情不能已,自然發而為文。如《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65便是此義。其《物色》篇中進一步探討了自然景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認為春夏秋冬的更迭,使作家依次產生“悅豫之情”、“郁陶之心”、“陰沈之志”、“矜肅之慮”等,并提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3]693的觀點;《詩品》開篇即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4]1等,也是強調了人“感物生情”,詩歌自然脫口而出。
關于物感說,學界一般認為源起于《禮記·樂記》,因其中首次提到“心感于物”的觀點——“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5]661,它指出了音樂等藝術是心感于物的結果。人們將此作為物感說的起源當沒有錯,不過它未對“物”作明確界定,也未言明“物”是如何引起創作主體的內心感受,如喜怒哀樂之類情感的變化,并如何以不同藝術形式表現出來,故而還只是模糊的、不成熟的說法。
緯書繼承發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大肆宣揚符瑞、災異、譴告等天人感應現象,文藝也被其納入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中。這方面黃金鵬先生有過較詳細的論述[6]106,可參看。大體上說,緯書認為文藝可以溝通天、地、人,如音樂能“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樂緯·動聲儀》)[7]537詩歌是“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8]2123等。在這種背景下,緯書進一步發展了物感說——“詩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7]544這不僅指出了詩是詩人感于外物的產物,還指明了“感物”而生詩的具體過程是“感——思——積——滿——作”,這對后世文論產生了巨大影響。如陸機在《文賦》中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9]1即指出了寫作過程是睹物感嘆而思,悲喜之情積于內,自然發于外的過程。本文前面提到的《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所探討的自然景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也與此相關。鐘嶸論詩時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斯四侯之感諸詩者也。……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4]47其中“搖蕩性情”、“感蕩心靈”等,也明顯是心感于物后積、滿而思,最后發之于外的過程,這無疑是在緯書詩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此外,緯書“物感說”中所感之物還包括“事”,即把“事”這一現實生活引入詩論中,提出詩歌應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如《春秋緯·說題辭》中說:“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8]2123其中的“事”即指現實生活;又“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7]538其中之“事”指“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包含了社會現實內容。這里需要一提的是,緯書強調詩歌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與傳統詩論中的“美刺說”有所不同。我國很早便有將文學創作與社會政治相聯系的觀念,如先秦以來就存在的采詩觀風,強調“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5]663,便是認為詩歌是社會政治的反映。后來的《詩大序》繼承了這一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0]16等,也是強調詩歌對社會政治的反映,很少涉及政教外的其他方面。這方面前人論述已多,此不贅。而緯書中說的詩歌所反映之“事”,無論是“在事為詩”,還是“齊俗奢,陳俗利巫”,雖與“言志”及“移風易俗”的教化相關,但相比于《詩大序》等的說法,卻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化說的影響,更多地是指社會風氣,指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之事。
眾所周知,鐘嶸的“物感說”中所感之物,除指自然景物外,還包括“楚臣去境”等社會生活內容,他非常重視現實生活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可以說,鐘嶸的“物感說”存在一個轉向,即由魏晉以來所強調的自然物向社會事物的回歸,但又不能說是向傳統“感物”的完全回歸。李健先生曾專門撰文討論鐘嶸的“感物”思想,認為它“與先秦兩漢的文學教化有著根本的不同。其主要表現在:在鐘嶸的感物思想中,作家、藝術家與社會現實的感應也像與自然物象的感應一樣是自然、自由的,而先秦兩漢的文學教化是強行賦予、刻意賦予,沒有任何自然與自由可言……”[11]96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先秦兩漢時的“感物”說,不重自然物象而重諷諫教化,而鐘嶸之“感物”說,除強調“詩是個人生命對自然生命的一種感發和體察”外,還強調對社會生活中“群”“怨”的反映,并且“不像《毛詩序》那樣著眼于政教得失,而是立基于個體的哀樂。”[12]55即和政教的關系已不大,有很多是與純粹的個人情感相關,如男女戀情、個人不幸遭遇引發的怨情等,《詩品》上品中的李陵、班姬,中品的秦嘉、徐淑等均如此。他的“感物”強調的是社會生活對人心的觸動,是自由、自覺的,擺脫了刻意附會政治的因素,這更接近緯書的說法。
二、對詩歌地位和作用之認識
先秦儒家詩論給了《詩》很高的地位,但那多是和政治教化相關的。如孔子論詩時提到詩的“興觀群怨”功能,強調美刺教化、有補于世,強調詩歌在疏導人們情感、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就詩之社會政治作用而言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有了極高地位。
《詩》等文藝在緯書中也有極高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教化有關,如緯書中認為《詩》“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詩緯·含神霧》)[7]464即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認為音樂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含,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7]540即音樂潛移默化的感染力可以用來移風易俗等。這些都是從教化角度來說的。不過,《詩》在緯書中的崇高地位不全取決于此,緯書已從更高的哲學高度上對《詩》作了全新判斷。《詩緯·含神霧》中說:“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7]464由于目前所見的緯書缺失嚴重,我們已無法確知這句話的具體語境及語意所指,但有一點很明顯,它認為詩在天地之間居于重要地位,能夠成為君德、百福、萬物的始祖和本源。在這里,詩似乎成了宇宙萬物的核心。這實際上把文學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詩緯》對詩之性質的這一認識,與傳統詩論強調詩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所不同,它將詩與自然天地聯系起來,是從詩在天地萬物中所處的地位上,來認識它所能發揮的作用的。《詩緯》作者之所以能提出這一說法,當是與緯學中的“天人感應”說相聯系的。前文已經提到過,在緯學的思想體系中,文學藝術可以使天、地、人溝通聯系起來,所以,緯學中的詩論、樂論等,也就是其“天人感應”說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對《詩》之地位、作用的認識也就明顯突破了傳統教化說。
鐘嶸在這方面的認識,非常接近緯書。他對詩歌地位作用的重視,在某些方面是著眼于教化,如認為詩歌能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強調詩歌在宣泄情感,維護社會政治穩定方面的作用等。但其認識又不限于此,如在論詩歌作用時提到“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響,幽微藉之以昭告。”[4]1其中“照燭三才”一說,即隱含了緯書中文藝溝通天、地、人的思想,并認為詩之光彩可輝光、陶冶天地萬物,也是從詩在天地萬物中的地位上論其作用的。他還認為詩歌能“動天地,感鬼神”[4]1,這明顯是取用《詩大序》中“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10]2的說法,卻舍去了其中關于詩歌政教作用的“正得失”的論說,故與政教的關系更遠,帶有了一定的天人感應色彩,這些不能不說是受緯書的影響。
三、詩歌之“言志”與“緣情”
傳統儒家詩論強調“詩言志”,強調詩對社會政治的反映,強調詩有補于世,很少涉及到情。現在學界一般認為,“言志”主要是表現人的政治抱負及對政治社會問題的態度和看法,雖然它不完全排除人的情感因素,如《詩大序》中曾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吟詠性情”[10]2等,但對涉及到的“情”,多要求歸于雅正,強調“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儀”,要求詩歌表達的思想感情不能有悖于“禮儀”,不能違背封建倫理綱常,不能有損于統治階級利益;要求詩歌能從思想感情上感化人和對人進行道德規范。
相比于傳統詩論,緯書論詩有明顯不同,它十分強調詩歌的抒情性。《春秋緯·演孔圖》中說“詩含五際六情。”此條下宋均注為“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7]583其實,此“六情”釋為《詩經》之“六義”甚不恰當,難以說通。現在一般認為,這“六情”說出自《齊詩》翼奉的“六情”說。翼奉在其上元帝封事中明確說到“六情”為“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13]3168即指人之喜、怒、哀、樂、好、惡等情感,這也是漢代對人情分類較普遍的看法。如班固就曾說:“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14]382仲長統也說過:“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15]957等。翼奉提出“六情”時,特別說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13]3170,認為詩應該自由、充分地表達人的情感,這實際上是在“言志”說的基礎上融合了情感因素,將“言志”說政治方面作用同人之情感因素結合了起來。其中,“止乎禮義”方面被淡化了,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言志”說對情感的束縛。對于《詩經》研究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視角,開啟了古代詩論由“言志”到“緣情”的道路,六朝時的“緣情說”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詩緣情”所強調的思想感情的抒發,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詩教的束縛,強調“發乎情”,看不到多少“止乎禮”的要求。這一點前人論述已多,此不贅。
鐘嶸論詩時也非常強調情感,《詩品序》中明確說道:“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4]1認為詩歌和舞蹈都是性情的表現,沒有性情的搖蕩,便沒有詩與舞,從而旗幟鮮明地提出詩歌“吟詠情性”的主張。更重要的是,鐘嶸特別重視那種與教化無關的個人情感,如《詩品》極重怨情,其上品十二家詩中,提到“怨情”的達八家之多;被列為中品的一些詩人,如“凄怨”的秦嘉、徐淑詩,“孤怨宜恨”的郭泰機詩,“長于清怨”的沈約詩等,他也都給予了肯定。他所重視的這些怨情,有些與“言志”、教化相關,但也有相當部分與之無關,如班姬詩“詞旨清捷,怨深文綺”[4]94,與傳統之“志”幾乎沒有任何關系,無關教化,卻被列入上品;又評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凄怨。徐淑敘別之作,亞于《團扇》矣。”[4]197夫妻之情也與言志、政教無關,卻列為中品之首;張華雖“兒女情多,風云氣少”[4]216,也被列入中品,等等。反之,一些教化意圖異常明顯的詩作,如班固的《詠史》等,鐘嶸卻只字未提。張伯偉先生論及這一點時也曾說:“(鐘嶸)將詩歌反映的內容及效用落實于‘可以群、可以怨’二端,‘嘉會寄詩以親’即‘可以群’,‘離群托詩以怨’即‘可以怨’。而且,這種‘群’和‘怨’并不像《毛詩序》那樣著眼于政教得失,而是立基于個體的哀樂。”[12]56所以說,鐘嶸雖未完全擺脫“言志說”的影響,但無疑是沿著緯書強調詩歌抒情性這一路走下來,離傳統“言志說”更遠了一些。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緯書的詩論與傳統詩論之間雖有一些共同之處,但也有著諸多的不同。比較鐘嶸詩論與二者的關系,我們不難看出,鐘嶸論詩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傳統詩論的影響,但在很多方面卻更接近緯書。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我們對鐘嶸詩論有更清楚、全面的把握。
[1] 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2] 嚴可均.全晉文[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4] 鐘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 孔穎達.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 黃金鵬.緯書與漢魏六朝文論[J].北京大學學報,1999(4):105-110.
[7] 安居香山.緯書集成[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 陸機.陸機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孔穎達.毛詩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李健.鐘嶸的感物美學[J].文學評論,2004(5):94-101.
[12]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4]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4.
[15]嚴可均.全后漢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
責任編輯:石長平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Theories of ChenWei and Zhong Rong
WANG Cheng-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Chen Wei was preval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till popular in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strange imagination and rich rhetoric in Chen Wei's writings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t that time, many literary theorists noticed the fact and pointed it out. Chen Wei also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ry theory. Zhong Rong's poetic theory was largely affected by it, for example,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poem, Zhong Rong's poetic theory, the Wu Gan Shuo, developed from Chen Wei'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tic status and role, Zhong Rong weakened its education role; instead he contacted poetry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nd commented on poetic role from its status in the natural world. Zhong Rong als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esentment irrelevant to traditional moralizing. He further developed Chen Wei's theory emphasizing poetry emotion which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etic theory.
Chen Wei; Zhong Rong; Poetic theory
2014-10-26
王承斌(1972—),男,安徽郎溪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學。
I206
A
1671-9824(2015)03-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