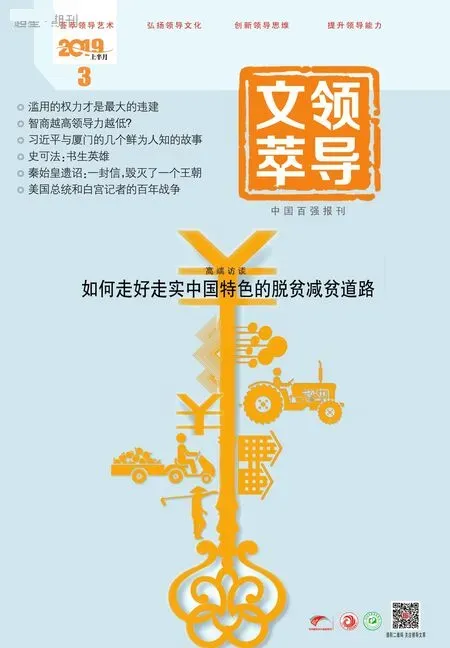時(shí)代夾縫中的魏源
□王龍
時(shí)代夾縫中的魏源
□王龍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則徐推薦下,入署理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幕下。接下來(lái)關(guān)于定海的防守,清軍將領(lǐng)們產(chǎn)生了激烈的爭(zhēng)論。有人主張堅(jiān)守定海,而魏源認(rèn)為,定海孤懸海中,難以固守,不如把兵力集中到浙江海岸上的城市,加強(qiáng)鎮(zhèn)海、寧波等地的防務(wù),誘敵深入內(nèi)河加以圍殲。魏源雖然多次據(jù)理力爭(zhēng),但意見(jiàn)完全不被裕謙采納。8月,英軍進(jìn)攻定海,定海很快淪于敵手。魏源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中毫無(wú)用武之地。
深感自己人微言輕的魏源,決意憤而辭歸。走在回家的路上,魏源心中很不平靜。他寫詩(shī)感慨道,前方炮火連天,自己卻臨陣脫逃,實(shí)在有違先前報(bào)國(guó)的初衷。可回想短短的從軍經(jīng)歷,眼看英軍狡猾至極,反復(fù)無(wú)常,而清軍將領(lǐng)們卻不悉敵情,一味胡亂指揮。朝廷和戰(zhàn)不定,左右搖擺,主政者昏庸誤國(guó),失敗明顯已無(wú)可挽回。去留彷徨之際,魏源深感憑借一己之力難以回天,不如回家去拿起筆來(lái),發(fā)奮著述,從事另一種戰(zhàn)斗。
面對(duì)前方依然接連傳來(lái)的敗績(jī),悲憤填膺的魏源開始苦苦追問(wèn):為什么一個(gè)“天朝大國(guó)”竟敗給了一個(gè)人數(shù)不多、遠(yuǎn)道而來(lái)的英國(guó)侵略者?這樣的戰(zhàn)爭(zhēng)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如今“款夷”(即簽訂和約)之后又該怎么辦?
揚(yáng)州絜園,魏源閉門謝客。他懷著“奮之奪之”的強(qiáng)烈情緒,廢寢忘食,挑燈夜戰(zhàn),著手整理擴(kuò)展林則徐交給他的文稿以及圖文資料,開始前無(wú)古人的創(chuàng)作之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在林則徐所輯《四洲志》的基礎(chǔ)上,增補(bǔ)了大量資料,完成了《海國(guó)圖志》五十卷本。死水微瀾的天朝,如同投入一塊激浪揚(yáng)波的巨石。這部石破天驚的劃時(shí)代著作,標(biāo)志著塵封千年的鐵屋中,終于發(fā)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聲強(qiáng)勁吶喊。
《海國(guó)圖志》是鴉片戰(zhàn)后中國(guó)人自主編撰的一部最詳細(xì)的世界史參考書。它全面介紹了世界各國(guó)的歷史、地理、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科技、宗教和民俗文化。魏源在該書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shuō):“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而作。”
“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這句振聾發(fā)聵的口號(hào),從此成為一個(gè)傷痕累累的民族為之奮斗的精神號(hào)角,成為一道照亮人心世道的啟明星,升起在暗夜沉沉的神州上空。當(dāng)整個(gè)清朝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之際,作為站在時(shí)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魏源挺身而出,沖破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提出“師夷長(zhǎng)技”的明智對(duì)策,可謂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然而這樣一部有用的奇書,在蒙昧無(wú)知的清朝統(tǒng)治者那里,卻如一堆廢紙。《海國(guó)圖志》被束之高閣,受盡冷遇。清廷高層絲毫沒(méi)有記取鴉片戰(zhàn)爭(zhēng)失敗的教訓(xùn),一味茍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張。
魏源去世后的咸豐八年(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請(qǐng)咸豐皇帝,將《海國(guó)圖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便使人“知夷難御而非竟無(wú)法之可御”。誰(shuí)知沉湎于酒色的咸豐帝對(duì)此毫無(wú)興趣,王茂蔭的奏折如泥牛入海。在許多守舊的朝廷官吏眼里,此書則為洪水猛獸。他們認(rèn)為中國(guó)“政教禮儀超乎于萬(wàn)國(guó)之上”,無(wú)法容忍魏源對(duì)西方“蠻夷”的“贊美”。更有甚者,主張將這本“大逆不道”的書籍付之一炬,以免遺禍大清。最終,《海國(guó)圖志》僅僅在國(guó)內(nèi)勉強(qiáng)印了千冊(cè)左右,銷聲匿跡。
1851年,日本長(zhǎng)崎港。一艘中國(guó)商船駛?cè)敫劭冢跈z查違禁物品時(shí),日本海關(guān)官員從這艘船上翻出三部《海國(guó)圖志》。仔細(xì)翻閱之后,日本人頓時(shí)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在他們看來(lái),這部聞所未聞、見(jiàn)所未見(jiàn)的奇書,簡(jiǎn)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給日本的最好禮物!
《海國(guó)圖志》為明治維新提供了強(qiáng)大的精神動(dòng)力和思想支持。主導(dǎo)改革的領(lǐng)導(dǎo)層融會(huì)貫通地總結(jié)出日本發(fā)展之路必須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shù)的結(jié)合”,加速推動(dòng)日本走上開國(guó)自強(qiáng)之路。
半個(gè)世紀(jì)后,梁?jiǎn)⒊u(píng)價(jià)說(shuō),日本維新派前輩“皆為此書(《海國(guó)圖志》)所刺激,間接以演尊夷維新之活劇”,最終完成了改革圖新大業(yè)。
1862年,《海國(guó)圖志》在大清早已絕版,無(wú)人問(wèn)津,被徹底埋入時(shí)代的風(fēng)塵之中。得知此消息,連日本人也不禁大發(fā)感慨。日本著名學(xué)者鹽谷世弘說(shuō):“嗚呼!忠智之士,憂國(guó)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獨(dú)為默深悲焉,而并為清主悲之。”
正如這位日本學(xué)者感嘆的一樣,對(duì)于魏源和他的《海國(guó)圖志》來(lái)說(shuō),書如其人,人竟類書,好像是一對(duì)苦命相連的雙胞胎。魏源的命運(yùn)和《海國(guó)圖志》一樣受盡蹉跎,最終湮滅于虛空無(wú)奈的悲劇宿命。
咸豐六年(1856年)深秋的一天,秋風(fēng)蕭瑟,草木凋零。杭州西湖附近南屏山的青石小道上,走來(lái)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他,就是半生飄蕩、憂患余生的魏源。
兩年前,朝廷有人保奏魏源繼續(xù)復(fù)職做官,但魏源對(duì)這個(gè)紛亂的世道已了無(wú)興趣,心灰意冷,對(duì)這個(gè)腐朽的王朝再也不抱任何振興的希望。他自稱“世亂多故,無(wú)心仕宦”,決心遁入空門,潛心研究佛學(xué),整理生平著述。
魏源的一生,和他所著的《海國(guó)圖志》一樣,在時(shí)代的夾縫中左沖右突,最終卻無(wú)法找到一條精神出路。他的人生命運(yùn),充滿不可思議的強(qiáng)烈反差和奇妙悖論:他出生在丘陵,卻能放眼天下;他少年得志,卻終老于科場(chǎng);他滿腹經(jīng)綸,卻不容于當(dāng)世;他學(xué)貫中西,卻皈依于佛門……魏源一生的經(jīng)歷,似乎全部成為他為之奮斗的社會(huì)圖景的反面教材。
他的命運(yùn)與時(shí)代的氛圍密切相關(guān),而那個(gè)封閉落伍的時(shí)代,也不可能為他提供真正的用武之地。這是魏源的悲哀,更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悲劇。
(摘自《隨筆》)
- 領(lǐng)導(dǎo)文萃的其它文章
- 問(wèn)世間名為何物
- 奧巴馬的外交決策小圈子
- 行政法院的設(shè)想與前途
- 資訊
- 采英拾貝
- 經(jīng)典重溫(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