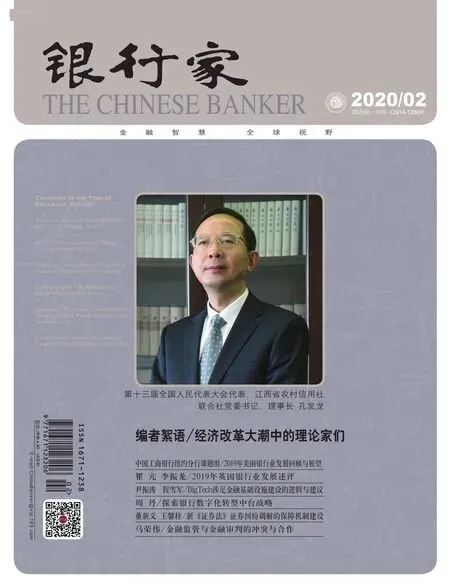2015:經濟形勢與宏觀政策
王松奇
一、 宏觀形勢——新常態下新無奈
2014年統計數據公布后,人們大都認為情況還算差強人意:GDP增長7.4%已超預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全年同比增長8.3%,廣義貨幣增長12.2%,狹義貨幣增長3.2%,糧食總產量達60710萬噸,比2013年增長0.9%,實現了十一連增。然而,作為經濟發展“風向標”,全國社會用電量卻只增長3.8%,電力消費增長創下新低,比2013年低3.7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用電量同比下降0.2%;第二產業用電量同比增長3.7%;第三產業同比增長6.4%;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同比增長2.2%。三大產業中,第二產業用電量增速較2013年下降了3.3個百分點,其中重工業用電量下滑尤為明顯,增速僅為3.6%,回落3.4個百分點;輕工業用電量增長4.2%,回落2.1個百分點。用電量變動的趨勢與中國經濟宏觀走勢和結構調整的大形勢恰好吻合,受治理大氣污染和產能過剩的影響,2014年前11個月,鋼材、十種有色金屬、水泥等高能耗產品的產量增速較2013年同期回落幅度均在10個百分點左右。除了用電量數據外,CPI僅為2%,遠低于全年3.5%的目標,PPI更是出現了連續34個月下降,這使國外的一些觀察家開始驚呼——“中國已出現通貨緊縮苗頭”。以上是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為基礎進行簡單形勢判斷,如果像民間所傳的那樣,考慮到多數地方政府都有謊報軍情的毛病,也就是說剔除GDP數據中20%左右的水分,那么,實際GDP增速也許6%還不到。
有的人可能會說,即使GDP增速不到6%又怎么樣了?中央政府指揮棒不是改變了(中央已明確不用GDP增長率作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指標)嗎?上海市政府也是在全國地方政府中率先提出不在年初確定GDP增長指標嗎?據說全國已有50多個縣市在仿效上海市政府的做法,不在年初工作規劃時確定GDP增速,現在全國上下都在用“新常態”來表達心態,這就是新形勢下的新無奈。也就是說,如果宏觀調控上不出現革命性變化,2015年的宏觀經濟仍然存在較大的下行壓力,從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說,正在經歷由過去高度依賴GDP到現在嚴重忽略GDP的態度轉變。我覺得,這也是目前需引起我們注意的一個新現象。GDP從此就不重要了嗎?當然不是。在現今經濟體量下,1個百分點損失就相當于失去6300億元財富,因此,經濟學界應當出現一種理性的聲音,對GDP絕不能抱不以為然的態度。
二、 最新動態——發改委狂批項目
為應對2015年的經濟下行壓力,發改委已低調狂批七大基建工程包,據媒體推算,投資總額已逾10萬億元,這個數額已達2008年年底為應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而緊急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兩倍半之多。想想也的確頗有意思:北大某教授兩年多前首提“克強經濟學”概念,并界定“克強經濟學”有三大支柱,曰:不刺激、去杠桿、搞改革。近兩年來,我們黨內的大筆桿子們挖空心思總結出一個新說法——“三期迭加”,即經濟增速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請注意,這里所說的“前期刺激政策”指的就是2008年底推出的4萬億刺激政策。上述種種權威聲音言猶在耳,現在就又有令人頗生小巫見大巫之慨的10萬億刺激計劃橫空出世了。這個2014年年底的10萬億與2008年底的4萬億相比,到底有哪些差別?我粗略想了一下,大致有三點:(1)形勢判斷差異,2008年底推出4萬億明確以提振內需因應危機為目的,2014年底發改委的10萬億只是“潤物細無聲”式地應對經濟下滑的基建項目儲備;(2)領導認同差異,2008年年底的4萬億曾是時任總理溫家寶果斷決策的驕傲,因此逢會便說以鼓舞士氣提振信心,2014年年底的10萬億計劃克強總理在公開場合似乎還從未提及,在達沃斯論壇演講時,克強總理還是說中國不搞大水漫灌,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3)2008年年底中國宏觀調控最大的事件不是4萬億刺激計劃的推出,而是多年以來一直奉行的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變成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這個貨幣政策風向標的徹底轉變(據說這個歷史性提法的發明人是易綱),正是從“穩健”轉向“適度寬松”才出現了銀行系統對地方政府平臺公司投資行為的強力信貸支持,并使得中國GDP增速在2010年一季度一下子就達到兩位數。刺激政策由此立竿見影。2009年,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達9.59萬億元,M2增速為27.68%,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實實在在充當了引擎的作用。盡管這個2008年年底的4萬億對產能過剩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中國通過刺激計劃的落實也形成了一大批優良的經濟基礎設施,我們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所有這些令國人自豪的東西其源有自,在相當程度上都與我們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下定決心推出的4萬億刺激計劃有關。
那么,要想讓新近的10萬億也達到2008年年底的4萬億的刺激效果,我們還差什么?
三、政策調整——財政不小氣,貨幣莫遲鈍
我們之所以信誓旦旦一再聲言為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原因就在于形勢判斷上出了問題,即低估了2015年經濟下行壓力問題的嚴重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決策層就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外需這駕馬車強勁拉動經濟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于是在“十二五”規劃中,我們曾把振興內需的希望放在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上,但在政策實踐中又出現了一些認識盲點,例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家庭消費支出大頭兒總是購房或租房支出,而衣、食、行等支出占比則要小得多,如果我們認定中國在進入中高等收入階段后也會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像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樣,住房支出成為家庭支出中的大宗支出,那么我們就要在房地產政策上有相應的調整,如果你一方面要提振國內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又對家庭消費支出的最大宗支出——住房支出采取種種抑制甚至是打壓政策,那么,提振國內消費需求的政策大目標就無法實現。另外,即使不提近10年來的房地產打壓政策,僅從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年度增速看,近年來基本都是在12%上下波動,即不管你提什么政策口號,消費需求的拓展空間實在不是很大。由此可見,如果外需在人民幣貶值背景下也難做大的改觀、國內消費需求又無力擔當“三駕馬車”中的主力,那么,對中國來說,剩下的就只有投資了,也就是說,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只能由投資這架馬車擔當。
主要用投資來拉動經濟背后的原因是中國的家庭及全社會高儲蓄率的現實,高儲蓄率就應當有高投資,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平衡增長。
有人可能會說,再加大投資產能過剩現象不是更加嚴重嗎?這個問題很好,它反映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擔心。其實投資增加不可怕,關鍵是投向的把握,如果我們把新增投資投向短板部門和過剩行業產業的壓縮、陳舊落后產能的淘汰以及節能環保和裝備制造業的升級換代上,那么,這樣投資不是越多越好嗎?至于增量資金的配置方向,我們既可以靠“看得見的手”,也可以靠“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其中,財政政策可以用預算投入、補貼資助、差別稅率等多種手段來引導社會資本在結構調整中發揮積極作用。我曾在多個會議場合評價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小氣,貨幣政策遲鈍”(當然這樣說也許有失偏頗),所謂財政政策小氣,就是我們在經濟結構調整實踐中,財政出錢或用減免稅率這種讓利手段運用得太少。根據美國等發達國家經驗,企業等微觀主體行為與一國的稅收稅率結構設計關系極大,所以,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的當下,要想實現決策層政策設計的理想目標,財政政策別太小氣,大大方方出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新的財稅辦法至關重要。
再說點兒“貨幣政策遲鈍”的問題。
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國央行集中了最優秀的一批金融專家,因此,我這里說貨幣政策遲鈍不針對任何人,而且,中國國情大家也知道,人民銀行并不是真正的貨幣當局,只有國務院才是起貨幣當局作用的機構,所以貨幣政策遲鈍問題似乎是在分析一個沒有獨立作用的中央銀行在決策中的窘境問題。
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強調堅持所謂的“穩健貨幣政策”,但細細考查,我們發現在同一穩健口號下,有些年很松有些年又很緊,所謂松緊隨意,“小大由之”。這就會給市場造成一些模糊的預期,即,你不知道它到底會出臺什么措施,微觀主體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透明度不夠是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大缺陷;二是靈敏度問題,我們雖然口口聲聲說預調微調,但市場頭寸和利率情勢已經很嚴重了,貨幣政策還常常不見出動作,實體經濟部門的形勢已經很嚴峻了,金融部門的資源配置還沒有出現引導性政策調整,這些就是我在這里所說的“貨幣政策遲鈍”。
怎樣不再遲鈍?我相信,央行的官員們比我們一定高明得多,關鍵是有沒有人能夠通過一定的形式有效地對有最終決策權的國務院領導施加影響,助其作出及時有效的宏觀調控決策。例如,眼下,通貨緊縮趨勢已越益明顯,那就是趕緊說服國務院領導降準降息并放松貸款指標管理,讓實體經濟獲得充分的信貸支持。從2014年數據看,M2增長12.2%,M1增長只有3.2%,在廣義貨幣增長與狹義貨幣增長之間竟然有9個百分點的缺口,我早就說過只有M1才能形成現實的流動性,因此,這9個百分點的活躍貨幣缺口,已預示2015年肯定是一個流動性緊缺年。
貨幣政策不要遲鈍了,趕緊采取行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