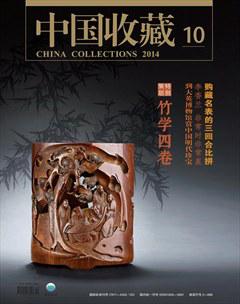竹簡,重拾文明的記憶
熊曲


散發著現代氣息的長沙簡牘博物館里,靜靜地躺著一些竹片。循著燈光,仔細地端詳,可以發現上面整齊地書寫著字,墨跡已有些淡了,字卻仍清晰可見。這些看似普通的竹片,已歷經1700多年。它們是在紙張發明且廣泛使用前,用于書寫的材料,被稱為簡牘。
在南方潮濕的環境里,這些竹簡在淤泥中浸泡了漫長歲月,卻仍能較完好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件多么幸運的事。然而,這批簡牘也曾險遭厄運。
1996年10月17日清晨,長沙市文物工作隊(翌年更名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到湖南平和堂商廈建設區域內的古井群工地里工作,突然發現有口古井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出于職業敏感,他們仔細地查看著被破壞的井口及附近,發現在褐色淤泥中裹著竹木片,于是小心地翻捋著,不禁內心一陣陣驚喜,簡牘!單位負責人聞訊后,馬上趕往了現場,一邊采取措施保護現場,一邊組織人員急忙趕赴五公里之外的湘湖漁場,對10月17日凌晨傾倒的數車渣土進行清理。這時,轟動全國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終于被發現了。
可惜的是,該井破壞十分嚴重,北半部原堆放的簡牘幾乎被鏟掘殆盡,破壞深度自現存井口起深達223厘米至270厘米,破壞面積約占整個J22井的一半。這樣,導致清理工作相當艱難。工作人員惟恐有所遺落,仔細搜尋,同時,小心翼翼翻撿著,生怕這和著淤泥的簡牘再有任何閃失。這種工作整整持續了十二天,搶救回了簡牘八十多袋。雖然,橫遭破壞部分的考古信息喪失了,文物也損毀了一些,但絕大部分的簡牘失而復得,使他們悵然心情增了一點欣慰。
這古井淤泥中的珍寶講述是怎樣一段歷史呢?簡牘主要記載的是三國吳國嘉禾元年至六年(公元232年至237年),吳國長沙郡臨湘侯國(今長沙市)的官方文書,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賦稅、戶籍、司法諸多方面。我們可以從其中一個較完整的簡冊——“吏民私買賣生口責收估錢事”中,來一睹當時社會現狀的端倪。
如圖所示的這枚木牘(圖1)保存完整,字跡清晰,用工整的楷書書寫,該木牘與六枚竹簡(圖2)是編連成冊的。按照圖片從左至右的順序,六枚竹簡上書內容依次如下:
1.市史唐玉謹列起嘉禾六年正月訖三月卅日受民賣買生口人名簿
2.士史錢賣女生口直錢八萬嘉禾六年正月廿□貸(?)男子唐調收中外
3.估具錢八千
4.大女依汝賣女生口葉直錢六萬嘉禾六年正月廿日貸(?)男子雷逆收中外估
5.具錢六千
6.大女劉佃賣男生口得直錢五萬嘉禾六年三月廿八日□郡吏張橋收中外估
這份簡冊的內容是由政府金曹下令,都市史唐玉核實吏民私買賣生口及政府向他們收取估錢的行政過程。其中“生口”指的是奴隸或戰俘。“估錢”是交易稅。從這個籍簿我們可以知道,在三國的孫吳是允許奴隸買賣,但需向政府交納交易稅的。估稅有確切的文字記載是在東晉,以前關于估稅的研究,都認為它是從東晉才開始征收的,但從走馬樓吳簡來看,它的征收時間起碼可以上推至三國時期,同時,從三國至東晉,估稅由向買方征收轉變為了買賣雙方征收。現代社會中,如房產中介,仍然沿用古代的做法,向買賣雙方收取費用。不過,孫吳估稅的稅率是很高的,達到了10%,而東晉為4%。
三國的歷史文獻資料罕見,主要是陳壽的《三國志》,但《三國志》有紀傳無志表,后人評其“失在于略”。長沙走馬樓吳簡出土近8萬枚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無疑可以填補許多歷史的空白,前面講的吏民私買賣生口籍簿中的估稅就是其中一例。同時,它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是正史常常遺忘的一角。值得一提的是,走馬樓吳簡中有7萬多都是竹簡。
竹簡,使用于何時,現無從知曉了。但我們可以說,它是在紙被普及之前的書寫材料。直到東晉末年才被已發時四五百年的紙取代。也許大家不禁會問,我們現在看到的早期的文字和書寫材料,不是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的龜甲、牛骨上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和鑄造殷周青銅器內側的銘文的金文么?其實,以簡為書寫材料,至遲在商初就已使用。由于簡很容易損壞、腐爛,所以早期的簡上的文字很難保存下來。《尚書˙多士》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里有“冊”字,寫得就像編連在一起的簡牘。典冊記載的是帝王的命令和典章制度等重要內容,肯定會比甲骨文、金文更重要,文字篇幅也定會更長。我們熟知的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的故事,就可知春秋晚期時,已廣泛使用竹簡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認為當時孔子所使用的簡牘是用皮革編綴的,有學者認為“韋”通“緯”,指橫線,與意為“縱線”的“經”相對應,韋編是橫向穿綴的繩,即編綴用繩。“韋編三絕”即指編繩數次切斷之意。
現在竹簡見諸于實物的,最早是1978年在湖北隨州發現的一座戰國初年曾侯乙墓,墓中有200多枚竹簡。繼而楚簡、秦簡、漢簡、三國簡、晉簡等都有出土。這些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不僅可以補充和豐富歷史、思想、文化等研究,而且還改正某些傳世書籍,甚至保留一些曾經失傳的書籍。郭店楚簡竹簡中有《緇衣》、《五行》《老子》等先秦儒、道兩家典籍與前所未見古佚書共十八篇;尹灣漢簡《神鳥賦》;銀雀山漢簡有《孫子兵法》及四篇佚文,《孫臏兵法》等;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古本《論語》、《儒家者言》、《文子》等古籍……都不勝枚舉。此外竹簡展示了我國各種書體,極大地豐富了文字和書體發展演變,拓展了書法藝術學習和創新。
竹子的品質,是古代君子象征;作為書寫材料,又承載了千余年文化。竹子分布廣、生長周期短,與木簡相比,更適合編綴起來以書冊形式使用。以前認為只有南方有竹子,其實,在秦漢時期的渭水盆地和中原地區,都分布有竹林。我國文明的傳播與流傳,也有賴于竹簡。《后漢書》記載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竹簡的普及是百家爭鳴、思想文化繁榮的基礎,促成了孔子的儒家學說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竹簡的發現,使我們這些后人能一睹歷史容顏,再現文明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