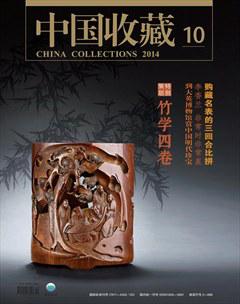民國之夜 有如苦竹
謝其章
民國的竹子,我想應該與唐宋元明清,或更遠的盤古開天地的羲黃時代的竹子無甚區別,一個物種的變異,幾千年是不夠的。以竹入畫,以竹喻君子,我們講得很多;竹子的品種我們也講了很多。回到本題,民國之竹,想說的卻是民國的幾位文人(張愛玲,周作人,胡蘭成,沈啟無),他們和一首詠竹詩的關系,他們和一本《苦竹》雜志的關系。
說起這幾位文人,人們很難把他們與“竹文明”“竹文化”聯系起來,可是他們卻共同賦與尋常的竹子——一種難以言說的苦味。這幾位文學造詣高超,天賦異于常人,但是人生之路,也只有一個“苦”字可以概括。
這三男一女,除了沈啟無,其他三位無須介紹。沈啟無(1902年—1969年),編著有《大學國文》《水邊》(詩集)《近代散文鈔》,一度被稱為“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1944年3月,周作人公開發表《破門聲明》,斷絕與沈啟無一切關系。周作人與沈破門后,沈啟無在北京呆不下去而轉投南方的胡蘭成。如果沒有這次投奔,民國之竹也就與沈沒啥關系了,沈啟無也寫不出那段關于苦竹的華美之辭了。
胡蘭成被官場排擠出來,在野之身閑著也是閑著,1944年10月便在南京辦了一本雜志,取名《苦竹》。《苦竹》連同人雜志都算不上,徑直稱胡蘭成的個人雜志得了,胡幾乎包辦了所有文章,其余幾篇張愛玲、炎櫻、沈啟無,亦是“胡邊人物”。《苦竹》只出了三期,第三期6篇文章全部是胡蘭成寫的,一篇署本名,五篇用的是化名。在創刊號上胡蘭成寫了《周沈交惡》,開頭說:“周作人有「破門聲明」,與沈啟無斷絕師生關系,登在中華日報上,聽人說了,我可沒有見,只在心里這么一閃;這是類似告迕逆,覺得不舒服。”結尾寫道:“周作人喜歡明人小品,而沈啟無歡喜六朝文,還有如,‘絲不如竹,但‘竹不如肉。我以為后唐的空氣比六朝更好,就因為六朝人是作家,而后唐人則本人就是作品。周作人和沈啟無決裂,沒有法子,也只好讓他們決裂吧,我個人,是同情沈啟無的。”
胡蘭成表明是站在沈啟無一方的,弱者,總是被同情。沈被周排擠得連工作都沒得了,破門歸破門,但是周作人的做法有點過,總該讓沈有口飯吃。寫到這,加一句我的想法,文人若選職業,執教鞭為人師似乎是惟一適宜的,最不合適的就是做官。胡蘭成說“前年周作人來南京,官場宴會有兩次我和他在一起,當時心里很替他發愁,覺得這是一種難受的諷刺。但后來知道,近年來他和老官僚們很談得來。這些都是人的塵埃,他會喜歡,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想起來,也只有塵埃才能證明空氣的存在,使清冷,沖淡的老人稍稍熱鬧,于是我替他悲哀。”如果用竹子來比喻,文人賞竹詠竹乃本色當行,但文人自身不是竹子。前面胡蘭成已經說了六朝人與后唐人的差別。
多年以后,胡蘭成說:“南京政府日覺冷落。我亦越發與政府中人斷絕了往來,卻辦了個月刊叫《苦竹》,炎櫻畫的封面,滿幅竹枝竹葉。”炎櫻是張愛玲的“閨蜜”,可是張愛玲后來也不喜得搭理她了,當初她倆是多么要好呀。接下來就要引出沈啟無對炎櫻《苦竹》封面畫的贊美了:
最近看到《苦竹》月刊,封面畫真畫得好,以大紅做底子,以大綠做配合,紅是正紅,綠是正綠,我說正,主要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紅容易流于火燥,用綠容易流于尖新,這里都沒有那些毛病。肥而壯大的竹葉子,布滿圖畫,因為背景是紅的,所以更顯得洋溢活躍。只有那個大竹竿是白的,斜切在畫面,有幾片綠葉披在上面,在整個的濃郁里是一點新翠。我喜歡這樣的畫,有木板畫的趣味,這不是貧血的中國畫家所能畫得出的。苦竹兩個字也寫得好,似隸篆而又非隸篆,放在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葉子似的,換了別的字,絕沒有這樣的一致調和。總之,這封面是可愛的,有東方純正的美,和夏夜苦竹的詩意不一定投合然而卻是健康的、成熟的、明麗而寧靜的,這是屬于秋天的氣象的吧,夏天已經過去了。
沈啟無
《苦竹》封面畫上的那首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正是這首詩將本文的四個文人在一個民國之秋,扯到一起。這首詩是如何構思到《苦竹》封面上去的?是出自誰的好主意?一首絕佳的題畫詩。
現在,我大致弄明白了這首詩是誰寫的和它是如何安排到封面上去的。周作人在《島琦藤村先生》里寫道:“案此系西行法師所作,見《山家集》中,標題曰‘題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不久之間,隨即天明。在《短夜的時節》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約是作者所很喜歡的一首,只是不可譯,現在只好這樣且搪塞一下。”(1943年8月23日)這就很明確了,此詩是日本人原作,周作人譯過來的。
《島崎藤村先生》原刊《藝文雜志》一卷四期(1943年10月),這本雜志的主編是周作人,此文后收入《藥堂雜文》(1944年1月北平新民印書館初版)。周作人的這篇文章被張愛玲看到了(張愛玲是在《藝文雜志》上看到的還是在《藥堂雜文》上看到的?都有可能。),張愛玲在《詩與胡說》中寫道:“周作人翻譯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我勸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輕性智識份子的典型,她看過之后,搖搖頭說不懂,隨即又尋思,說:‘既然這么出名,想必總有點什么東西罷?可是也說不定。一個人出名到某一程度,就有權力胡說八道。”《苦竹》的封面是炎櫻畫的,但張愛玲很大可能參與意見了,這首日本詩十有八九是張愛玲安排上去的。
沈啟無在《南來隨筆》里寫道:“也就是去年秋天的現在,我在朋友的家里,他要我寫一首日本人寫的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這真是一首好詩,表現日本人樸實的空氣,譯成中文,我們也很得一個了解。” 胡蘭成所寫《苦竹》編后,還有一番議論:‘頃刻之間,隨即天明。我知道,這‘頃刻,它有一點讓人不好受;一面在等,一面在驚異忐忑,你的手正有一點兒抖,然而心可是快樂的,很大的快樂,——在恐懼中,不安中,還沒有說出,可是畢竟要說出了。”
民國之夜,有如苦竹;張周沈胡,有如苦竹。